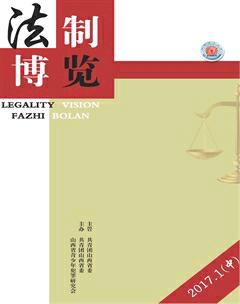信息視野下的刑事卷宗移送制度的研究
陳軍
摘要:〖HJ1.36mm〗在刑事訴訟的卷宗移送制度上,我國(guó)的刑訴法在不同司法背景下經(jīng)歷了三次的改革:1979年習(xí)慣性的全案移送、1996年實(shí)行的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移送、2012年全案移送回歸。中國(guó)的卷宗移送制度改革兜了一個(gè)圈,從終點(diǎn)又回到了起點(diǎn)。而全案移送制度,其仍存在的痼疾:法官預(yù)斷風(fēng)險(xiǎn)仍始終存在。筆者在信息化視野下提出完善卷宗移送制度的建議:實(shí)行電子卷宗。
關(guān)鍵詞:審判中心主義;案卷移送制度;法官預(yù)斷
中圖分類號(hào):D925.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2095-4379-(2017)02-0101-02
信息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為中國(guó)法院確保司法公正、提升審判質(zhì)效、更好維護(hù)社會(huì)公平正義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撐。近年來(lái),中國(guó)最高人民法院將信息化建設(shè)作為一場(chǎng)深刻的自我變革,將信息化成果應(yīng)用于司法審判和法院管理的各個(gè)領(lǐng)域,取得顯著成效。中國(guó)立法者在2012年修改刑訴法的時(shí)候再一次選擇了全案移送制度。但是其中一個(gè)頑疾就是法官預(yù)斷的問(wèn)題仍然解決不了,筆者認(rèn)為電子卷宗是一個(gè)明智的選擇。
一、“全案移送主義”回歸的改革歷程及背景
(一)“全案移送主義”改為“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制度”的改革背景
我國(guó)1979年刑事訴訟法中,確立的是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而且審前審查是實(shí)質(zhì)審查,所以法官在開(kāi)庭前基本已經(jīng)形成了內(nèi)心確信,導(dǎo)致庭審流于形式,有罪判決的證成不發(fā)生在庭審中,這嚴(yán)重違背司法公正和現(xiàn)代法治精神。相較于英美的人權(quán)保障觀的訴訟價(jià)值取向,我國(guó)秉持的是犯罪控制觀,對(duì)于犯罪分子一追到底,所以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只要法官預(yù)斷了,那么危害是極其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hù)權(quán)會(huì)被無(wú)形中削減,預(yù)斷之后是一種偏見(jiàn)。而這與法官公正司法獨(dú)立觀念背道而馳,有損司法形象和尊嚴(yán),帶著這種爭(zhēng)議性的全案移送制度運(yùn)行了17年后,1996年的刑訴法修改時(shí),借鑒了英美法系起訴狀一本主義,然后結(jié)合我國(guó)的司法實(shí)際,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制度應(yīng)運(yùn)而生。
(二)“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制度”改為“全案移送主義”的改革背景
1996的刑訴法為了排除法官的庭前預(yù)斷以及對(duì)于英美法系“起訴狀一本主義”的艷羨規(guī)定了“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制度”。制度設(shè)計(jì)看似很完美,但是法律移植也會(huì)水土不服,“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制度”帶來(lái)很多新的問(wèn)題,首先,該制度并沒(méi)有取得排除法官預(yù)斷的預(yù)期目的,因?yàn)橹饕C據(jù)的最終解釋權(quán)掌握在檢察機(jī)關(guān)手里,一般檢察機(jī)關(guān)為了達(dá)到追訴的目的,只會(huì)移送有罪證據(jù),那些罪輕或者無(wú)罪證據(jù)故意不移送。其次,由于移送的是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那么律師的閱卷權(quán)難以保證。最后,由于主要證據(jù)復(fù)印件制度的存在使得檢察機(jī)關(guān)對(duì)于證據(jù)的使用擁有能動(dòng)性,正是因?yàn)檫@點(diǎn),為檢察機(jī)關(guān)搞證據(jù)突襲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使得審判效率大大降低。為此,2012年刑訴法修改了該項(xiàng)制度,回歸了全案移送制度。但是在當(dāng)前較為復(fù)雜的司法環(huán)境下,以及在大力推進(jìn)司法改革的時(shí)代背景下,如何從案卷移送方式上解決法官預(yù)判以期實(shí)現(xiàn)審判中心主義便成為了當(dāng)下最主要的問(wèn)題。
二、審判中心主義下“案卷移送制度”的問(wèn)題分析
從2012年至今,刑訴法運(yùn)行至今已經(jīng)是4個(gè)年頭了,但是法官預(yù)斷、庭審流于形式問(wèn)題依舊存在。所以在大力倡導(dǎo)審判中心的今天較為科學(xué)的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一)法官預(yù)斷風(fēng)險(xiǎn)仍然不能避免
早在新刑訴法出臺(tái)之前就有學(xué)者對(duì)于全案移送制度表示擔(dān)憂,1996年刑訴法改革全案移送制度就是為了能夠排除法官庭前預(yù)斷,因?yàn)樯钪ü兕A(yù)斷對(duì)證據(jù)裁判主義和自由心證的危害,所以我國(guó)開(kāi)始了由強(qiáng)職權(quán)主義模式到抗辯式模式改革,但是全案移送主義的恢復(fù)可能會(huì)完全摧毀抗辯式庭審改革成果。其次檢察機(jī)關(guān)把所有卷宗全部移送到法院,由于中國(guó)法院對(duì)案卷的依賴性很強(qiáng),合議庭成員勢(shì)必會(huì)通過(guò)研讀案卷內(nèi)心確信斷案,這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前一度泛濫的“先定后審”現(xiàn)象,極有可能會(huì)“死灰復(fù)燃”。為什么立法者還是選擇了以前令人詬病的全案移送制度呢?
(二)默讀審判難以避免
自由心證原則和證據(jù)裁判主義要求法官斷案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通過(guò)內(nèi)心的良知、理性等對(duì)證據(jù)的取舍和證明力進(jìn)行判斷,并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法律不預(yù)先設(shè)定機(jī)械的規(guī)則來(lái)指示或約束法官,而由法官針對(duì)具體案情,根據(jù)經(jīng)驗(yàn)法則、邏輯規(guī)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lái)自由判斷證據(jù)和認(rèn)定事實(shí)。而全案移送制度讓法官在審前就接觸大量案件事實(shí)和證據(jù),不由自主的就會(huì)形成預(yù)斷,那么等到真正的庭審中,法官并不注重庭審過(guò)程,審判只是走形式。默讀審判也再所難免。
三、在信息化視野下完善卷宗移送制度的建議
刑事訴訟應(yīng)該采取哪種案卷移送方式在我國(guó)是個(gè)具有爭(zhēng)議的難題,在刑訴法修改以前理論和實(shí)務(wù)界就此展開(kāi)了激烈的討論,有保守派的:恢復(fù)全案移送,也有激進(jìn)派的:起訴狀一本主義。我認(rèn)為這兩種觀點(diǎn)都有待商榷,徒法不足以自行,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我國(guó)的具體國(guó)情。因此,筆者嘗試站在信息化視野下給出自己的建議:
(一)電子卷宗概述
法官作為一個(gè)有思想的人存在,有理性一面,也有感性一面。有自己的喜怒哀樂(lè),而作為法律人的法官,社會(huì)將其至于一個(gè)崇高的理性人地位。但人天生有局限性,法官斷案中自由心證肯定會(huì)受這些影響,這是在所難免的。為了克服法官預(yù)斷,站在信息化的視角看,電子卷宗或許是一個(gè)突破口。技術(shù)似乎比人更具有中立性。電子卷宗就是公安機(jī)關(guān)將所有案卷材料移送到檢察機(jī)關(guān)的案管中心,由案管中心將紙質(zhì)案卷材料依托數(shù)字影像、文字識(shí)別等技術(shù)制作而成的電子文檔,圖像、音頻、視頻等電子文件。在最近舉行的世界互聯(lián)網(wǎng)大會(huì)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zhǎng)周強(qiáng)提出了建設(shè)智慧法院,打造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而推行電子卷宗是應(yīng)有之義,電子卷宗可以提高審判效率、減輕法官預(yù)斷、解決律師閱卷難的問(wèn)題。
(二)電子卷宗的建立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院長(zhǎng)周強(qiáng)大力推進(jìn)審判信息化改革,并形象的稱信息化建設(shè)和司法改革是人民司法事業(yè)發(fā)展的“車之兩輪、鳥(niǎo)之兩翼”,信息化是人民法院又一場(chǎng)深刻的自我革命,信息化已成為司法能力和司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新的審判方式。
電子卷宗就是充分利用大數(shù)據(jù)、云計(jì)算、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和機(jī)器學(xué)習(xí)等技術(shù),將紙質(zhì)卷宗技術(shù)轉(zhuǎn)化,如江蘇法院研制出的智審1.0系統(tǒng),通過(guò)OCR識(shí)別等技術(shù),一鍵掃描,實(shí)現(xiàn)電子卷宗自動(dòng)生成,智能分類,減少了人工制作過(guò)程。同時(shí)自動(dòng)識(shí)別的電子卷宗信息還可自動(dòng)回填至案件信息表中,減少了人工錄入工作量;法官還能直接檢索、編輯、利用電子卷宗,激活了數(shù)據(jù)價(jià)值。電子卷宗制作的證據(jù)清晰、直觀、法庭說(shuō)理性強(qiáng),不僅法庭各方參與者都能看到,法官還能在庭審中對(duì)證據(jù)進(jìn)行放大、標(biāo)注等操作,改變了傳統(tǒng)庭審中法官、辯護(hù)律師、被告人及旁聽(tīng)群眾“聽(tīng)”證據(jù)的局面,使庭審更加規(guī)范、直觀,法官也不用在庭審前仔細(xì)研讀卷宗形成內(nèi)心確信斷案,這種直觀的形式也激活了整個(gè)庭審,有利于雙方的辯論,使死氣沉沉的庭審現(xiàn)場(chǎng)充滿活力,更有利于庭審實(shí)質(zhì)化,實(shí)現(xiàn)審判中心主義。去年7月8日,由四川省資陽(yáng)市檢察院公訴的謝某、樊某販賣毒品案一審,法庭調(diào)查階段,樊某當(dāng)庭翻供,辯稱“不清楚販賣的是毒品”,控方當(dāng)即通過(guò)電子卷宗系統(tǒng),快速檢索并展示了偵查階段的訊問(wèn)筆錄。犯罪嫌疑人翻供時(shí),利用電子卷宗展示原始證據(jù)對(duì)于法庭不予采信其辯駁起到重要作用。
司法改革苛于法官的責(zé)任過(guò)大導(dǎo)致法官不得不庭前仔細(xì)研讀卷宗,電子卷宗很好的解決了這個(gè)問(wèn)題,電子卷宗使法官直觀、生動(dòng)的了解案情,可以簡(jiǎn)化程序,做到有的放矢。法官在正式庭審中更加關(guān)注審判中來(lái),而不是研讀案卷,而且電子卷宗的好處不止于此,過(guò)去原始卷宗就一份,只能輪流看,要核實(shí)細(xì)節(jié)就更加困難。而假如使用電子卷宗的證據(jù)回溯功能,只要鼠標(biāo)一點(diǎn),引用的證據(jù)在哪一頁(yè)就原汁原味的展現(xiàn)在面前。這就使得實(shí)行檢察官辦案質(zhì)量終身負(fù)責(zé)制有了可靠的工具,與此同時(shí),承辦法官在辦理案件時(shí),可以通過(guò)電子卷宗系統(tǒng)的證據(jù)管理功能,明確哪些證據(jù)已經(jīng)使用、哪些證據(jù)未使用、哪些證據(jù)有疑問(wèn),并自動(dòng)匯總為閱卷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的案件存在的問(wèn)題,有效避免遺漏事實(shí)、遺漏證據(jù)、遺漏疑點(diǎn)等情況,在檢察界,這不亞于一場(chǎng)信息化革命。電子卷宗系統(tǒng)的使用極大提高了審判效率,很好的解決了“案多人少”的窘境。
電子卷宗還有一個(gè)優(yōu)點(diǎn)就是一經(jīng)掃描,不能更改,只要改動(dòng)就會(huì)留下證據(jù),是最原始的辦案記錄。所以會(huì)倒逼司法人員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做到依法辦案,是一種無(wú)形的監(jiān)督模式。而且隨著庭審實(shí)質(zhì)化改革的推進(jìn),現(xiàn)場(chǎng)出示原始證據(jù),執(zhí)法過(guò)程是否有瑕疵一目了然,這使得偵查人員更愿意出庭作證,大大提高證人出庭率,有利于實(shí)現(xiàn)審判中心主義。
執(zhí)業(yè)律師閱卷難,是一個(gè)“老大難”。紙質(zhì)卷宗只有一套,承辦檢察官自己要看,分管檢察院、檢委會(huì)專委在討論審核案件時(shí)也需要查閱,導(dǎo)致給律師的閱卷時(shí)間相對(duì)有限,律師閱卷不充分,那么犯罪嫌疑人的辯護(hù)權(quán)難以保障,控辯雙方力量懸殊,法庭庭審呈現(xiàn)“二打一”的局面。但是如果推行電子卷宗,律師可以在指定期間去檢察院的案管中心閱卷,而且隨著電子卷宗系統(tǒng)升級(jí),基本可以實(shí)現(xiàn)律師異地閱卷,以往需要到當(dāng)?shù)厝ラ喚淼陌讣灰f交申請(qǐng),很快就可以拿到電子卷宗,節(jié)約成本,方便律師。傳統(tǒng)辦案模式下,隨著案件辦理進(jìn)展,紙質(zhì)卷宗要在偵查機(jī)關(guān)、檢察機(jī)關(guān)和法院之間流動(dòng),有的案卷材料達(dá)到萬(wàn)頁(yè),繁瑣的搬運(yùn)、整理、分析工作占據(jù)了辦案人員大量時(shí)間。隨著電子卷宗系統(tǒng)的推行,不僅提高了審判效率,而且還有利于減輕法官預(yù)斷,使法官更加注重庭審,而不是通過(guò)研讀卷宗來(lái)定罪量刑。
[參考文獻(xiàn)]
[1]龍宗智.論建立以一審?fù)彏橹行牡氖聦?shí)認(rèn)定機(jī)制[J].中國(guó)法學(xué),2010(2).
[2]陳瑞華.案卷筆錄中心主義—對(duì)中國(guó)刑事審判方式的重新考察[J].法學(xué)研究,2006(4).
[3]張建偉.審判中心主義的實(shí)質(zhì)與表象[N].人民法院報(bào),201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