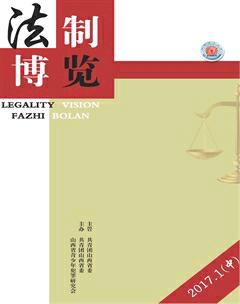刑辯律師的執業風險與防范
張春霞
摘要:刑事辯護律師是被告人合法權利的爭取者和維護者,刑事辯護律師權利的實現程度關乎著被告人自由的保障程度。對于律師在執業過程中的行為多數國家采用非刑事制裁來實現,而我國刑事法律規范對刑辯律師的設限則相對較多,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部分條文的修改更是引起律師群體的不滿,本文主要討論《刑法修正案(九)》第36、37條可能招致的刑辯律師執業風險。
關鍵詞:合法權利;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D926.5;D9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02-0218-02
一、對《刑法修正案(九)》第37條的解讀
《刑法修正案(九)》第37條是對刑法第309條“擾亂法庭秩序罪”的修改,出發點是為了更好地維持法庭秩序,保證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關于該條款的修改法官群體表示支持,律師群體則多數反對。
遭受律師群體詬病的原因可能是:第一,修正案增設了第3和第4款規定,但新增的第3款規定的“侮辱”“誹謗”“威脅”等文字性表述主觀性和不確定性較強,主要依靠法官自由裁量可能導致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同時在刑法中已有侮辱罪、誹謗罪的規定,行為人的類似行為完全可以評價為侮辱罪、誹謗罪,無須單獨另行規定;而且這一將語言暴力入罪的規定也可能弱化律師群體在法庭辯論階段的積極性,我國律師在法庭上并沒有言論豁免權,“律師界之所以極力反對,是擔心這一條款被濫用。一旦被濫用,律師可能成為這一條款最大的受害群體,他們在法庭上偶爾的情緒激動、出言不慎就可能入罪,進而形成“寒蟬效應”[1],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而言可能不利于律師有效辯護的進行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推進。另外有學者認為本罪的行為主體并不是針對律師,本罪行為人甚至可以包括審判法官本人,這一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國目前的庭審制度是以法官為主導的,如果本罪主體包括法官本人會導致審判法官在該案中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不利于對案件做客觀中立的判斷,裁判結果難免有失偏頗。
第二,刑罰是最為嚴重的處罰措施,通常認為通過其他法律手段可以達到同等法律效果時便不再需要刑法進行規制,這也是刑法謙益性的要求。我國現有法律體系(除刑法外)對擾亂法庭秩序的行為已有較為完備的規定,如《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律師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均有規定,分別予以行業紀律處罰、行政處罰、司法處罰,刑法另設條文進行規制有違刑法謙抑原則的要求。
另有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很多律師擔心本次第37條的修改是針對律師群體,對于這一點筆者對我國“擾亂法庭秩序罪”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做了一個大概的數據統計。截止2016年11月7日中國裁判文書網收錄的“擾亂法庭秩序”的刑事案件共計37例,處罰結果分為3大類:其中30例是以本罪定罪處罰的,2例是以他罪(分別是尋釁滋事罪1例,妨害公務罪1例)定罪處罰的,5例是不予受理的。比較有意思的結果是在上述所有案件中沒有一例的行為主體是律師的,雖然這并不能說明該條就不是專為律師而設,但有一點可以看出,律師很少會以本罪定罪處罰。當然,由上述數據可以得知自1997年刑法中新增“擾亂法庭秩序罪”(包括《刑法修正案(九)》對本罪的修改)的近20年以來司法實踐中提起本罪的案件量相對比較少,對于適用頻次不高的條款投入大量的立法成本是不明智之舉。
二、對《刑法修正案(九)》第36條的解讀
第36條新增泄露案件信息罪,本罪設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限制律師在法庭以外的言論自由,將律師的言論自由與占領輿論“高地”辯論策略運用由“強強聯合”式轉向“背道而馳”式。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高度普及和發達的社交軟件更是成為律師引導輿論的“東風”,廣泛的受眾群體通過大肆傳播的信息得以接觸和知悉相關案件信息對于監督案件的公正審判有著積極的作用,但這些帶有個人立場的誘導性語言使得對案情偏聽偏信的強大“民意”成為司法審判的輿論壓力,法院即使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做出符合法律但未順應“民意”的審判仍有可能遭到公眾質疑。《刑法修正案(九)》對律師庭外言論的規制造成律師恐慌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本次修法的如下修改。
首先,泄露案件信息罪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一詞定義不明確,如“不應當公開”既可以理解為“依照法律規定不應當公開”,也可以理解為“依照司法解釋或規范性文件及行業規范不應當公開”,極端者甚至可以理解為“依照司法辦案機關要求不應當公開”,[2]如此容易導致律師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證據,披露案卷材料時遭受本罪的指控,而在36條規定出臺之前律師有以上違規行為時受到的是行業紀律處分或者行政處罰,36條擴大化了入罪范圍。同時容易導致法官審理該類案件時可行使的自由裁量權范圍過大,不利于維護同類案件裁判結果的統一性。
其次,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辯護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有權予以保密。”該規定與第36條矛盾之處在于:第一,對于律師而言上述第46條的規定是權利,36條則是義務,義務是必須履行的,權利卻是可以放棄的,“對權利的放棄并不會產生不利的后果,也就是說當辯護律師放棄保密權而泄露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時并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三、刑辯律師執業風險防范
無論是擾亂法庭秩序罪還是泄露案件信息罪,最基本要求是對于現有的法律條文做出合理的立法解釋,明確“侮辱”、“誹謗”“不應當公開的信息”等的具體指向,這樣既使法院裁判有法可依,又使律師行使權利明確得到法律保障。為保證案件得到公正審判實現結果正義,在涉及上述36條、37條的罪名指控時應當堅守程序正義,借鑒《刑事訴訟法》關于“妨礙作證罪”的規定適用指定管轄、異地管轄等特別程序,任何人不得擔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將案件交由原審法院之外的法院進行審判,這樣既能防止職業報復又能保證辯護律師的有效辯護。
《律師法》第37條規定律師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并沒有其他配套規定進行落實,條文形同虛設,我國可以參照修改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0條規定的律師相關言論享有的民事以及刑事上的豁免權,讓律師敢于發聲,為當事人權利進行有效抗爭。同時,律師群體應提高自身素質,再好的制度要得到預期的效果都必須有合格的執行者,否則制度再完善執行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因此我們在改善制度同時應努力提高律師群體自身素質,嚴格依照法律辦事,即使是死磕也應當是有理有據的磕,而不是一味地胡攪蠻纏,在實現司法公正的道路上,律師與檢察官、法官一樣目標是一致的,三方都是正義的推進者。
律師應充分行使作為公民享有的言論自由權,但在法庭外應審慎的發表自己的言論僅能客觀介紹案件基本信息或對案件事實,不得在案件未經法院裁判,包括審判開始前和審判進行中,利用社交軟件或傳媒對案件做傾向性或引導性評價。在輿論報道對案件當事人嚴重不公正時,律師可對此作出回應,但回應的目的僅在于減輕不公正的輿論影響。
[參考文獻]
[1]擾亂法庭秩序罪”該怎么改[N].南方周末,2015-7-17(1638).
[2]馬晶等.律師庭外言論規制—兼論刑法修正案九“泄露案件信息罪”[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2(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