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shè)計與生活世界
李清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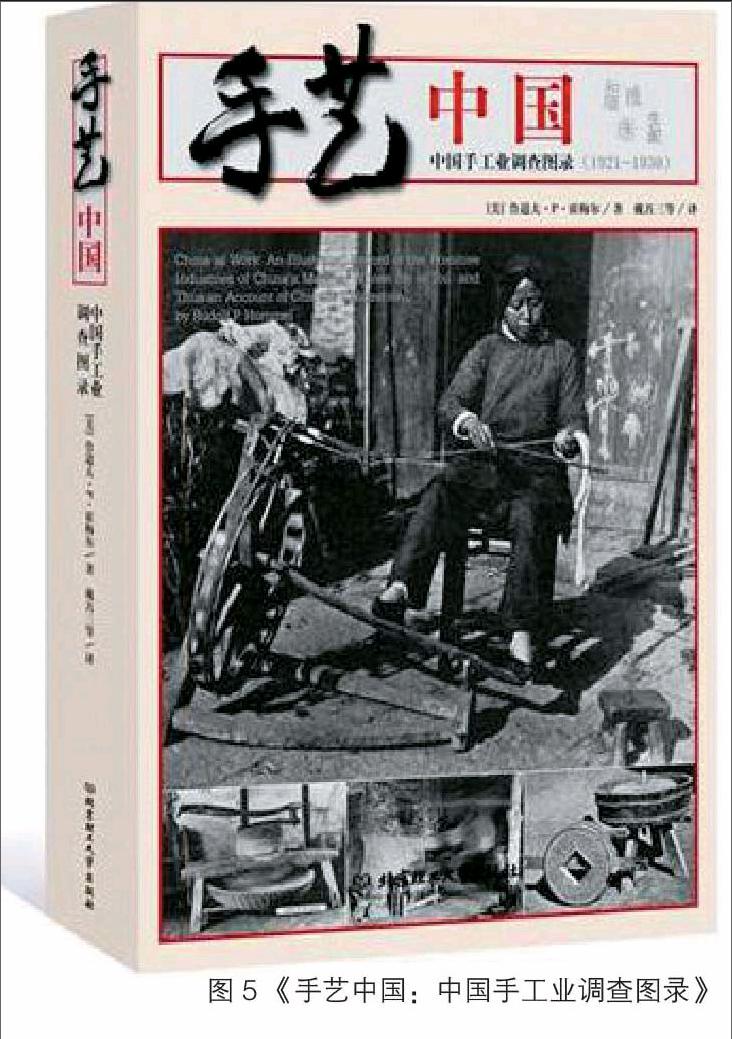


[摘要]工業(yè)時代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給人類生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環(huán)境惡化、資源枯竭、國家和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區(qū)域性政治動蕩等等;更深層次的危機還有文化多樣性和傳統(tǒng)文化的消失、人類生存價值感和意義感的缺失等。在后工業(yè)時代。這些危機更是日益顯露出來。設(shè)計現(xiàn)象學啟示我們以極富智慧的方式對待科學技術(shù)、自然環(huán)境與人類自身之間的關(guān)系,啟示我們?nèi)绾卧谏钍澜鐚ふ胰祟惿娴膬r值感和意義感。對當代設(shè)計文化的現(xiàn)象學反思,其目的并非倡導放棄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和工藝而恢復到傳統(tǒng)的手工藝制造(這是典型的烏托邦主義和歷史還原論)。而是要從中汲取傳統(tǒng)設(shè)計文化的智慧和精髓,努力在當下的設(shè)計實踐中追尋生命存在的價值感和意義感。實現(xiàn)向生活世界的回歸。
[關(guān)鍵詞]設(shè)計;生活世界;當代設(shè)計文化;現(xiàn)象學反思
文明史的研究表明,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一個不斷累積和漸進的過程。其總體呈現(xiàn)為一種加速度的運動軌跡:人類花費了上百萬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從猿到人的進化;在之后的幾十萬年至數(shù)千年的歷史期間,人類社會的生產(chǎn)力和科學技術(shù)水平以異常緩慢的速度處于不斷地累積和發(fā)展過程中;最后,在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內(nèi),人類先后完成了文明史上影響深遠的三次科技革命,把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帶入了一個高速發(fā)展的軌道。回顧最近三百年的歷史,三次科技革命不但賦予了人類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強大力量,而且創(chuàng)造了夢幻般的人類生活圖景:高效智能的機器、極大豐富的商品、方便快捷的交通、觸手可及的遠程即時通信、無處不在的信息流通與共享、數(shù)字化的生存方式……似乎即便是上帝,也要為人類的偉大成就歡欣鼓舞。
然而,現(xiàn)實遠不如那么樂觀,正當人類沉浸于自己創(chuàng)造的巨大成就中時,一系列文明的副產(chǎn)品無情地敲碎了人類的酣夢:環(huán)境惡化、資源枯竭、國家和地區(qū)發(fā)展的不平衡、區(qū)域性的政治動蕩等等;更深層次的危機還表現(xiàn)為文化多樣性和傳統(tǒng)文化的消失、人類生存的價值感和意義感缺失等等。這一切都迫切需要我們對既創(chuàng)造了人類輝煌文明又給人類生存帶來了深層次危機的當代設(shè)計文化展開深刻反思。
一、后工業(yè)時代的設(shè)計文化與人類未來抉擇
后工業(yè)社會的概念首先由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DanieI Bell)提出。他根據(jù)人類社會組織、技術(shù)發(fā)展狀況、生產(chǎn)模式和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xiàn)出的不同面貌,把人類社會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前工業(yè)社會、工業(yè)社會和后工業(yè)社會。我們把貝爾的觀點稍加拓展便能描繪出一幅人類文明發(fā)展歷程的生動圖景:前工業(yè)社會是蒸汽機(圖1)出現(xiàn)之前的傳統(tǒng)社會,它以傳統(tǒng)主義為軸心,以自然需求為驅(qū)動力,人類生存完全依賴于未經(jīng)改造的大自然;工業(yè)社會以經(jīng)濟增長為軸心,以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為驅(qū)動力,人類依仗機器向大自然瘋狂攫取生活資料;而后工業(yè)社會以知識為軸心,以消費經(jīng)濟為驅(qū)動力,人類仰仗高度發(fā)達的科學技術(shù)變本加厲地開發(fā)、利用和消費資源。
在后工業(yè)時代,人類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心由第一產(chǎn)業(yè)的農(nóng)業(yè)和第二產(chǎn)業(yè)的制造業(yè)轉(zhuǎn)向了以服務業(yè)為核心的第三產(chǎn)業(yè)。服務業(yè)發(fā)展的目標正是為高度發(fā)達的商品經(jīng)濟開辟和培育消費市場,因此它為消費經(jīng)濟的高歌猛進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消費也因此成為后工業(yè)時代經(jīng)濟發(fā)展的巨大引擎。在后工業(yè)社會的消費經(jīng)濟時代,經(jīng)濟發(fā)展的“速度”和“總量”、資源配置的“質(zhì)量”和“效率”成為衡量世界各國經(jīng)濟活力、國民生活水平進而是“幸福指數(shù)”的重要指標。因此,在商品經(jīng)濟高度發(fā)達的前提下和消費引擎的強有力推動之下,各種服務業(yè)和服務業(yè)的基礎(chǔ)和媒介行業(yè)呈井噴式增長;銀行、互聯(lián)網(wǎng)、物流、電子商務、休閑旅游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整個世界經(jīng)濟呈現(xiàn)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然而,任何一位稍具反思精神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這種依靠消費刺激來推動和維持的經(jīng)濟增長將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后果。稍一反思,這一問題的答案便昭然若揭。就拿當下正發(fā)展得如火如荼的電子商務來說:伴隨著商品的盲目和無序流動,伴隨而來的是交通壓力的劇增、資源的驚人浪費(如交通運輸設(shè)施、人力、燃油、包裝)和環(huán)境的急劇污染;商品和快遞包裝由于缺乏有效監(jiān)管而造成的資源浪費、環(huán)境污染以及隨之而來的安全隱患。但與此同時,生產(chǎn)商品的工業(yè)企業(yè)并未因電子商務的繁榮就退出了歷史舞臺。尤其在我國,由于工業(yè)化進程所經(jīng)歷的時間較為短暫,因此曾經(jīng)西方工業(yè)革命時期由于技術(shù)落后、規(guī)劃不合理和管理粗放而造成的觸目驚心的環(huán)境污染狀況當前正在我們國家大規(guī)模地蔓延開來。近年來國內(nèi)高發(fā)的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等惡性事件,正是這一狀況的集中體現(xiàn)。我們的生存環(huán)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和危機。
一方面是工業(yè)領(lǐng)域所造成的巨大環(huán)境污染(圖2),一方面是消費經(jīng)濟領(lǐng)域所造成的資源驚人浪費,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得經(jīng)濟可持續(xù)發(fā)展受到嚴重制約的同時也使得人類生存狀況急劇惡化。由此可見,商品的極大豐富和科技的飛速發(fā)展并未給人類帶來真正福祉。即便是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其環(huán)境經(jīng)過幾百年的持續(xù)治理已經(jīng)大有改觀,但其建立在消費經(jīng)濟基礎(chǔ)之上的發(fā)展模式仍然面臨著深層次危機。尤為重要的是,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和認識的逐步深入,人們越發(fā)認識到,地球作為人類休戚與共的家園,任何一個國家的自然和生態(tài)環(huán)境都不能“獨善其身”,任何一個區(qū)域的環(huán)境污染也都將直接影響到整個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良性運轉(zhuǎn),因此人類必須建立起了一種整體的生態(tài)觀和發(fā)展觀。
更深層次的反思告訴我們,人類當下的環(huán)境和生存危機與我們自身的設(shè)計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對人類當前的設(shè)計文化進行深刻反思就成為當務之急。從現(xiàn)象學的角度來看,我們自身的設(shè)計文化不但直接導致了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持續(xù)惡化,而且這種設(shè)計文化所造就的自然態(tài)度和工具理性,把人類生存中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價值感和意義感無情地消解了。從這一角度來看,人類當下的設(shè)計文化正面臨著一個關(guān)鍵抉擇,這決定了人類能否走出當下危機,走上一條可持續(xù)的健康發(fā)展之路。
在這一方面,傳統(tǒng)設(shè)計文化的生活世界中正隱藏著一條能使人類當下設(shè)計走出深刻危機的可能性路徑。傳統(tǒng)技藝中正蘊藏著人類生存的深層次智慧。從現(xiàn)象學和布迪厄社會學思想的角度來看,世界不同民族地方設(shè)計文化中的傳統(tǒng)技藝不但是身體經(jīng)濟學對主體身體結(jié)構(gòu)和動力學特征長期干預和模塑的結(jié)果,更是特定設(shè)計文化場域?qū)χ黧w習性長期培育的結(jié)果,與此同時,這也是主體文化身份的一個逐步建構(gòu)過程。這一培育、模塑和建構(gòu)過程的最終結(jié)果,不但保證了人類相互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更保證了文化中的每一個體在生活世界中能尋找到人類生存豐盈的價值感、意義感和歸屬感。從而使人類走上一條健康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道路。
二、設(shè)計的文化身份與生活世界中人類存在的價值感和意義感
身份是文化研究領(lǐng)域一個異常復雜的概念,
它通常在個體與群體兩個維度上展開。正如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在個體層面,文化身份的研究通常與精神分析話語中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概念密不可分;而在群體層面上,文化身份的研究又與民族(ethnic)、種族(racial)和國家(nation)等定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概念息息相關(guān)。但顯然,無論是在個體層面還是群體層面,文化身份都絕非某種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恰恰相反,它是一個不斷建構(gòu)的動態(tài)過程。芬蘭民俗學家勞里·杭柯(Lauri Honko),就把群體文化身份界定為“通過不斷的協(xié)商把人們聯(lián)合在一體和歸屬的現(xiàn)實之中,并且在宇宙中為‘我們建構(gòu)了一個空間(也把‘我們和‘他們區(qū)分開來)的一系列價值、象征和情感”。而從精神分析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個體的文化身份則伴隨著語言能力的習得,在個體人格的社會化過程中被逐步建構(gòu)起來。雅克·拉康的鏡像理論正闡明了這樣一個建構(gòu)過程。與此同時,個體文化身份與群體文化身份并非兩個彼此隔絕的領(lǐng)域,布迪厄的社會學思想就把這兩個領(lǐng)域有機地統(tǒng)合了起來。他提出的文化資本、習性和場域等概念,正可以對我們思考設(shè)計中的文化身份問題提供極富價值的啟發(fā)。
從設(shè)計史的角度來看,世界每一民族的設(shè)計文化,其一方面植根于民族群體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tǒng)中,另一方面又與當下每一個體的生活世界密不可分。也就是說,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無論是群體還是個體,設(shè)計文化都是文化身份建構(gòu)過程中一個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它參與到了民族和個體文化身份建構(gòu)的動態(tài)過程中。
在當代西方文化史上,世界后現(xiàn)代狀況的出現(xiàn)與人類學對他者的發(fā)現(xiàn)和深入研究密不可分。正是人類學對他者的發(fā)現(xiàn)和深入研究嚴正挑戰(zhàn)和質(zhì)疑了西方中心主義和邏各斯中心主義。用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話說,就是它動搖了西方人的道德自信和智力自信。隨著西方中心主義和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道德自信與智力自信的動搖,令人眼花繚亂的后現(xiàn)代主義學說在整個西方當代文化中大行其道。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因此源源不斷地生產(chǎn)出形形色色的后現(xiàn)代知識。正如利奧塔所言:“后現(xiàn)代知識并非簡單的權(quán)威工具;它提升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并且強化我們?nèi)淌懿豢赏s性的能力。它的原則不是專家的一致性,而是發(fā)明者的形似性。”在后工業(yè)時代,伴隨著第三次產(chǎn)業(yè)革命而來的交通、信息和通信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進一步把由人類學家們發(fā)起的對于他者的研究、理解和交往推進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西方中心主義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再也不能適應全球化的發(fā)展浪潮,他者文化在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過程中,在理論上被抬升到了到了一個與“我文化”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后工業(yè)時代,“我文化”在與“他者文化”之間的頻繁交往過程中,這種交往行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被納入到了“我文化”的身份建構(gòu)和“協(xié)商”過程中。而且尤為重要的是,工業(yè)時代造就的工具理性和自然態(tài)度的大規(guī)模泛濫,在后工業(yè)時代不但直接造成了整個自然環(huán)境的急劇惡化和資源的枯竭,而且伴隨著不同文化間交往過程的推進,不斷擠壓著文化中風俗習慣、情感、價值、道德和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的生存空間,造成了主體生活世界中價值感和意義感的普遍喪失。人類生存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危機顯然與人類設(shè)計文化直接相關(guān),這就迫切需要我們對當下的設(shè)計文化展開深層次反思。
生活世界是胡塞爾現(xiàn)象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把人類對待世界的態(tài)度區(qū)分為自然態(tài)度和科學態(tài)度。胡塞爾認為,自然態(tài)度催生出了自然科學,它把包括人在內(nèi)的整個世界存在當作客觀的異己之物來加以對待。這種態(tài)度進一步催生出了實證主義觀念,它認為一切知識,其存在的唯一合法標準即在于可實證性或可檢驗性,一切與這一標準不相符合的東西就不能稱之為知識,將被從知識王國中無情地驅(qū)逐和清理出去。在近代,自然科學強有力地推動了工業(yè)革命,其決定性勝利不但模塑了人類對待世界(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態(tài)度,更使得實證主義觀念大行其道,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價值觀。人類生存中更為根本的領(lǐng)域,如情感、價值、道德及宗教信仰等,由于不符合實證主義的知識標準,因此被不斷蠶食,被從神圣的知識王國中驅(qū)逐出去。與自然態(tài)度相比,現(xiàn)象學態(tài)度則是一種反思性的態(tài)度,它致力于通過反思把我們帶回到那個“原始明見性”的未受自然科學實證觀念所污染的世界,如其所是地呈現(xiàn)事物在世界中的存在,在這種反思態(tài)度中,人類的情感、價值、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等,都有其自身存在合法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塞爾提出了“生活世界”這一概念。
從現(xiàn)象學的角度來看,工業(yè)時代的設(shè)計正是自然態(tài)度在設(shè)計領(lǐng)域的集中體現(xiàn),是自然科學實證主義價值觀勝利的又一決定性領(lǐng)域。在工具理性傳統(tǒng)浸染和實證主義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現(xiàn)代設(shè)計,集中表現(xiàn)為對新技術(shù)、新材料和新工藝的極力推崇,對機械化、規(guī)模化生產(chǎn)所帶來的高效率和社會富足歡欣鼓舞。這種設(shè)計文化景觀在工業(yè)時代的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中隨處可見。如紐約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在1934年組織的“機器藝術(shù)展”,就“強調(diào)簡潔的、幾何化的、經(jīng)典的形式,從符號上和物質(zhì)上適應新材料和現(xiàn)代批量生產(chǎn)技術(shù)”。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因此倡導一種“機器美學”,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就提出,住房是居住的機器,倡導建筑設(shè)計的極簡原則(圖3)。在《明日之城》的“前言”部分,柯布西耶寫到:“城市是人類的工具。但時至今日,這種工具已經(jīng)鮮能盡其功能。城市,已失去效率:它耗蝕我們的軀體,它阻礙我們的精神。城市里四起的紊亂令人深感冒犯:秩序的退化既傷害了我們的自尊,又粉碎了我們的體面。它們已不適宜于這個時代,它們已不適宜于我們。”正是對城市規(guī)劃現(xiàn)狀的極度不滿,他才提出“明日之城”理想城市形態(tài)規(guī)劃的烏托邦構(gòu)想;包豪斯提出設(shè)計中“形式追隨功能”的主張,其第一任校長、著名建筑設(shè)計師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還提出“少即是多”的原則(圖4),認為“好的設(shè)計可以讓人一眼看出建筑的用途。將裝飾、象征主義和姿態(tài)抹掉,留下的便是純粹的骨架:質(zhì)地、顏色、重量、比例和輪廓”。這種對新技術(shù)、新材料和新工藝的推崇,對理性、秩序、功能、效率和批量化生產(chǎn)的極度推崇,就構(gòu)筑起了西方工業(yè)時代設(shè)計文化的獨特景觀。
在工業(yè)時代的設(shè)計文化中,由于對功能、技術(shù)、效率、秩序的狂熱追求,設(shè)計中的裝飾、美學風格、觸感甚至舒適性體驗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這就造成了設(shè)計對人類生存更為根本的價值、道德、情感體驗、宗教信仰以及與這些要素相伴而生的風俗習慣等文化要素之生存空間的致命擠壓和根本性忽略。
在當下,異彩紛呈甚至光怪陸離的“他者文化”伴隨著第三次產(chǎn)業(yè)革命帶來的交通、信息和通信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而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呈現(xiàn)在每一個“我文化”之前。“他者”的設(shè)計文化在理論上獲得了與“我”的設(shè)計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面對異彩紛呈而又光怪陸離的“他者文化”,“我”產(chǎn)生了對自身文化進行反思的沖動,這種反思不斷加深著“我”對自身文化身份的危機感和焦慮意識,于是文化歸屬和文化認同的迫切性就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正是人類對自身生存中價值感和意義感被無情消解而產(chǎn)生的一種深層次焦慮的集中體現(xiàn)。深陷危機和焦慮中的人類,急切地渴望重新回到那個情感、價值、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等都有其存在之堅實根基的、未受自然科學實證主義觀念所“污染”的那個“原始明見性”的生活世界。
三、設(shè)計向生活世界的回歸
毫無疑問,人類企圖重新回到那個完全未受實證主義觀念“污染”的、“原始明見性”的生活世界,并非倡導今天的設(shè)計文化完全放棄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和工藝而回復到傳統(tǒng)的手工藝制造。這是典型的烏托邦主義和歷史還原論,在現(xiàn)實語境下不但完全不具備可操作性,而且是根本上的逆潮流而動,將被歷史無情拋棄。通過對設(shè)計文化進行反思,我們的目的是在人類當下乃至未來設(shè)計中以增加對審美、情感、道德、宗教信仰乃至風俗習慣充分尊重的方式,來在設(shè)計文化中追求人性尊嚴和人類生存的價值感和意義感,從而回復到人類本真的生活世界。
在為這一偉大使命而奮斗的歷程中,我們顯然任重而道遠,涉及的問題更是千頭萬緒,可能會遭遇的困難也不勝枚舉。但有一點無疑是可以肯定的: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人類能夠繼續(xù)生存和發(fā)展下去的唯一道路。
現(xiàn)實地看,我們確實可以從對地方設(shè)計文化中傳統(tǒng)技藝的深層次反思中,尋找到如何對待科學技術(shù)、自然環(huán)境與人類自身之間關(guān)系的深層次答案,從而啟示我們?nèi)绾卧谏钍澜鐚ふ业饺祟惿娴膬r值感和意義感。在后工業(yè)時代,作為對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一味追求功能、效率、理性和秩序的一種反動,后現(xiàn)代設(shè)計越來越關(guān)注設(shè)計物品的語境性特征,越來越關(guān)注地域文化中設(shè)計物品使用者獨特的審美、情感、道德倫理和風俗習慣等人性化訴求。這與工業(yè)時代的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比較起來無疑是一種巨大進步。羅德島設(shè)計學院自由藝術(shù)系主任丹尼爾·卡維基(Daniel Cavicchi)在談羅德島設(shè)計學院的培養(yǎng)目標時就指出:“設(shè)計師為特別的人群、地域、和狀況制造物物品,他們研究其品質(zhì)和意義以便他們的設(shè)計成為最具關(guān)懷性的物品。”
傳統(tǒng)設(shè)計由于生長于地方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該文化中的風俗習慣、審美風尚、道德和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在每一設(shè)計物品中都打下了其深深的烙印,該文化中的每一個體因此也都能夠在這種設(shè)計物品的使用和消費過程中自然而然地獲得豐盈鮮活的情感和價值體驗。生存的價值感和意義感正是在這種體驗中得以被確證和升華。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地方的傳統(tǒng)設(shè)計文化顯然已經(jīng)異常活躍地參與到了后工業(yè)時代主體文化身份的建構(gòu)過程中。這種建構(gòu)對于緩解工業(yè)時代人類生存價值感和意義感的消解而帶來的危機和焦慮無疑將起到別的文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更具體地考察,地方設(shè)計文化中的傳統(tǒng)技藝是一種典型的具身性知識,這種“具身”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這種技能并非現(xiàn)代化工業(yè)生產(chǎn)條件下機械化、精確化和標準化的操控模式,而是一種與人類身體高度融合的身體習慣和技能操控模式。其結(jié)果是,在產(chǎn)品設(shè)計和制作過程中,設(shè)計師的個性、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力都得到了極為鮮明、充分地體現(xiàn)。其二,這種技能的具身性還表現(xiàn)在特定文化中的審美習尚、道德倫理、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文化要素在產(chǎn)品設(shè)計過程中的大量融入。其結(jié)果是使得該文化中的個體更容易從對這些設(shè)計物品的使用和消費過程中獲得豐盈鮮活的審美和情感體驗,更能夠從中追尋到人類存在的價值感和意義感,從而最終獲得文化身份的認同和再建構(gòu),真正尋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回復到人類生存更為本真的生活世界。這種回復和追尋與人類當下高度發(fā)展的科學技術(shù)和生產(chǎn)工藝非但不相矛盾,我們反而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強有力的因素,服務于我們當下的設(shè)計實踐。在標明自身文化身份并從自身文化中尋找到認同感、歸屬感的同時,也尊重進而欣賞“他者文化”中的設(shè)計文化,從而強有力地促進和推動不同設(shè)計文化之間的深層次交流。
文化身份作為公民身份的一個重要維度,它是公民在參與到特定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等子系統(tǒng)的相互協(xié)作過程中逐步培育和建構(gòu)的結(jié)果,“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在生活世界中得到維護和培養(yǎng)”。從布迪厄社會學思想來看,在特定的地方設(shè)計文化中,傳統(tǒng)技藝是一種高度的具身性知識,在長期的設(shè)計、生產(chǎn)、使用和消費實踐中,這種具身性知識正是在特定場域中,文化資本及各個文化資本要素之間長期斗爭、協(xié)商和培育的結(jié)果,這種斗爭、協(xié)商和培育最終造就了該文化中每一個體獨特的習性。它攜帶著豐盈的地方性知識,它包括前文分析中所指出的特定地域文化中的審美習尚、道德倫理、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極為豐富的文化要素。與此同時,從新現(xiàn)象學創(chuàng)始人赫爾曼·施密茨的觀點來看,設(shè)計師和消費者習性在特定場域中,訴諸文化資本的斗爭、協(xié)商和培育的過程,也是主體身體經(jīng)濟學結(jié)構(gòu)和動力學特征的形成和模塑過程。設(shè)計物品以訴諸人類身體情感氛圍的方式,對主體身體的結(jié)構(gòu)和動力學特征進行干預和模塑。正是在這一干預和模塑過程中,特定文化中的審美習尚、道德倫理、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在主體和設(shè)計物品之間不停地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主體人格、群體文化(包括設(shè)計文化)正是在這種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中得以不斷培育和生成。沉浸于這一設(shè)計文化中的每一個體,也就自然都能從這種文化中尋找到有著堅實根基的人類存在的價值感和意義感。這也正是人類生存中最本真的生活世界。從這一層面上看,設(shè)計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充滿希望的人類未來發(fā)展的美好圖景。
魯?shù)婪颉·梅霍爾的《手藝中國:中國手工業(yè)調(diào)查圖錄》(圖5)就以令人嘆為觀止的嚴謹和求實精神,為我們展示了前工業(yè)時代中國自然經(jīng)濟語境中一幅設(shè)計文化的全景圖。書中對二十世紀早期仍活躍在中國大地的基本工具和農(nóng)業(yè)、交通、制衣、建筑、運輸?shù)裙ぞ呤聼o巨細的紀實性描述,不但能夠引發(fā)我們對于人與自然、資源、環(huán)境以及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深層次思考,而且透過這些描述,我們能夠深刻領(lǐng)悟到中國傳統(tǒng)技藝中所蘊藏著的中華民族深層次的、卓越的生存智慧。
可見,在地方設(shè)計文化的傳統(tǒng)技藝中,正蘊藏著使得人類擺脫當下危機的深層次智慧,那是人類生存中最為豐盈的價值感和意義感得以生長的沃土,這正是我們當下后工業(yè)時代設(shè)計文化中極為稀缺也最為迫切需要的。我們當下的設(shè)計文化,正應該在設(shè)計實踐中,努力追尋人類生存中更為根本的價值感和意義感,從而實現(xiàn)人類設(shè)計向生活世界的真正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