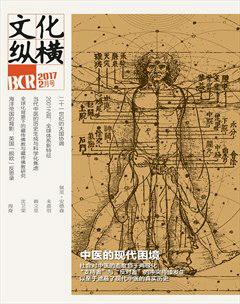中醫(yī)的現(xiàn)代困境
近年來,中國大陸興起一股“文化熱”和“國學熱”,作為中國傳統(tǒng)的重要載體,中醫(yī)文化也備受追捧,堂而皇之地進入各類“國學班”、“文化書院”之中。吊詭之處在于,中醫(yī)本身長期呈現(xiàn)“外熱內(nèi)冷”的發(fā)展態(tài)勢:1949年以來,中共高層在政策上一直支持中醫(yī)的發(fā)展;與之相對應,中醫(yī)行業(yè)的發(fā)展卻不盡如人意,在人才培養(yǎng)、行業(yè)規(guī)范和國家立法方面,都面臨重重障礙。不僅如此,社會對中醫(yī)的態(tài)度也趨于兩極化,“支持者”與“反對者”的沖突持續(xù)加劇,以至于遮蔽了現(xiàn)代中醫(yī)的真實面貌。
從疾病治療的角度看,中醫(yī)的現(xiàn)代之路,開始于近代中西醫(yī)的碰撞與匯通。正如皮國立的文章所言,這一歷程大概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1912年以前,基本上是中醫(yī)對西方生理解剖學知識的反思與響應;在此之后,則主要在細菌論、病理學和衛(wèi)生防疫等問題上展開論爭。在匯通與論爭的角力之中,西醫(yī)的理論與技術刺激了中醫(yī)學理的發(fā)展,促使近代中醫(yī)們?nèi)ニ伎肌⒄砉逃兄畬W術。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統(tǒng)一政權建立,現(xiàn)代中醫(yī)的體系最終形成。賴立里的文章指出,中共建政以后,成建制的院校、標準化的課本和制藥廠,種種現(xiàn)代醫(yī)學的必要體系設置,使得現(xiàn)代醫(yī)學的諸多要素逐漸滲透進中醫(yī)之中。特別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共陸續(xù)推行的“西(醫(yī))學中(醫(yī))”和赤腳醫(yī)生運動,對現(xiàn)代中醫(yī)的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前者加強了中醫(yī)在體制內(nèi)的地位,后者則進一步推動了中醫(yī)的普及。
然而,這一中醫(yī)體系基本是對西醫(yī)體系的模仿,為當前中醫(yī)的發(fā)展留下諸多隱患,肖相如以一個從業(yè)者的視角,指出當前的“科研”評價體系導致中醫(yī)發(fā)展的“虛假繁榮”,雖然中醫(yī)機構本身很繁榮,但中醫(yī)的實質卻所剩無幾。類似的問題也反映在中醫(yī)的海外傳播之上,張一凡的文章指出,雖然目前中醫(yī)藥已經(jīng)傳播到183個國家和地區(qū),但基本都停留在“個體戶式”的診所模式階段。在西醫(yī)科學體系迅猛發(fā)展之下,作為傳統(tǒng)醫(yī)學一部分的中醫(yī)藥在立法、標準制定、教學體系、職業(yè)系統(tǒng)和社會聲譽方面都處于邊緣位置。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現(xiàn)代中醫(yī)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呈現(xiàn)出某種悖論:一方面是當前中醫(yī)與中國文化關系的扭曲,肖相如認為,目前社會上泛文化的論調(diào)正將中醫(yī)引向虛玄、神秘,很多中醫(yī)不愿夯實醫(yī)學基礎知識,加強醫(yī)學基本功的訓練,而是將精力用在了相關玄學文化的學習上,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現(xiàn)代中醫(yī)的療效和聲譽日漸下降;而另一方面是中醫(yī)的發(fā)展亟需中國人重新理解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賴立里的文章強調(diào),“中醫(yī)立法會生產(chǎn)出很多騙子”的流行觀念,反映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依舊高度西化、科學化,也正因如此,“科學性”才會成為現(xiàn)代中醫(yī)的持久焦慮。發(fā)展中醫(yī),有必要在文化層面上對現(xiàn)代西方的科學主義有一個清醒的認知。
最后,本期封面選題的實現(xiàn)得益于上海證大集團戴志康先生的支持,在此謹向他致以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