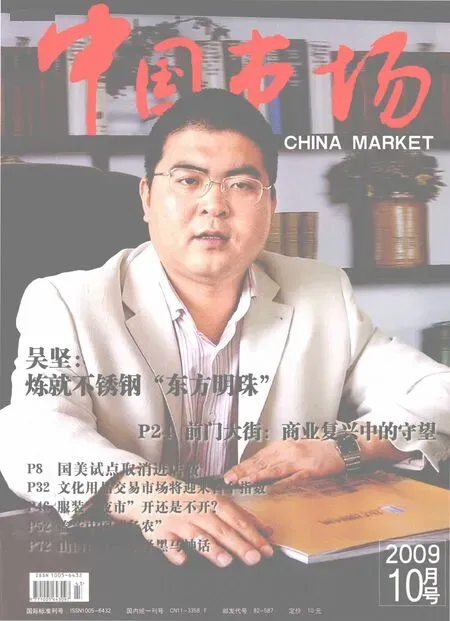論村兩委換屆選舉中弱勢群體的話語權
[摘要]我國村民自治制度確立多年,仍面臨政策實施的困境,弱勢群體話語權的缺失是其主要原因。分析其缺失的原因以及如何使弱勢群體話語權得到回歸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村民自治;弱勢群體;話語權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3201
我國村民自治制度最早提出于1982年《憲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2010年重新修訂的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明確規定我國村民委員會性質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突出強調其產生和管理方式是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它從法律角度確認了村民委員會性質和發揮的作用。農村法治建設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題中之意,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環節。村民委員會依法進行換屆選舉,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民主權利的直接行使,也有利于推進我國農村民主法治建設。然而,我國村民自治制度確立多年,仍面臨政策實施的困境。以鄉村社會治理為代表的我國基層民主協商之路,也亟待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摸索、前行。
1我國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困境
我國村民自治制度的現實困境是:①制度上,我國農村分布廣、條件各異,村民客觀生活環境決定了制度或法律的可操作性必須要貼近農村現狀。村民自治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很難完全滿足各種現實狀況的需求,還有基層村民委員會自身缺乏應有的監督體制。②經濟條件上,農村落后的經濟條件,迫使年輕的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留守的老人、婦女、兒童無法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村民委員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需要村民自己出錢作為經費支持,才能維持正常的公務辦理,經濟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③思想意識上,傳統的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思維方式,使村民對于民主一詞格外陌生,村民并不關注公共事業的發展。又由于地理環境閉塞和地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村民的民主意識有很大局限性。
每三年一次的村“兩委”換屆選舉,是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基層民主政治的主要實現途徑。然而,現存的“鄉政村治”格局即鄉鎮政府的行政管理權和農村的村民自治權,由于村民自治是在國家政權強力推進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就容易導致村民自治的行政化傾向。還有在小農思想作用下,農村根深蒂固的血緣、家族觀念所導致的村民自治權被牢牢地掌握在極少數宗族勢力、鄉村精英(農民企業家等)和村干部手中。以大學生村官、婦女、外出務工人員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在村委換屆選舉中的話語權嚴重缺失。
2弱勢群體話語權缺失的原因
話語權從政治術語上講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以言語形式進行的權力擴展[1]。從制度的角度來講,農民話語權是指農民政治權利和民主意識的集中表達,包括農民的信息知情權、發展決策權、管理參與權、分配監督權和平等訴求權等[2]。從新聞學視角來看,話語權是指公民運用媒體對其關心的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及各種社會現象提出建議和發表意見的權利,是公民的一項不可讓與和不可剝奪的民主權利[3]。
關于弱勢群體話語權缺失原因的探究,學者主要從內因和外因的角度來分析。從內因的角度來講: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導致其失去說話的陣地,無法使信息集中凝聚,在與其他利益集團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由于經濟地位和文化素質導致農民整體素質偏低,限制了其行使話語權的能力。從外因的角度來講:渠道方面,信息傳輸渠道不暢,造成農民話語運載困難,包括農民利益表達時遭到基層干部的漠視、拖延,媒體在農村信息傳播的缺位[4];制度方面,農民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的缺位和現行的各種制度對農民權利保護的缺失[5]。以農民為代表的弱勢群體話語權缺失的原因,不能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的探討,更應從現實角度挖掘其自身的不足之處。
首先,普通村民民主意識薄弱,參與能力有限。一方面,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君君臣臣”的傳統禮教束縛,導致村民的民主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現代化進程中,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城市,更多地考慮經濟上的收益,剩下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根本沒有參與競爭的意識和能力。
其次,強勢群體勢力強大。宗族家族中的長輩威信較高,地位不容置疑;鄉村精英通常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如農民企業家,來爭取村委權力,以便政商聯合,獲取更大經濟效益。原村干部與鄉鎮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系,擁有更便利的獲得完整信息的渠道,也可以在程序上“左右”選舉結果。
最后,鄉鎮政府在信息傳達和組織監督上的行政化傾向。鄉鎮政府充當著“把關人”的角色,在選舉信息的上傳下達中麻痹弱勢群體和上層領導,以實現其控制力。組織傳播中的“末梢”現象,也使原有政策精神在逐級傳播的過程中內容遞減,或僅在少數領導干部中小范圍公開,在“擬態環境”中使弱勢群體喪失平等競爭的機會。
3弱勢群體話語權的回歸
政治上的賦權有利于鈍化邊緣群體的政治意識,使他們認同現存體制,實現邊緣群體的政治一體化,從而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運轉[6]。因而,弱勢群體話語權的回歸顯得至關重要。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目標的大背景下,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使弱勢群體話語權得到回歸,需從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改革現有的鄉村治理體制,建立新型法治的鄉村治理、管理體系。農村治理中的重大決策都要于法有據。分清治理和管理的界限,管理為鄉村治理提供服務和公共資源,而依法自治立足于農村自有文化,避免行政化傾向。激發村民組織化意識。長期以來,鄉鎮政府包辦農民之事,使農民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而村民自治要求村民自發形成自我管理、民主選舉的意識。
第二,培養和輸入新型鄉村治理人才。農村帶頭人要來自于農村,又高于農村,即農民子弟大學生的培養和輸入。高校要有意識加強農業技術推廣和鄉村治理方向的人才培養。政府應用優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吸引農村出去的大學生反哺農村建設。現實中的村干部普遍老化、知識素質不高,而新到的大學生又有可能專業不對口,無法真正發揮作用,造成人才的浪費。另外,提高大學生“村官”的待遇,打通其上升渠道,才能使鄉村治理源源不斷地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建立鄉村治理者權利與義務、職責與薪酬對等的行政和勞動管理體制,以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發村民自治的原動力,避免村干部腐敗和宗族勢力壟斷。加強農業現代化建設,招商引資,提高經濟實力。利用高新技術手段和市場信息,建立有共同利益機制的村民合作組織,提高經濟效益。同時通過各種培訓和宣傳,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增強對合作社的認識,使村民真正參與進來,充分發揮農民自身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共同致富。
4結論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突破口,或許就在于大學生“村官”的科學化引入。同步推進城鄉法治建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做好“三農”工作,都急需既懂法又能深入了解農村實際情況的專業化鄉村治理人才的出現。只有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才能使廣大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展進程、共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
參考文獻:
[1]李軍,朱新山“翻譯者”模式和村治實踐[J].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05(3):88
[2]厲有國我國農民話語權缺失的制度因素審思[J].天府新論,2009(2):98
[3]鐘云萍論我國農民權益保障的缺失——以農民的話語權為視角[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5)
[4]倪新兵農民話語權缺失:信息傳播維度解析[J].青島農業大學學報,2007(19):4
[5]譚志奇,廖順余,冼平芳我國農民話語權缺失的原因及對策[J].安徽農業科學,2008(9)
[6]王可園,齊衛平政治賦權與政治一體化:1832年英國選舉權擴大的政治分析[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5(10)
[作者簡介]段飛飛(1989—),女,河南三門峽人,遵義醫學院人文社科學院研究生,就職于三門峽市陜州區硤石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