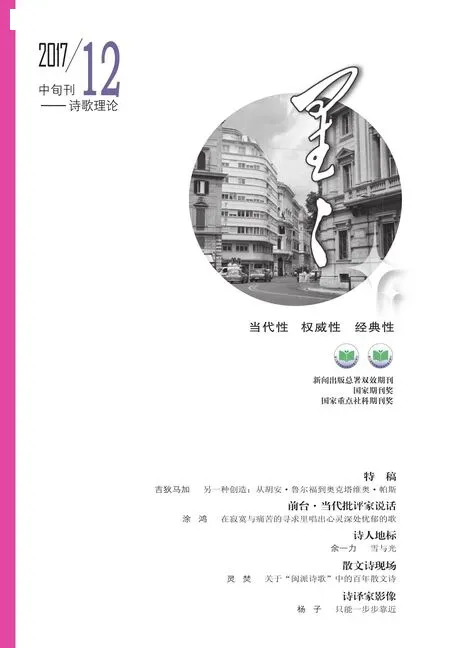在“野外”抒情
郭 靜
民歌與謠曲可算是詩歌最早的前身,中國自古便有其根源。以《詩經(jīng)》整體的思想性和藝術(shù)價(jià)值來看,“三頌”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國風(fēng)”,“風(fēng)”即是天然樸素回蕩著自由之聲的地方民歌。民歌傳統(tǒng)的傳承不是偶然,因?yàn)樵姼枵嬲暮诵模肋h(yuǎn)是對(duì)真實(shí)自我的不斷追尋和對(duì)自由的本能渴求。當(dāng)代詩歌這種民歌式吟詠,與《詩經(jīng)》國風(fēng)之不同在于,其書寫往往不以詩歌意象與內(nèi)涵的密度取勝,也不以日常農(nóng)耕生活場(chǎng)景為背景,而是以“野外”的空闊自由和在寂寥空間中人與人之間可能存在的更為親密的關(guān)系為主題,展現(xiàn)出了當(dāng)下詩人對(duì)自由精神的向往,以及在城市擁擠與焦慮情緒壓迫下,逃離冷漠與束縛的潛在訴求,是詩人從傳統(tǒng)詩酒文化和“野外”空間汲取慰藉的表現(xiàn)。本期推薦的三首短詩,均以“小”為題,字里行間有著謠曲般的哀怨悠揚(yáng),內(nèi)容上,以抽離日常的場(chǎng)域?yàn)楸尘埃蚴敲C2菰蚴谴阂吧街校只蚴秋L(fēng)中的鄉(xiāng)土,可說是表現(xiàn)了詩人對(duì)“野外”的鐘情,對(duì)遠(yuǎn)方的渴望。
《小黃馬》是一曲草原上的哀歌,是一位游牧少女在落日下蒙古包旁哼唱的民謠。小黃馬的悲傷似琴聲般悠揚(yáng)哀婉,斷斷續(xù)續(xù)響在草原上空。小黃馬的悲傷源于母親的死亡,也源于要承襲母親的一生最終也死在草原上。它的悲傷無以形容,詩人卻用幾乎重復(fù)的六句詩表達(dá)了出來。失去母親的“小黃馬”這一意象并無特別之處,但因?yàn)槊晒挪菰膶挄鐭o邊和牧民長日寂寥的生活背景烘托,在詩人的反復(fù)吟唱中顯現(xiàn)出更耐人尋味的意境。這種淡淡的彌散在整個(gè)草原上的憂傷,與荒野中生命不斷逝去又新生、循環(huán)往復(fù)的亙古哀愁,使這首短小的謠曲,在被日常生活壓抑的人心中激蕩起一種遠(yuǎn)古的綿長憂郁和對(duì)流浪生活的無盡想象。
《小謠曲》一詩的語言有著古詩的內(nèi)核和質(zhì)感,傳統(tǒng)詩歌意象充盈其間。春深,酒濃,天藍(lán),風(fēng)暖,月西沉,伊人淺笑,孤獨(dú)遺世,南方之地,時(shí)間走得緩慢。這樣小小的美好,小小的溫暖,小小的感動(dòng),看似稀松平常,放在當(dāng)下細(xì)細(xì)想來卻是難得。“亂石耽于山中”一句為詩眼,隱逸的情懷涌動(dòng)在整首詩中。小謠曲更是小夜曲,詩人清唱種種美妙的事物,比如藍(lán)得恰到好處的天色,這一切都只有在“山中”才可得,只有遠(yuǎn)離世俗才能體會(huì),只有在“野外”、在飲酒的夜晚才能忘我和陶醉。這響在深夜中的謠曲令人靈魂安定,心緒平和。
與《大風(fēng)歌》雄渾灑脫的高歌相反,《小風(fēng)歌》溫軟哀怨,詩人在風(fēng)中低聲訴說著年輕時(shí)羈旅他鄉(xiāng)的憂愁。時(shí)間流逝,生命逝去,世間的事物皆如此。而風(fēng)就像是一位見證者和撫平萬物痕跡的整理者,使塵歸塵土歸土,使萬物顯現(xiàn)本質(zhì)。曾經(jīng)隨風(fēng)遠(yuǎn)行,瀟灑爛漫,流浪的人終于在故土沉睡,風(fēng)又來吹拂。而“我”已不再想遠(yuǎn)行,只愿長眠故鄉(xiāng),與風(fēng)訴說滄桑。流浪與歸鄉(xiāng),生命的逝去與虛無,是這首詩引人入勝的地方,輕聲低吟的語句中有著生命不能承受之憂愁。
某種程度上必須承認(rèn),這些詩歌中流露出的古典的流浪和憂郁氣質(zhì)使被城市與日常逼仄空間禁錮的人從中獲得活力,只有在“野外”,一種詩意的情緒才可能出現(xiàn),曾經(jīng)在農(nóng)耕和游牧人們之間存在的親密關(guān)系才可能被期望。而城市化的當(dāng)下居住空間,則充滿人性的冷漠,忙碌使人們無暇靠近真實(shí)自我,內(nèi)心的聲音和掙脫禁錮的念頭也往往只是在腦中一閃而過,只有敏感多愁的詩人才會(huì)在擁擠的城市一隅,以詩歌抵達(dá)遠(yuǎn)方和心靈的遼遠(yuǎn)寧靜。卡爾·克勞斯曾說:“不是被愛者在千里之外,而是這距離本身被愛。”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理解,當(dāng)下詩人對(duì)“野外”的鐘情,不是真的希望回歸原始的生活方式,而是想與日常逼仄生存境遇保持一種距離,并期待從遠(yuǎn)離日常的所在之處找到溫暖的寄托和憂郁的空閑。
我們不能否定這種謠曲抒情的真實(shí)性,但對(duì)這種情感的書寫與感知,卻應(yīng)保持經(jīng)常性的自審和叩問,警惕一種虛無的逃避的趨向,警惕一種表面化概念化的“遠(yuǎn)方”與缺乏內(nèi)在能指的“傳統(tǒng)詩性”。自由不是詞語的遠(yuǎn)走高飛,關(guān)于行走的力量、人性的溫暖、真實(shí)自我的表達(dá),才是民歌傳統(tǒng)、“詩酒”文化的精神內(nèi)核。或許抱著這樣的態(tài)度,當(dāng)下新詩的謠曲書寫才能更內(nèi)在更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