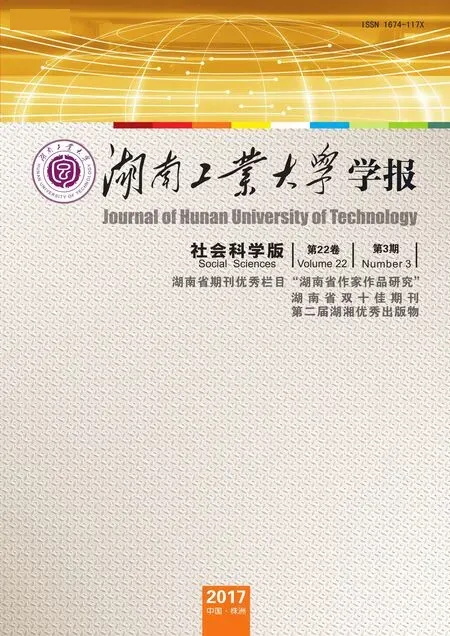論“人類命運共同體”對“霸權”與“均勢”的超越
張永紅,殷文貴
(湖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論“人類命運共同體”對“霸權”與“均勢”的超越
張永紅,殷文貴
(湖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霸權主義和均勢體系在國際秩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霸權主義滋生的五大均勢體系給人類社會造成了深重災難。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超越“霸權”與“均勢”的新型國際秩序觀:汲取了歷史上霸權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經驗教訓,是一種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新型權力觀;順應當今世界發展與變革潮流的客觀要求,是一種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型利益觀;深深扎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是一種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新型文明觀。
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霸權主義;均勢體系;新型國際秩序觀
縱觀世界歷史發展的長河,人類社會似乎總是跳不出“霸權”與“均勢”相互交織的陷阱,特別是近代歐洲30年戰爭確立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后,國際關系一再陷入“霸權-均勢-霸權”的怪圈。時至今日,盡管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旋律,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在國際關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給國際秩序的變革與調整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天下為己任,汲取人類歷史的經驗教訓,立足國際社會相互依存的大勢,提出并不斷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牢牢占據了國際秩序重塑的制高點,為超越“霸權”與“均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一 霸權主義:均勢體系產生的根源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認為:“國家間的政治無非就是強權政治,爭奪權力、增加權力和炫耀權力是國際關系的常態。”[1]縱觀500年的近代世界歷史,“強權即真理”成為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的通用法則,國家間的戰爭與革命占據了國際秩序的主流。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人類戰爭史。然而,戰爭過后,各國往往以會議和條約的形式建立短暫的均勢體系(即國際體系或國際秩序),“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俾斯麥大陸同盟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就是這種均勢體系的典型。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各國交往日趨密切,全球化進程逐步加快,由此開啟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爭奪霸權的需要,世界各國發生過許多戰爭,簽署過許多條約,并形成過幾個相對大的均勢體系,但真正稱得上世界范圍內的均勢體系始于歐洲30年戰爭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618—1648年,為了爭奪歐洲霸權,以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為首的天主教同盟和以德意志新教諸侯為首的新教同盟,打著宗教的旗號,進行了長達30年的戰爭,最終戰爭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的簽署而宣告結束。這個合約的簽署,標志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該體系開創了以國際談判和國際會議的形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即當一方(一國或多國)認為其已經比另一方強大之時,便用武力的手段加以侵略,而一旦在侵略過程中力不能及或失敗之后,他們又會以國際會議、國際協商并通過締結和約的方式重新調整關系,形成新的均勢體系,以保存自身實力。對此,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表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普遍意義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價值觀上是中立的。它的規則適用于任何國家:不干涉他國內部事務,邊界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享有主權,鼓勵遵守國際法。”[2]相比中世紀而言,這一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的確有很大進步,它被視為歐洲近代國際公法的基礎,開創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和以主權平等為原則的國際新秩序。
遺憾的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確立,并未阻止戰爭的爆發。在實際的國際較量中,強國依舊憑借自身的優勢和實力欺辱弱國,不過在做法上往往是在局部戰爭后以國際條約的形式來調整國家間的關系。100多年后,此消彼長的力量對比和連續不斷的戰亂終于使“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維也納體系”。19世紀初,拿破侖為了稱霸歐洲連續發動多次戰爭,但遭到了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的強烈反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進一步加強了歐洲國家的主權觀念和民族主義意識,并且各國也諳熟了以條約形式來調整國家間關系的做法,于是最終反法同盟同法國簽訂了結束戰爭的“維也納和約”,建立了一種新的歐洲均勢體系——維也納體系。該體系是僅次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第二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國際體系,但在維持幾十年后又被歐洲革命風暴沖垮了。不過,五強爭霸(英國、法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的格局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雖然1871年德國統一后的俾斯麥一度建立了一個以德國為軸心的新的歐洲國際秩序“俾斯麥大陸同盟體系”,但基本上是曇花一現。20世紀初,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向帝國主義過渡,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一戰后,美國成了國際政治中的主角,其聯合英國、法國、日本等國通過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構筑了著名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這個體系本質上是帝國主義之間分贓的產物,而分贓不均最終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隱患。二戰后,以美國、英國、蘇聯為首的戰勝國依照戰時藍圖設計了“雅爾塔體系”。但好景不長,驟然而至的“冷戰風云”很快就驅散了“雅爾塔體系”的慘淡陽光,此后美蘇兩家的冷戰成了國際關系的主旋律。1991年蘇聯解體后,“雅爾塔體系”亦逐步解體,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并依靠其獨一無二的超強實力不遺余力地推行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一直持續至今。
二 均勢體系:人類共同的悲哀
在某種程度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俾斯麥大陸同盟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等均勢體系對于減少戰爭傷亡、緩和國際局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不能忽視的是,這些均勢體系本身就是戰爭的結果,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產物,其蘊含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無疑加劇了受剝削國與戰敗國的仇恨,成為了下一次戰爭爆發的導火線。因此,相較于數次戰爭給各國人民帶來的災難,這些體系的作用可謂微不足道。據不完全統計,僅30年戰爭就導致超過800萬神圣羅馬帝國人死亡,占帝國總人數的1/3;歐洲的300多座城市、2 000多座村莊在戰爭中毀于一旦,無數的礦區、寺院、工廠變成了一片片廢墟。德國詩人馬丁·歐佩茨將此描述為:“樹木不再站立,花園變得荒涼,而鐮刀與犁現在卻變成了冰冷鋒利的劍。”此外,戰爭的深重創傷和戰后的分裂局面,致使德意志經濟急劇衰退,死灰復燃的農奴制使農民受到更加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德意志民族的強者風采在很長時期內不復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說:“三十年戰爭的嚴重后果,使德意志有200年不見于政治積極的歐洲國家之列。”然而,比30年戰爭更為嚴重的是兩次世界大戰。據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全球15億人卷入戰爭,戰爭傷亡人數超過3 000萬,損失經濟3 400多億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遍及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使全球17億人卷入戰爭,戰爭傷亡人數多達1億(僅中國就傷亡人數超過3 500萬),損失經濟40 000億美元,給人類社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世界很快分化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雅爾塔體系”也逐漸被冷戰秩序所取代,人民再次陷入了危機與戰爭的深淵。第一次柏林危機,蘇聯對柏林長達324天的“交通管制”全面切斷了西柏林的水路交通,導致國際形勢驟然緊張起來,同時加速了德國的分裂和北約組織的成立。朝鮮戰爭,美國公然利用聯合國的名義取得53個國家提供的“道義”援助,并糾集15個國家的兵力組建了所謂的“聯合國軍”,致使世界主要國家陷入了戰爭的泥潭。長達20年的越南戰爭,不僅給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而且使美國深陷經濟困境與政治危機。作為越戰決策人之一的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曾一度認為在亞洲反對共產主義是值得的,但是經過近30年的沉默與反思后,他不得不坦白:“我根據我的判斷,事后證明我們錯了。我們過高估計了失去越南對西方安全的影響。”[3]而美國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越南戰爭是美國過去歷史上最悲慘的一章。”[3]除此之外,差點將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古巴導彈危機,蘇聯對阿富汗長達10年的侵略,美國對格林納達的入侵等,無不是冷戰秩序中美蘇爭霸的惡果。
如果說冷戰前的國際格局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是赤裸裸的傳統安全威脅,那么冷戰后美國一家獨大的格局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的則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并存的困境。就傳統安全而言,從攻打南聯盟到入侵伊拉克,從捉拿薩達姆到消滅卡扎菲,再到今天北約與俄羅斯軍事沖突的不斷升級,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作風可謂暴露無遺。盡管隨著中國、俄羅斯、歐盟等的崛起,美國在稱霸世界的道路上一再受挫,但強大的綜合國力仍然使其在當前“一超多強”的國際秩序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從非傳統安全來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國際問題的凸顯與國際秩序的“失序”,不論是反恐聯盟在打擊“伊斯蘭國”恐怖主義上的力不從心,還是六方會談在解決朝核問題、伊核問題上遇到的重重阻礙,抑或世界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傳染病擴散等問題上所產生的矛盾分歧,如此等等,說明了美國主導的后冷戰秩序不僅沒有起到“領頭羊”的作用,反而在全球治理中制造出越來越多的矛盾與沖突。當然,辯證地看,冷戰后的國際秩序確實比之前所有的國際秩序都要好,因為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組織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二戰后正義一方的勝利成果,并且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使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從中收益。但是,作為有“良知”和“善念”的人類,我們決不能因為“霸權”和“均勢”給各國帶來一定的好處就忽視它給人類所帶來的血淋淋的傷亡現實。譬如,當前“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北非引起愈發激烈的區域動蕩、北約與俄羅斯沖持續不斷的地緣政治博弈、“伊斯蘭國”恐怖主義的大肆蔓延等,這些與霸權主義有密切關系的國際問題,無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總之,在均勢體系支配的國際秩序下,只會滋生戰亂與沖突,人類只能生活在一個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共同體”內,而沒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有的只是沖突、戰爭、蕭條、無序、悲憫、失落。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奉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篤信窮兵黷武、強權獨霸,堅持贏者通吃、零和博弈,這種國與國相處之道不僅不能解決世界上的問題,反而是制造沖突和戰爭的根源。”[4]
三 “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霸權”與“均勢”的新型國際秩序觀
歷史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塑造。面對世界近代以來“霸權”與“均勢”反復交替的國際秩序,如何超越這種要么“霸權”要么“均勢”的循環怪圈,是擺在當前國際關系領域的重大課題。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深邃寬廣的歷史視野和統籌全局的戰略思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型國際秩序觀,汲取霸權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經驗教訓,順應當今世界發展與變革潮流的客觀要求,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新型權力觀,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型利益觀,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新型文明觀。
1.“人類命運共同體”汲取了歷史上霸權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經驗教訓,是一種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新型權力觀。馬克思指出:“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5]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侵略擴張史,而中國就是這部殘酷歷史的主要受害者之一。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來,中華民族受到帝國主義長達百年之久的侵略和奴役,中國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蹂躪和屈辱,一度瀕臨亡國滅種的境地。僅14年的抗日戰爭,中國就犧牲了3 500多萬炎黃子孫,而且造成了難以計數的經濟財產損失,中國社會發展倒退了數十年。經歷百年苦難的中國人民深知和平的來之不易,所以更懂得國與國之間相互尊重與平等相待的重要性。基于此,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呼吁:“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偏見和歧視、仇恨和戰爭,只會帶來災難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處……才是人間正道。”[6]其中的“相互尊重、平等相處”就表明:在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秩序中,“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主權和尊嚴必須得到尊重,內政不容干涉,都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7]。因而“各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只能由本國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8],不能以“世界政府”和“國際警察”的身份隨意干涉他國內部事務,不能隨意將本國的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強加給別國。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所闡釋的那樣:“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9]由此可見,與過去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侵略擴張的霸權行徑實現“大國崛起”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完全摒棄了傳統帝國主義的權力政治觀,是一種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新型權力觀,因而不愿意也不可能重走“霸權”與“均勢”的老路,完全能夠跨越大國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
2.“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當今世界發展與變革潮流的客觀要求,是一種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型利益觀。“霸權”與“均勢”的慘痛教訓時刻警醒著世人:“和平而不是戰爭,合作而不是對抗,共贏而不是零和,才是人類社會和平、進步、發展的永恒主題。”[10]正如學者陳若松所說:“歷史昭示我們,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無法帶來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兩極分化,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愿望和期盼。”[11]在當今世界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關鍵時期,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顯得更為緊迫和必要。自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以來,美蘇兩級格局最終瓦解,并向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方向演進。21世紀以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得以深入發展,同時隨著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持續推進,人類社會真正進入了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歷史”中的全球性時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交融格局。在此格局下,“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和平力量的上升遠遠超過戰爭因素的增長,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7]。但與此同時,傳統問題與非傳統問題交織的局面使得各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挑戰。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仍處于變革調整期,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二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陰魂不散,美俄地緣政治博弈愈演愈烈,中東北非亂局一發不可收拾,冷戰秩序所導致的陰影正日逐漸擴大;三是全球恐怖主義牽動全球神經,伊核、朝核問題談判相持不下,氣候變化、難民危機、網絡安全、貧困問題、傳染病擴散等全球性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深刻復雜的全球性難題相互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給人類的未來帶來重重挑戰。
全球性問題呼喚全球性的治理方案。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演講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7]在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際問題面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更不能憑借一己之力去克服國際難題,必須相互合作、相互依賴、同舟共濟、權責共擔。不能“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更不能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把本國的幸福建立在別國的痛苦之上。二戰前夕,英國、法國、美國為求得一時茍安,公然無視德國、日本等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行徑,一再實行所謂的“綏靖政策”,最終招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2003年,美英聯軍為了防范和打擊恐怖主義,公然繞開聯合國安理會,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伊拉克發動了長達7年之久的戰爭,給伊拉克人民造成了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的同時,也為今天“伊斯蘭國”恐怖主義的猖獗埋下了禍根。由此可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不論是因為一己私利對別國錯誤行為的姑息縱容,還是因為強權獨霸隨意干涉侵略他國,最終傷害的不僅僅是自己,而是包含“命運共同體”內的所有國家。因此,各國唯有順應世界發展與變革潮流的客觀要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方能超越“霸權”與“均勢”相互交織的國際舊秩序,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3.“人類命運共同體”深深扎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是一種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新型文明觀。毋庸諱言,現代文明起源于數百年前歐洲歷史上的一場持續200余年的文藝復興運動,它使“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帶領西歐邁出了中世紀的蒙昧與黑暗,吹響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進軍的號角,造就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然而,這種繁榮的背后往往是圈占土地、販賣人口、奴役他人、武力擴張、建立殖民地等,并且在實現過程中催生了霸權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一方面,由于爭奪地區霸權的需要,各國競相角逐、爾虞我詐,導致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的爆發,給人類文明打上了一層不可磨滅的陰影;另一方面,霸權和戰爭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仇恨,一些國家逐漸形成了唯我獨尊的心態,進而導致極端民族主義的滋生(如希特勒的“種族優越論”、日本的“拯救論”、俄國的“沙文主義”)。可見,文藝復興在開啟人類文明曙光的同時,又建構了傳統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延續到今天就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所主導的國際體系,而這個體系不但未能使人類得以解放,反而打破了阿拉伯世界脆弱的地緣政治平衡,引爆了中東種族和宗教的火藥桶,加劇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大肆蔓延。這就是當代西方的文明,一種建立在霸權、戰爭、沖突基礎上的文明。為此,有學者指出:“人類文明的交匯已經走到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人類危機呼喚人本主義在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的繼承和發揚,呼喚一場新的文明復興。”[12]“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縮影,內含多樣、包容、共存、和諧等新型文明理念,無疑是這場“新的文明復興”的開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邦者下流”,這是中華民族以天下為己任、海納百川的胸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中華民族敦厚平和、推己及人的待人原則;“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這是中華民族求同存異、兼容并包的處事之道;“和衷共濟”“兼濟天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等,這些體現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中形成和傳承下來的文明理念早已流淌進了中華兒女的身體,融入了炎黃子孫的血液,成為了中華民族不可變更的文化基因。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講話中就明確表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人類歷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融合的宏偉畫卷”。[13]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時再一次指出:“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不同文明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7]由此可知,“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的既非過去帝國主義通過侵略戰爭而征服四方的榮耀,也不是由于實力懸殊而暫時通過條約維持短暫和平的陰謀。它超越國家、地區、民族以及宗教之間的隔閡、沖突與紛爭,是一種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新型文明觀,也是一種超越“文明沖突論”和“歷史終結論”的新型國際秩序觀。
當今世界,超越“霸權”與“均勢”,追求和平與發展,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要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就必須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型國際秩序觀,超越殖民擴張、冷戰思維、霸權政治與零和博弈,使身體和腦袋同時邁入21世紀。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9]
[1] 趙可金.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公共外交的方向[J].公共外交,2016(4):5.
[2]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胡利平,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75.
[3] 梁志明.越南戰爭:歷史評述與啟示:越南抗美戰爭30周年勝利紀念[J].東南亞研究,2005(6):14.
[4] 王 恬,牟宗琮,張夢旭.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習近平總書記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創新外交理念與實踐述評[N].人民日報,2016-01-27(01).
[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6] 佚 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在京隆重舉行[N].人民日報,2015-09-04(01).
[7] 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7-01-20(02).
[8] 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03-25(02).
[9]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7-02(02).
[10] 佚 名.習近平在俄羅斯媒體發表署名文章《銘記歷史,開創未來》[N].人民日報,2015-05-08(01).
[11] 陳若松.科學發展觀的價值訴求[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5:262.
[12] 葉小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共識[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7(3):3.
[13] 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9-29(02).
責任編輯:徐海燕
Transcendence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all Mankind” over “Hegemony” and “Equilibrium”
ZHANG Yonghong, YIN Wengui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Since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hegemonism and equilibrium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particular, the five equilibrium systems nursed by hegemonism have caused great catastrophe to human society. As a new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dvoca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ranscends “hegemony” and “equilibrium”. Firstly, drawing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the disasters of hegemonism in history, it is a new view of power featuring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 Secondly, conforming t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world today, it is a new concept of win-win cooperation and mutual development. Thirdly, deeply rooted in the soil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a new civilization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Xi Jinping;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hegemonism; equilibrium system; new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3.014
2017-02-26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習近平總書記綠色發展思想研究” (16YBA128);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重點項目“習近平綠色發展思想視域下的綠色責任擔當研究”(17A058);湖南工業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研究”(CX1608)
張永紅(1972-),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工業大學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化、休閑文化研究;殷文貴(1991-),男,云南曲靖人,湖南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D0-02
A
1674-117X(2017)03-007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