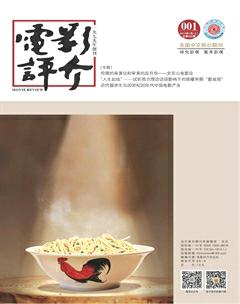國產微電影的敘事學分析
楊慧
網絡時代與移動計算時代的到來,為微電影的超速發展,提供了傳播驅動與移動分眾的不可或缺的堅實的物質基礎。微電影作為一種微創作、微制作、微傳播的影視藝術產品,更貼近于后現代生活,因此,其更具備后現代新敘事特質。微電影的這種后現代新敘事特質,既是創作者意志的一種意象化圖景,又是現實生活藝術化的一種擬真意象化呈現。微電影的現實源泉,也因此而遠比其他影視藝術形式都來得更加充沛順暢。同時,微電影的微門檻也使得微電影作品尤其是佳作得以大量涌現。針對微電影進行敘事學分析,不僅能夠對后現代微電影的發展進行更加深入的藝術解構與藝術思考,而且亦能夠對微電影的未來發展提供一點理論支撐與理論參照。
一、 微電影的后現代新敘事藝術特質分析
(一)后現代新敘事特征
客觀而言,微電影的出現既有賴于傳播條件的無極化改善,更有賴于移動計算的應運出現,正是二者的深度融合,才使得微電影的時代如浪潮般勢不可擋。由此可見,微電影的誕生,從其本質上而言,顯然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科技發展的必然。[1]敘事起源于人類對自身生產生活體驗的反映,微電影因其微敘事而呈現出了獨特的后現代新敘事特征,這些特征首先即是微觀眾最喜聞樂見的幾種特征,即針對微事件的紀實敘事、針對微事件的惡搞敘事、純搞笑式敘事。這幾種后現代新敘事特征中,尤以純搞笑式敘事的微電影傳播最速。其次,微電影敘事的最主要特征還包括強高潮與短鋪墊,由于微電影的時長普遍較短,因此,短鋪墊更考驗微電影敘事的擬真能力、演繹能力、快速沉浸能力。[2]最后,微電影敘事還存在著后現代新敘事主導的較多近景甚至特寫敘事的特征,同時,微電影更注重于懸念式敘事與反轉式敘事。
(二)后現代新敘事角度
從普遍的影視藝術視角而言,敘事具有非同一般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恰恰緣于敘事方案的不可窮盡性,敘事方案的幾乎不可窮盡性,既為影視藝術提供了更大的光影操縱藝術空間,同時又為微電影提供了更大的光影藝術發揮空間。在國產微電影中,我們不僅看到了針對微電影的敘事者所進行的變換式藝術發揮,亦經常看到微電影中的敘事視角的變換式發揮,同時,具體到敘事視點,微電影的視點密集性與緊湊性也給微電影創作帶來了敘事時空調度與敘事節奏調度的高強度發揮性。從社會學視角而言,微電影敘事角度中的人物選取亦具有更貼近生活性,這樣的敘事角度選取可為一石二鳥,因其不僅能夠更易快速引發觀眾的普遍心理親近感,同時,亦更易快速引發觀眾對劇中人物產生情感上的強烈共鳴感。
(三)后現代新敘事時空特質分析
眾所周知,影視藝術是一門操縱時空表現形式的藝術,因此,其對于敘事學研究而言,時空特質是影視藝術之中舉足輕重的關鍵。而微電影則由于其微特征,而使得其在后現代新敘事的規訓之下,其時空特質具有較為普遍的弱共和性與強歷時性,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特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微電影的時空布局不可能具備大電影的大縱深,此外微電影也不可能具備大電影的大過度式的宏大的場景,更不可能具備數以百計乃至數千計的影職人員,也不可能進行變幻莫測的劇情復雜性。因此,微電影的時空設計有其微敘事的特殊的架構支撐。
例如,在后現代新敘事技法中較為常見的敘事反轉技法,即是一種典型的微電影敘事時空特質,這種反轉性時空特質能夠為觀眾帶來更大刺激感與震撼感,且更易產生具強烈沖擊力的歐亨利式效應。而這種歐亨利式效應的敘事建構,重在刻意地以詭敘人為地為觀眾制造意識盲點與潛意識陷阱,并由此對淺沉浸狀態中的觀眾“反戈一擊”。
二、 微電影的敘事學基本分析
(一)后現代新敘事模式
針對微電影的后現代新敘事特質的認真分析可見,在微電影的極速發展表象的掩蓋之下,我們已然看到了微電影的發展困境,微電影的這種發展困境首先與其創作本體有著直接的關系,其次,微電影的這種發展困境亦與其“微”不無關聯。由此可見,囿于微電影的客觀條件,微電影在敘事不斷嬗變的過程中,呈現出了一種與后現代敘事不完全相符的較為單一的敘事模式,這種較為單一的敘事模式顯然極大地弱化了微電影的微言大義,同時,也極大地弱化了微電影的陌生化的敘事性。通過針對大量微電影的觀察可見,微電影的后現代新敘事模式存在著一種“敘事引述-敘事沖突-敘事沖突完結-敘事終結”這樣的單線弱張力模式,這樣的敘事模式不僅使得微電影的藝術性大幅降低,而且亦使得其可觀賞性也同時隨之降低,并且其視覺震撼力與視覺沖擊力更會等而下之。可見,鼓勵微電影創作者探索且創新敘事模式勢在必行。
(二)后現代新敘事參照
深入研究微電影敘事的一個必備的功課,就是必須對微電影的敘事構造,及其內部活動加以解構,愛森斯坦在這方面為微電影提供了基于敘事符號學原理的經典范例。而從另一視角而言,愛森斯坦的時空分割與交錯融合,人為地增加了戲劇的解釋難度,因此,巴贊為微電影規訓了一條“現實漸近線”,這條“現實漸近線”顯然對于微電影的后現代新敘事至關重要。國產微電影在理論方面的弱化顯然源于對敘事理論理解的模糊,在這一點上,麥茨及其敘事學理論為國產微電影指明了一種敘事復雜化的發展方向。同時,布努埃爾更以其“自由幻影”為微電影敘事展現了更多的偶然性與意外性等陌生化敘事選項。對國產現代微電影更具參照價值的顯然是弗朗索瓦·若斯特的電影話語及其敘事考量,“即視化、即聽化、即知化”等即為國產現代微電影提供了敘事倫理與敘事想像等高級敘事的進階之途。
(三)后現代新敘事升華
雖然可供敘事參照的萬花筒般變幻的理論令人眼花繚亂,但是,歸結起來,我們看到,后現代新敘事理論,早已經由針對影視藝術的純粹理論與純粹技法研究,升華而為一種敘事倫理與敘事想像的研究,換言之,以什克洛夫斯基的話語表達,就是要充分發揮影視技術潛意識下隱藏著的靈性,創造影視形式藝術的詩性影視藝術作品,以及創造能夠更加充分發揮影視藝術作品中的故事性、情節性、語義性的散文式影視藝術作品。事實上,從這種意義而言,微電影的單純敘事研究已經上升為一種敘事學意義上的藝術考量。縱觀國產微電影,我們看到普遍在敘事方面缺乏淺意象與細膩敘事的深度融合,同時,更缺乏直接敘事與多元化敘事的深度融合,這種致命缺陷顯然弱化了國產微電影的自我風格敘事張力。可見,應大力鼓勵國產微電影的強創意性、強互動性、強內容性的針對敘事的精雕細琢。
三、 微電影的敘事學進階分析
(一)進階式模式化敘事分析
針對微電影的后現代新敘事學理論的研究可見,敘事模式本無定式,尤其是微電影的敘事模式,完全可以在追求無限張力的情況下,進行更加自由的意識建構。針對微電影的敘事實踐研究,亦更加清楚地令我們看到,微電影敘事的真正藝術性,恰恰在于其可持續地,針對微電影的敘事微架構、敘事微風格、敘事微主題等所大力進行的“微”創新。因此,國產微電影的敘事,完全可以做到對于單一線索的全面突破,完全可以采用多線索的縱橫交錯,形成一種意象繁雜的更加符合后現代意識的敘事杰作;同時,國產微電影亦可將單一線索進行多線索拆分,并在單一線索與單一的時空之中建構起多重線索,以實現更加復雜的一主多副、一顯多隱、一動多靜等更多架構、風格、形式的敘事。[3]
(二)進階式敘事類別分析
從后現代新敘事學視角而言,我們看到,國產微電影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大類,即表達敘事類與內容敘事類,表達敘事類即以事件之所指所進行的敘事,內容敘事即以事件之能指所進行的敘事。同時,國產微電影還可以按照敘事手段與敘事路徑的曲直分為金剛怒目式直接敘事與菩薩低眉式委婉敘事,從這種意義而言,顯然,金剛怒目“怒”,不及菩薩低眉“恕”。事實上,微電影的敘事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影視敘事有了非常大的不同,那就是,微電影的敘事已經最大限度地模糊了現實與擬真現實之間的那條顯著的紅線,微電影的敘事完全可以創造
出多重的時間段落,甚至許多微電影即以實錄現實
(下轉第109頁)
(上接第103頁)
構成其敘事主體,因此,微電影的敘事即可以由現實本體敘述,亦可以由擬真現實他者敘述。無論敘述者為何,事實上,微電影所詮釋的都是一種完整的影視話語,既能夠將時間段落非現實化,亦完全可以將時間段落現實化。
(三)進階式意象化敘事分析
事實上,無論是敘事模式的法無定式,還是內容敘事所涉及的情節與行為,亦或是表達敘事所涉及的模仿、敘述與語義等等,都是微電影敘事的較為基本的范疇,從更高級的敘事視角而言,敘事還應該成為一種超越客觀物象,并且將主觀情思與主觀情懷與客觀物象映像加以深度融合,從而形成的一種敘事意象。唯其如此,創作出來的微電影才能夠真正達到形神兼俱、虛實皆合、動靜相宜的進階式藝術境界,同時,從微電影的意象境界考量,其實微電影從這種意義上而言,亦是一種創作者以其作為主觀自由王國意識渲泄的精神代償。從更進階的意義而言,微電影更是一種遠比大電影更銳利的影視符號學表達,這種影視符號學表達,為微電影由表象性閾進入象征閾,再由象征閾進入意象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敘事自由度,敘事的這種意象閾顯然更加考驗微電影創作者的社會學想像力與社會圖景的研判分析能力。[4]
結語
無論從何種意義進行研究與觀察,微電影都顯然是更貼近現實生活的產物。微電影的形諸于影視藝術思維的吉光片羽,都是創作者由人間煙火中采集與升華的智慧結晶。微電影以其微言大義,與微意無窮而深受后現代時代觀眾的普遍歡迎。從敘事學視角而言,微電影更應傾力于透過人間煙火的表象,以更深入的體悟與更深刻感悟,為觀眾帶來更具感染力的淺沉浸的意象。唯其如此,方能更加立體地式展現出,后現代社會中的蒙太奇式的生命過程與社會歷程。最后,從更加進階的敘事學意義而言,微電影更應成為一種微意象的微凝聚,同時,亦更應以這種微意象的微凝聚為線性主線,以輔助的非線性次要線索與其并行,以微電影的敘事者與傳遞者的智慧,向微電影的接受者傳遞更加精彩紛呈、更加光影繽紛的影視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