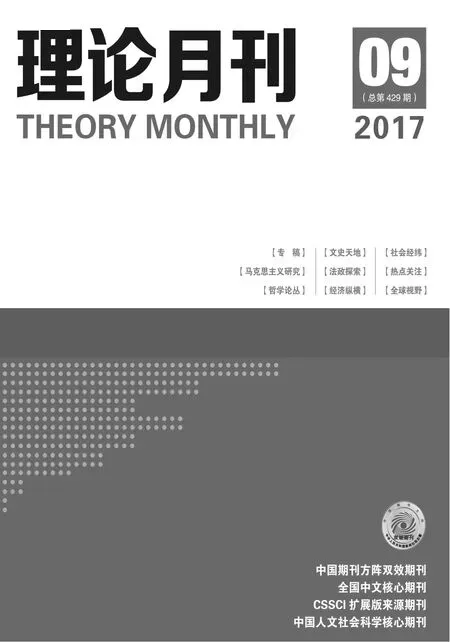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思想與方法
□黃思賢
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思想與方法
□黃思賢
(海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海南 海口571158)
郭沫若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相關學術成果異常豐厚。在古文字研究中,他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作為指導思想,以研究社會歷史文化為最終目的,結合現代理論與傳統方法,對已取得成果勇于否定與自我否定。雖然他的研究存在一些瑕疵,但其在古文字研究中的成績和思想方法無可否定,并將裨益于后學者。
郭沫若;古文字研究;思想;方法
郭沫若先生在其80余年的人生中,無論是文學與歷史,還是考古與文字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他離去的40多年中,其學術成果也已成為諸多學科的重要研究資料和研究對象。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有關郭沫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與歷史兩個領域,古文字研究雖也被提及,但卻不深入。
談及郭沫若先生在古文字學領域的地位,自然會提到“甲骨四堂”。實際上,他的古文字研究并不僅限于甲骨文,而是廣泛地涉及金文、石鼓文等古文字。從已公布的研究成果來看,郭先生對古文字的研究起于1929年前后,在其后的幾十年中,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甲骨文方面,主要集中在甲骨文的整理與著錄、甲骨文字的考釋和甲骨學自身規律的發現和研究等方面。其代表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和《殷契萃編》。金文方面,涉及金文整理、考釋和文字研究等,主要著作有 《兩周金文辭大系》《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等。石鼓文方面,出版了《石鼓文研究》一書。沈兼士先生曾盛贊其為“能總集大成”[7]。另外,郭先生在戰國文字、簡帛文字、碑刻文字等方面也有一定建樹,其代表作有 《侯馬盟書初探》《熹平石經魯詩殘石》等。
郭沫若先生在文字學領域所取得的成績固然與其個人的勤勉相關,但同時也與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思想密不可分。正確的思想理念可以確保正確的研究方向,科學的研究方法則保證了研究過程的科學性和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1 以社會歷史文化研究為目的
研究古文字莫過于兩個目的:一是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古文字,是純粹的古文字學。二是為其他的目的去研究古文字,古文字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郭沫若當屬于后者。“我們現在也一樣地來研究甲骨,一樣地來研究卜辭,但我們的目標卻稍稍有點區別。我們是要從古物中去觀察古代的真實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虛偽的粉飾——階級的粉飾。”[2]195
實際上,《郭沫若全集·甲骨文字研究》的編撰與所考釋的古文字同樣表現出這一目的。該書的排次為“釋祖妣”“釋臣宰”“釋耤”……。這一順序顯然與古代社會發展史相契合,這些考釋的文字正好是一個個時代的歷史文化標簽。該書雖名為甲骨文字研究,但卻也是一部小型的社會歷史研究。
在《甲骨文字研究》的重印弁言中,他直言不諱地寫道:“這些考釋,在寫作當時,是想通過一些已識未識的甲骨文字的闡述,來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1]7又“甲骨文字的研究,經過其后的安陽小屯的科學發掘,已有了很大進步。殷代社會的真實情況,比起二十年前也更加明了了。殷代是青銅器時代和奴隸社會,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事。”[1]7“得見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會之真情實況燦然如在目前,得見甲骨文字后,《詩》《書》《易》中的各種社會機構和意識才得到了它的泉源”[2]195。
在古文字研究中,郭沫若始終堅持這一研究目的。在“釋祖妣”,他并沒有一味地從字形、字音或字義上進行考證,而是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探討古代的婚姻制度。諸如“閑常考家族進化歷史,得知婚姻之演進亦有一定郵程。”“父子之關系雖疏,母子之關系較密。在群居生活中,漸進則與同一母氏之下自然成一集團。而交接之事在同一集團中初無限制,學者稱之為血族群婚”[1]22等。在本文的最后,郭沫若寫道:“以上所述祖妣字之解釋均可為互證,且于宗教之起源與古代文化之認識上有關系,故余備論之如是。”[1]64
在社會歷史研究中,郭沫若頻繁地引用古文字及其相關古文字拓片,有力地支撐了他的觀點,古文字研究的作用在這里發揮得淋漓盡致。比如在探究上古的牧畜問題時,使用了以下古文字資料:“今夕其雨,獲象”(《前》三,三一,三)[2]200。又如,“服象的證據除了上御字之外還有一個很有意義的‘為’字。據羅釋‘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并做為,從爪從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類編》三,九),這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一個發現”,郭沫若進而論斷:“六畜乃至七畜均已存在,其應用也很繁多。”[2]204
郭沫若研究古文字的這種目的,與其個人的學術背景和做學問的基本理念密切相關。他最初涉獵的領域并非文字學,而是文學歷史。隨著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語言文字,尤其是古文字開始成為其前進的絆腳石。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盛行的學術背景下,他也匯入了這股研究大軍,但初衷未改。
正是這一背景和這一鮮明的目的使得郭沫若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多文字學成果。這一目的也使得他的文字學研究頗具特色。也許,郭沫若的本意并非文字,但卻成為了一位成果豐厚的文字學家。
2 傳統方法與現代理論的結合
郭沫若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文化新舊交替時期,傳統思想文化與外來新型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也就是在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中,造就了一批學貫中西、頗具創新能力的學者,郭沫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從他的歷史、古文字等研究成果來看,傳統的經學、小學痕跡是非常明顯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也已融入其中。在這些現代思想中,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據目前研究,郭沫若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始于上世紀20年代。隨后,他深入地研究了相關著作,并翻譯了《政治經濟學批評》《德意志意識形態》等作品。在稱頌這種思潮的同時,他也將這種思想融入到他的歷史文化、考古、古文字等研究領域。
在反思過去的相關研究中,郭沫若曾說:“談 ‘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2]9“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范圍,然后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2]8。在新思想的面前,他找到了自信,“以前沒有統一的思想,于今我覺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決的問題,于今我覺得尋得了關鍵。”[6]
在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中,唯物歷史觀的表現極其鮮明。比如,匕(牝),古解釋為“匕,比也”。郭沫若批道:“余案‘匕者,比也’乃后起之說,其在母權時代,牡尤不足以比牝,逞論牝比于牡。”[1]38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以“母權時代”作為時代背景來研究“匕者,比也”。即在那樣一個時代,不是女子向男子看齊,而是男子向女子看齊。這一解釋顯然有悖于那樣一個時代背景,當為后人臆說。
又如釋“王”,《說文》有:“……一貫三為王……”,這顯然是對王權的夸贊。郭先生則依據生殖崇拜及社會發展的背景進行了解釋,“其在母權時代用毓以尊其王母者,轉入父權則當以大王之雄以尊其王公。”認為“王”亦為生殖崇拜,為陽器。我們權且不去懷疑郭沫若此類解釋的正確性,但其研究思路值得稱頌。
在古文字考證中,郭沫若還融入了民俗學、民族學的相關知識理論。比如甲骨文“賓”字的考釋,“蓋賓從宀匕,匕亦聲。賓匕,脂真陰陽對轉也,從匕在宀下,與宗同意。或從亼……近時鄉人尤有祀飯瓢神者,當即古俗之孑遺也。”[1]43這里旁引了鄉人的習俗,后文又進而列舉道“日本亦有此習,凡社祠多以飯匙晉獻,以飾于壁。 ”[1]43
在借鑒現代科學理論的同時,郭沫若并沒有摒棄傳統的研究方法,而是充分地使用傳統文獻學和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方法。
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互證。例如,在《釋祖妣》一文中,為論證上古祖妣相對的關系,首先列舉了傳世文獻,《詩·小雅·斯干》:“似續祖妣”;《詩·周頌·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得出祖妣相對;繼而引用出土文獻,齊侯镈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1]19。最后得出《爾雅·釋親》:“父為考,母為妣”當系戰國詩人語,《帝典》諸篇為孔門所偽托。又如,“娥”即娥皇的論證,郭沫若先引用了卜辭:“貞子漁有(有)(豊)于酒。”(鐵二六四葉一片)其中為祭祀對象,擬定為“娥”,再引許書:“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1]29最后得出結論:“字于人名之外古無他義,則此妣名之“娥”非娥皇沒屬矣。”[1]29
據上下文意考字。在考證卜辭中的“臣”時,郭沫若論道“然而所謂臣民者,固古之奴隸也。彝銘中入周以后多賜臣民之事。夨令簋:作冊夨令尊俎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凡此均臣民與土田都邑器物等同為賜予之物,人與物無別……此臣民即奴隸之明證。”[1]66這里講臣與上下文中的田地器物等比較分析,得出臣為奴隸的結論。
據異文考字。在論證“賓”與“宗”的關系中,郭沫若論道:“鐘一器其有“用好賓”語,一作“用好宗”,其二編鐘一作賓,一作宗,是賓宗同義之證。”[1]43
除了通曉上古文獻,郭沫若也熟諳傳統小學。在文字論證中,他大量地使用音韻、訓詁、文字等小學理論。在《釋干支》中,郭沫若認為“辰”為一種農具,其中有這樣的論述:“故辱字在古實辰之別構,惟字有兩讀,其為耕作之器者則為辰,后變而為耨……由音而言,則辱、蓐與農乃侯東陰陽對轉,故辱、蓐、農古為一字”[1]205,此為“小學”中的音韻之法。論證中,郭沫若也常據字形考證古文字,例如“王”字,“卜辭王字極多,其最常見者作“”,與士字之或體相似,繁之則為“”(前六卷三十頁七篇),若(後下十六頁十八片)。省之則為(前四卷三十頁六片),若“”(前三卷二十頁三片)。”[1]49從“王”的古字形論證了“王”與“士”的關系,進而得出“王”字亦取象雄性生殖器。
總之,在古文字考證中,郭沫若充分地使用了各種理論方法,尤以唯物史觀的運用最為突出。
3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古文字研究有其特殊性。由于歷史久遠,論證材料缺失,在古文字考釋中,各家往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要想在該領域取得突出的成果,除了要有科學的理論和豐富的資料,還需大膽地設想和推測。所謂的大膽,不是毫無根據地臆想,而是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原則。在郭沫若的研究中,其大膽的背后是以唯物歷史觀為堅實基礎,以社會學、民族學等現代學科為支撐。
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中,似乎有著詩人般的氣質和想象。在探討十二地支起源時,他這樣寫道:“釋支干篇所談到的十二支起源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依然是一個謎。我把他解釋為起源自巴比倫的十二宮,在今天雖然還是沒有更好的直接物證,但也沒有更堅實的反證。古代太遼遠了,物證恐怕是很難找到的。但我依然寄系這希望的希望:在地下發掘系統地廣泛展開的時候,能夠得到更多的證明。”[1]9在這里,郭沫若將十二地支的起源與古巴比倫聯系在一起。
在古文字考釋中,郭沫若的“祖妣”考頗具想象。關于“祖妣”,學界的觀點很多。其中,郭沫若的“生殖崇拜”說最具沖擊力,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曾認為郭沫若的這種解釋是異想天開,頗具冒險性[4]33。“祖妣”考一文中,以生殖崇拜為基礎,考釋一系列相關字,值得注意的有:(1)“祖妣”,“然則祖妣之朔為何耶?曰祖妣者牡牝之初文字也。”[1]36“是則且實牡器之象形也,”“匕乃匕柶字之引申,蓋以牝器似匕,故以匕為妣,若牝也。”[1]38認為“祖妣”為雌雄生殖器。(2)“士”,“土、且、士實為牡器之象形。”[1]39(3)關于“示”,“此由字形而言,‘’實‘’之倒懸,其旁垂乃毛形也。”[1]41(4)“賓”與“方”,“蓋古人于內外皆有牝神,祀于內者為妣,祀于外者為方,猶牡之祀于內者為祖,祀于外者為土也。”[1]44即“方”為雌性生殖器,“賓”,則為屋內之生殖器。(5)母與后,“后辟之后亦崇拜生殖之意。”即女性生小孩的情形。
考釋中,郭沫若從“祖妣”入手,進而關聯了一系列相關字,并一一論證,成體系地揭示原始的生殖崇拜。整個論證頗具規模,對學界具有深遠的影響。
此項研究中,郭沫若并不只是簡單地提出觀點,而且進行了周密嚴謹的論證。例如,為論證“土(且)”和“匕”為雌雄生殖器,郭沫若羅列了從牛、從羊、從豕等相關的雌雄動物,從文字的構形角度進行了論證,并得出“卜辭牡牝字無定形,牛羊犬豕馬鹿隨類賦形,而不盡從牛作。”[1]36文字形體和相類推的想象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為論證“土”,及與“且”的關系,郭沫若先分析了兩者的古文字形。“土字古金文做‘’,卜辭作‘’,與‘且’字形近。”再比較了兩者的字音,“由音而言,土、且復同在魚部”。最后從古代宗教制度進行了分析,“而土為古社字,祀于內者為祖,祀于外為社,祖與社二而一者也。”[1]39論證中涉及語言文字學、宗教學、文化學,非常充分。為論證“士”,郭沫若同樣分析該字的古字形,“士字卜辭未見,從士之字如吉”,卜辭中沒有發現獨體的“士”,卻列舉構形中的“士”,并將此字形與“土”的字形比對。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幾個字之間的字音關系,“士”與土、且的語音關系“士音古雖在之部,每與魚部字為韻,如《禮記·射義》引《詩》‘曾孫侯氏’八句以舉、士、處、所、射、譽為韻……”[1]39
雖然學界對郭沫若的觀點紛紛提出異議,但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更有力的證據推翻其結論。我們認為,這與其大膽推測背后的堅實理論是密不可分的。
科學研究就是要不斷探究未知的領域,如果都清晰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也就沒有研究的必要。在陌生領域前,研究需要大膽地設想和猜測,并不斷地進行研究論證。
4 否定與自我否定
在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中,有繼承,但更多的是批判。有對前人成果的批判,也有對時人的批判,也有對自己的批判。在批判中,作者提出自己的觀點;在批判中,更新著自己的觀點。
對漢字的研究,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留下許多不同的觀點,有些還很經典。兩千年來,人們遵循著這些經典,或引用,或闡發。當中國傳統思想的禁錮打開后,學者開始科學地對待這些觀點,或繼承,或批判。郭沫若在古文字的研究中,使用新材料、新思想、新方法,在批判古人的同時,提出自己的新觀點。
對于“士”字,古人有“推十合一”之說。郭沫若批道:“‘推十合一’之說,亦必非士之初意。孔子之意殆謂士君子之道,由博返約。然士為士女之士實遠在士君子之士以前。 ”[1]38
《說文解字》中,許慎引用了孔子的觀點“一貫三為王”來解釋“王”字。郭沫若毫不客氣地批道:“此乃后起之字形以為說,非王字之本義也。王之古文,畫不限于三,中不貫以一……據此可知孔仲尼不識古字,每好為臆說。 ”[1]50
《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后世貶帝號,號為王”。郭沫若批道:“按以卜辭,此說殊不確,蓋卜辭天子已稱王,且已稱其先公為王亥、王恒、王夨矣。 ”[1]49
羅振玉和王國維是古文字研究的大家。郭沫若曾評價道:“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2]8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深受兩位學者的影響,但在后來的古文字研究中,郭沫若對兩位的觀點提出一些反對意見。
比如“后”,王國維認為“像倒子在人后,故引申為先后,又引申為繼體君……”[1]47郭沫若認為:“立說均甚精到,惟采許書后為繼體君之說,則事有不盡然者。”[1]47并列舉傳世文獻進行駁斥,“《書·盤庚》曰‘古我前后’、曰‘我古后’,曰‘我先神后’,曰‘高后’、曰‘先后’,及《商頌》之‘商之先后’,凡此等稱述之中,即創業垂統之成湯亦被含括,且為主要之中心人物,此非繼體君之謂也”。[1]48此番評論甚是公允。
實際上,郭沫若在研究中,也不斷地修正著自己的觀點。在《甲骨文字研究》的重印弁言中,他曾寫道“今天看起來,固然是錯誤,但其實我在作那種看法的當時,已經就覺得不大妥當。特別在寫這些考釋里面的釋干支的時候,看到當時天文知識的水平相當高,作為原始氏族社會怎么也難說明。但我固執著自己的舊說馬虎過去了。這應該作自我檢討的:就是做學問時,未能夠充分地做到實事求是。”[1]9
又如古文字“匕”,在《甲骨文字研究》中,郭沫若曾論道:“匕乃匕柶字之引申,蓋以牝器似匕,故以匕為妣,若牝也。”但在1955年,他致信楊樹達:“‘匕’當時“匙”之初文,‘匕’形之略變,許說為‘反人’,非是。‘匕’用為‘且匕’或‘牡牝’字,乃假借之例。”[3]507前認為是“引申”,后修正為“假借”。
學問需要爭鳴,需要不同的聲音。對于未知領域要勇于探索,不怕犯錯。科學研究的突破往往建立在否定的基礎之上。郭沫若就是這樣一個典范。
5 結語
從遺留下來的資料和成果,本文梳理了郭沫若的幾條研究古文字的思想方法。這些思想方法彼此互相關聯,互為因果。研究社會歷史的目的決定了他的古文字學的研究方法與學術定位,科學唯物史觀則指引著古文字的研究方向,敢于批評的精神讓其不斷地前進,傳統與現代研究理論讓他的研究更加科學。正因為這樣,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與其他古文字研究相比,更具鮮明的前瞻性和科學性,也讓他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令人嘆服的古文字研究成果。
唯物史觀為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鋪設了一條康莊大道,但也讓其古文字研究蒙上濃郁的歷史色彩,同時也掩蓋了文字學本身的特質。在古文字研究中,郭沫若往往以預設的社會背景去看古文字,這與古人以當時的社會背景去觀照“王”為“一貫三為王”有著某種相似,只是古人所見到的文字比我們所見到的時間晚。假若所預設的社會背景存在問題,并以此去觀照古文字,那么必然會影響到古文字研究的準確性。因此,我們認為,古文字研究在重視歷史背景的同時,更應尊重文字的本體。比如,在“皇”的考釋中,郭沫若認為下面的“王”與獨體的“王”同樣是雄性生殖器,這顯然與其所預設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但如此下來,上部的“白”又該如何解釋?事實上,他也沒有給出解釋,令人疑惑。筆者倒是贊同“皇”為“煌”,為“火燭”,用為皇帝之皇,當為文字之假借,只是一種普通的用字現象,并沒有那么玄妙。另古文字“黎”,郭沫若先生前后有解釋不一致的現象。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有“耕具、耕事、耕牛之黑者均謂之黎。耕具犀銳謂之利,耕事有獲亦謂之利,耕民面黑則謂之黎。”[1]88,而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則認為:“為甚么民會稱“黎”呢?這大約就是中國古代的先住民族,這種人或者就是馬來人和四川的黎族的祖先,馬來人和彝族都是棕黑色的,馬來人的傳說也說他們的祖先是從北方來。恐怕這些民族的祖先就是古代的蚩尤或者三苗了。”[2]121到底是什么?他沒有給出最后的答案。
瑕不掩瑜,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其在文字研究中所開創的方法和提倡的思想值得我們去學習探討。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 1 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郭沫若書信集[M].黃淳浩,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4]郝雯雯.郭沫若的甲骨學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1.
[5]符丹.郭沫若古文字整理方法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10.
[6]郭沫若.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G]//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沈兼士.石鼓文研究三事質疑[J].輔仁學志,1945(1).
責任編輯 李利克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9.009
H028
A
1004-0544(2017)09-0052-05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6XMZ017);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課題(HNSK(YB)16-124)。
黃思賢(1975-),男,江西臨川人,文學博士,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