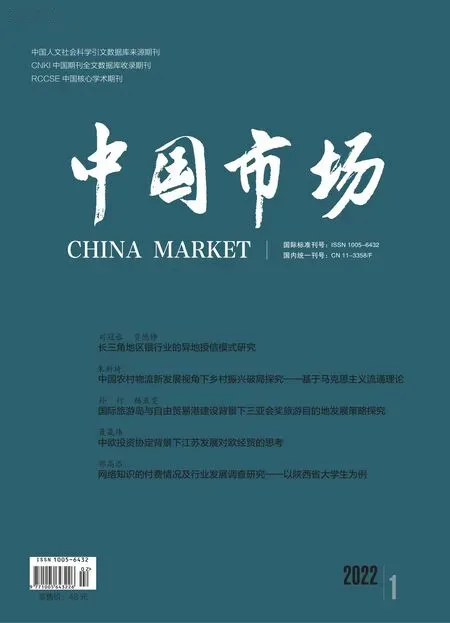金融監管模式的演進及對我國監管體制改革的啟示
王松


[摘要]文章從金融監管客體與監管主體兩個角度分析了世界范圍內金融監管模式的演進路徑,總結了金融經營業態與監管模式之間、演進路徑之間的一般關系,并在討論美國次貸危機后監管模式變化的基礎上,對我國正在推進之中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金融監管;監管模式;演進;改革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2.061
金融監管模式是指一國或者地區對其金融監管客體、監管主體的制度及體制安排。金融監管模式的演進本質上反映著監管理念的演進。世界范圍內金融監管理念的演進大致有以下幾個發展階段:一是20世紀30年代以前,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提供一個穩定貨幣供給,防止銀行擠兌帶來的消極影響,很少涉及對金融機構經營行為的監管;二是20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時期凱恩斯主義興起,金融監管理念順應了這一變化,美國等國開始執行嚴格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制度;三是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經濟界新自由主義理論開始復興,金融監管隨之開始放松,混業經營、金融創新持續深化;四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這一時期一系列區域金融危機相繼爆發,尤其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使得政策制定者反思“市場化監管”的弊端,逐漸更加關注金融系統性風險防范,更加注重金融安全和市場效率之間的平衡。
1 金融監管模式的演進
1.1 基于監管對象的監管模式演進
第一,機構型監管。機構型監管模式按照金融機構類型設立監管機構,不同的監管者監管不同的金融機構(見圖1)。各國金融監管體制傳統上就是根據金融分業經營的現實而按照機構監管的原則來設立的。在金融分業經營下,機構型監管效果十分明顯,可以發揮監管專業分工優勢,解決不同監管目標的相互沖突,也可以保持不同監管者之間一定程度的競合,避免不必要的重復監管。但隨著金融混業經營的深入發展,機構型監管存在著一些問題。如在混業經營下提供相同金融服務的不同金融機構面臨不同的監管者,其監管標準可能不一,從而影響公平競爭;此外,金融控股公司也可利用其跨業經營的便利實現監管套利。
第二,功能型監管。功能型監管按照金融業務類型來設立監管機構,不同金融業務由不同的監管者監管(見圖2)。在混業經營背景下,跨行業的金融機構和跨市場的金融產品不斷出現,原有金融業態之間的界限不斷模糊,這樣機構型監管就顯得力不從心。功能型監管則不拘泥于機構性質,強調跨行業和跨市場監管,這樣就更有利于金融風險防范和化解。功能型監管也有其固有缺陷,如混業經營可能導致功能監管者忽略不同行業風險控制技術和文化差異,也可能導致監管者之間由于協調不充分而出現監管效率下降和金融機構疲于應付的局面。
第三,目標型監管。由于機構型監管和功能型監管各有利弊,目標型監管便在金融理論和監管實踐中應運而生。金融學家Taylor 1995年提出的“雙峰式”監管就是目標型金融監管模式的典型代表,雙峰監管認為金融監管有兩類核心目標,即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見圖3)。雙峰監管模式得到了澳大利亞、荷蘭等國的積極響應。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后越來越多的國家在金融監管改革中的成功運用,世界范圍內目標型監管趨勢愈加明顯。目標型監管這種新的監管模式擺脫了具體的機構或業務導向的約束,定位于金融監管的根本目標。與分業多頭監管相比,它降低了監管者之間相互協調的成本和難度,避免了監管真空和重復;與功能型統一監管相比,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監管機構之間的競爭制約關系從而避免了監管壟斷導致的監管效率下降。當然,實施目標型監管,需要對現有的金融監管機構進行徹底的調整,其實施難度可以想象。
1.2 基于監管主體的監管模式演進
第一,多邊監管。多邊監管模式由多個機構實施對不同金融產品、不同金融機構和不同金融市場的監管,監管機構間沒有隸屬關系,各自在其職權范圍內執行監管。多邊監管最為典型的是金融分業監管模式。
第二,混合監管。混合監管模式是介于統一監管與多邊監管之間的一種折中監管模式。巴西、美國等國的牽頭、傘形監管模式就是這種監管模式的典型代表。
第三,統一監管。統一監管模式由一個統一的機構實施對所有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的監管。英國和日本都在20世紀末根據國內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進行了監管體制的“大爆炸”改革,實行統一監管模式。理論上,統一監管可以獲得監管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避免多邊監管容易產生的監管沖突、監管疏漏和重復監管,從而提高監管實效。但是,統一監管由于缺乏監管競爭也可能會導致監管效率的下降,在從多邊監管走向統一監管的過程中如果監管機構整合不好,也有可能帶來監管規模和范圍的不經濟。
1.3 金融監管模式的一般演進路徑
圖4總結了金融業態與金融監管模式之間的一般演進路徑。虛線代表的是一種最優的對應關系,比如,在分業經營的情況下,由于一個機構只能經營一種業務,這樣采用機構監管與多邊監管本質上是一致的。在混業經營條件下,業務界限打破了,此時就適宜從業務的角度采用功能監管,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各個功能監管者之間互不隸屬,這樣在高度混業經營的情況下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成本將會極高,所以在機構設置上就適宜監管機構內置化,采用統一監管;抑或跳出機構與業務之爭采用目標監管,相應地在機構設置就應采用峰式監管架構。當然實踐中各經營業態、監管思想和機構設置不一定是一一對應的,因為過渡狀態的存在為監管模式的具體實現形式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2 金融監管模式演進的美國案例分析
2.1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演進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美國國會出臺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逐漸形成了一種“雙線多頭”的金融監管模式,“雙線”指聯邦和州均各設有金融監管機構,“多頭”指對不同的金融機構設有不同的監管機構,這些監管機構主要有聯邦儲備體系(FRS)、貨幣監理署(OCC)、儲蓄機構監理署(OTS)、國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等。70年代后隨著金融混業經營不斷深化,金融監管不斷放松。1999年美國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從法律角度確認了混業經營的事實,確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并建立了傘形監管制度,即美聯儲承擔金融控股公司傘形監管者職能,金融控股公司的子銀行和非銀行類子機構仍分別保持原有的監管模式。從機構設置上看,傘形監管是介于統一監管與分業多頭監管之間的折中監管模式;從監管思想上看,傘形監管盡管強調功能監管,但是實踐中機構監管特征依然突出。實際運行中,上述監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監管重疊、監管缺位和監管標準不一等問題,這也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2.2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改革取向
自2008年后,美國政府在總結金融危機原因的基礎上,實施了一系列監管改革措施,先后出臺了《現代金融監管構架改革藍圖》《金融監管改革框架》《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等文件,簽發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這些改革文件和法案具體內容雖然有所差別,但有許多共同的改革取向。比如《現代金融監管構架改革藍圖》中提出整合監管資源,建立三個新的大型監管機構,即建立市場穩定監管者(MSR)、審慎監管者(PFR)和行為監管者(BCR),全面負責對整個金融體系和經營行為進行監管,對投資者和消費者進行必要保護;《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則要求建立金融穩定委員會(FSOC)和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切實加強對跨市場衍生品和影子銀行的監管。可以看出,上述改革文件和法案均注重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注重加強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注重推進金融消費者保護,這與目標型監管思想總體一致。作為在世界金融體系中有著重要地位的美國逐漸轉向目標導向型監管,這一模式或者說這一模式所代表的金融監管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的運用趨勢將會得到進一步強化。
2.3 對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許多實業集團以及金融機構通過組建金融控股公司打通貨幣市場、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一些跨市場的金融產品也不斷涌現,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越發明顯。但金融監管模式仍然屬于分業機構型監管,與我國當前的金融業態以及系統風險防范要求極不相符。尤其是2015年的股災為我國金融監管敲響了警鐘,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刻不容緩。這一點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均取得了廣泛一致,但如何實施監管體制改革爭論很大。從本文分析的世界范圍內金融監管模式的演進路徑以及美國最新監管改革實踐來看,在對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進行頂層設計時需要注意以下三點:一是盡管具體監管模式的選擇受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結構等多種因素影響從而呈現多樣性,但縱向看監管模式的演進仍有章可循,體現了從機構監管到功能和目標監管、從分散多頭監管到統一監管的演進路徑;新的監管體制應有利于發揮功能監管和目標監管的優勢,從而促進全面實現金融監管的最終目標。二是隨著我國混業經營的深入發展,金融創新產品變得越發復雜,極大地超出了金融消費者的理解能力;新的監管體制應有利于加強行為監管,從而促進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三是從靜態分析,各種監管改革方案都各有利弊;新的監管模式應有利于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提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能力,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
注釋: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意見。
參考文獻:
[1]張偉.對本輪危機前后美國金融監管體系變化的比較分析[J].國際金融,2014(10).
[2]張瑩.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及啟示[J].中國金融,2013(16).
[3]尚金峰.開放條件下的金融監管[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6.
[4]李波.以宏觀審慎為核心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DB/OL].(2016-02-04).http://www.yicai.com/news/4748214.html.
[5]廖承紅.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初探[J].中國市場,201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