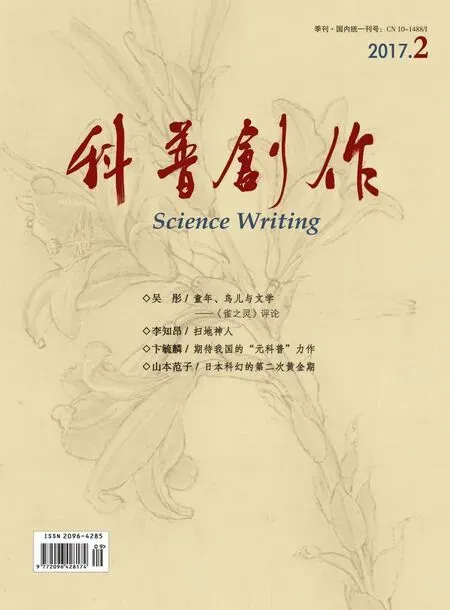從未來走向死亡—電影《降臨》背后的時間經驗與生死觀念
中西比較視野下的科幻命題
電影《降臨》講述了語言學教授路易斯·班克斯通過讀懂外星人語言從而打破人類集體面對外星人時的囚徒困境,最終促使各國展開合作的故事。而她也在和協助自己的理論物理學家班克斯共同揭開外星人文字之謎的過程中走到一起,收獲了屬于自己的愛情。電影中提示路易斯在學會外星人的非線性語言之后,能夠“回憶”起自己的一生,或者按照她自己的講法,可以“看到未來”,于是借助這種能力最終促成了各國之間的合作。然而,她也被這種能力所困擾,以至于在最終“看到”她會和班克斯結婚生子并面臨他們的女兒夭亡,于是她向這位理論物理學家問道:“如果你能一覽自己的人生,從出生到死亡,你會嘗試改變嗎?”

圖1 電影《降臨》海報
科幻電影有其嚴肅的科學設定,并借助光影變化來進一步呈現某些難以實現的合理想象,但在表達過程中總是要和普通人的意義世界產生非常強的關聯,才會引起觀眾共鳴,而這恰恰是科學所不擅長的地方。當我們看到牛頓定律、麥克斯韋方程組、薛定諤方程時,我們會驚異于大自然的神奇和物理學的簡潔,但其背后所包含的世界觀、時間觀等帶有哲學意味的內容卻離我們越來越遠,除非借助更具有沖擊力的表達方式,我們才可能感受到新理論背后所承載的內容——比如當思考生與死這樣的大問題時。
在《降臨》中,作為語言學家的路易斯在掌握外星人語言的同時獲得了一種新的時間經驗,她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被同時展開,并能夠在需要的時候調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提前”知道了自己會和班克斯有一個女兒,并看到班克斯之后的離家出走和女兒的最終死亡。于是,在新的時間經驗背后所蘊含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假若理解外星人的非線性語言后能夠看到自己的一生,那是否意味著所有事情都注定發生,如此一來,人還需要做出努力嗎?
盡管這只是一個假設,但并不妨礙我們去思考它的可能答案,從而反思我們自己究竟持有一種什么樣的時間經驗和生死觀念。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借助中國和古希臘的例子來說明不同的時間經驗,并在對生死觀念的反思中回應這個問題。
不偏不倚的時間經驗與中國人的生死觀
當人類第一次抬頭仰望天空時,會驚異于太陽每日東升西落、周而復始的運動,于是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了最初的時間單位——日,而對星空的觀察并注意到月相的周期變化,使人們有了一個更大的時間單位——月,最終在對太陽周年運動的觀測中人們建立了年的概念。正是在這三個既有變化,又不斷重復的天文現象中,人們逐漸建立了對時間的最初認識。在這一點上,古希臘和中國沒有什么不同,然而先人在此基礎上的思考和實踐卻大相徑庭。
我們不妨先從中國開始。宇宙是中國最古老的關于空間和時間概念的理解,“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這兩個字的連用則最早出自《莊子·齊物論》:“旁日月,挾宇宙,為其吻合”,是說圣人能夠做到同日月并明,懷抱宇宙,和外物吻合一體。正是在這種將內在經驗與外部世界的統合中,中國人的時間經驗在農耕活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法——夏歷,也稱為農歷。農歷實際上是一種陰陽合歷,即同時考慮到太陽和月亮的周期運動而制定的,一方面根據月相的變化將一個月分成大月30天和小月29天,一方面又根據太陽視運動的周期確定一年的長度。由于兩者并不完全重合,一個太陽回歸年要比12個朔望月長,比13個朔望月短,所以就有了閏月的概念。最常用的方法是“十九年七閏”,從而達到兩者周期的最小公倍數,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的公歷(陽歷)生日和農歷(陰歷)生日會有重合的現象。而二十四節氣就是在農歷的基礎上,結合氣候和物候變化制定,以幫助人們確定農業生產活動的重要時間節點。
當然,除了這種周期循環的時間經驗之外,孔子也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慨,向我們提示時間具有某種單向性,個人的時間經驗在短暫的一生被轉變為生死意識,并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是孔子在《論語》中“未知生,焉知死”的重生避死,到了張載則變成“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一方面是莊子在《齊物論》中“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一視同仁,到了王羲之便有了“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無奈。于是,在中國既有在線性時間經驗上所發展起來的發達的歷史書寫的傳統,又不時會根據天干地支、陰陽五行而產生“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各種歷史循環論。
但這兩種經驗在先人眼中卻是并行不悖的,循環的時間經驗并不取消個人的努力,而是給人們提供了從事各種農業活動的合適時機。不同階段的人也都要面臨不同的人生命題,死亡不足懼,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中國人的宇宙論才沒有掉入徹底的循環當中,而是取得了一種不偏不倚的“中庸”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路易斯在習得外星人語言后的所作所為,無疑是更接近中國文化的。
希臘人的永恒理念與靈魂不朽
在古希臘,盡管也存在線性發展和周期循環的時間經驗,但以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為例,我們會發現其最終的追求和儒道迥異。
在《蒂邁歐篇》中,這樣寫道:“天體存在之前,沒有白天、晚上、年月等。在造物者的計劃中,這些東西都隨著天體的形成而產生。它們都是時間的形式。”這是對時間形式的最初概括,強調之所以能形成這種時間經驗,乃是由于天體運動變化所至,這里的“天體”并非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含義,因為那個時候對于宇宙構造的假設和我們不同,所有的運動的天體其實是固定在不同的球殼上,這些球殼分成若干層,通過球殼的轉動才形成了我們肉眼可見的運行軌跡,這也是后來托勒密乃至哥白尼建立其天文學說的一個基本假定。
柏拉圖將時間理解成運動和變化,于是通過計算天體的運動規律就可以理解時間的本性,乃至理解整個宇宙。但這個看起來并不新奇的做法在科學史上被多次強調,因為其提供了一種將自然數學化的思想,并鼓勵更多的人去實踐這種思想。《蒂邁歐篇》完整描述了一個通過數學構造的宇宙模型,無論這只是一個隱喻,還是那個時候的古希臘科學家們認為世界真的如此,但柏拉圖提供了一種思路——從伽利略開始,到開普勒、牛頓,一直到麥克斯韋、愛因斯坦,最偉大的科學家都通過數學來表達自己對于這個世界的理解。
而正是在對數和靈魂的統一理解中,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學說獲得了某種相似性。對柏拉圖來說,永恒理念才是值得追求的東西,因為一切被造物都是有朽的,只有通過理念去把握背后的那個統一的東西,人才能獲得靈魂的不朽,這一點在畢達哥拉斯的學說中有更具體的體現:
畢達哥拉斯對他的門徒們講過些什么,沒有一個人能夠肯定地說得出來,因為門徒們保持一種異乎尋常的緘默。可是,以下幾點是眾所周知的:首先,他認為靈魂是不朽的。其次,靈魂能夠移居到其他生物體中去,而且循環反復出現,以致沒有一件絕對新的東西。最后,因此可以說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是血緣相通的。關于投生問題,塞諾芬尼在哀歌中提供證據……他是這樣講到畢達哥拉斯的:“他們說,當有一只遭到痛打的狗穿過時,他(畢達哥拉斯)充滿憐憫地喊叫道:‘住手!不要打它。它是我一個朋友的靈魂;我聽到它吠聲時就認出了他。’”
柏拉圖在對前人的工作進行思考之后,最終提出了現象界和理念界的區分,并指出前者依靠感覺和意見,處于不斷變化中,因而并不實在,而后者依靠理性和真理,是永恒不變的。現象界只是模仿理念,并且是一個并不完全的摹本。現象界的一切都可以經過數字計算而確定,這最終導致了一種僵化的宇宙圖景,因為一切都變成了力學定律,我們的生活世界逐漸與這種宇宙圖景分道揚鑣。但對于物理學家來說,這種分離是不自覺的,比如,電影結尾暗示路易斯的丈夫——班克斯在他們的女兒長大后不久選擇了逃離,原因就在于當他知道了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而感到一種徹底的絕望,既包括生活世界的無奈,也包括物理世界的崩塌。
人類文明的基石是科學
通過考察古代思想中的時間經驗,我們會進一步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異。而讓我們感到詫異的是,一部現代的科幻電影就其哲學基礎而言,可能更接近東方人的思維方式。從古希臘的占星師到現代的理論物理學家,每一個頭腦聰明的人都試圖將自然的某種規律從神秘主義的面紗下解放出來,并自認為通過對未來的預測和事實的驗證獲得某種可以決定世界的力量。科學正是在這種信念下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并給人們一種印象——“文明的基石是科學”,正如電影《降臨》中的理論物理學家在第一次見到那位語言學教授時所說。
盡管科學照亮了我們的世界,但人依然會對黑暗產生畏懼,對死亡產生畏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仍然需要哲學家、語言學家的存在,如此人類文明才能像莊子在《齊物論》中所說的“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