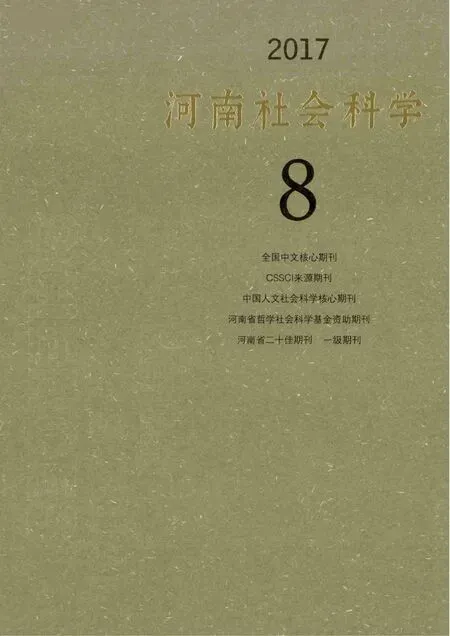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消費者響應的互動機理研究
邊衛軍,趙文龍
(西安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消費者響應的互動機理研究
邊衛軍1,趙文龍2
(西安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一段時間以來,企業社會責任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國家受到了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普遍關注。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與實踐,不但能夠讓企業受到激勵,在履行責任的過程中獲得回報,還能為企業的生產運營提出警示——任何負面的社會責任行為都會對目標客戶的購買意愿與推薦意愿產生直接影響,企業利益會因此而受到損害。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產生,會讓企業與消費者形成新的互動范式。一方面,企業會主動把社會責任納入對經濟利益的訴求當中,并以此構建自身的目標體系;另一方面,消費者會把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消費決策行為的參照系中。雙方的良性互動有助于健康市場秩序的發展與維護。
企業社會責任;消費者響應;互動機理
在對企業進行的早期研究中,學者們普遍認為企業不但應該承擔經濟與法律層面的責任,還要在其生產經營過程中承擔部分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會產生多種不同的作用,直接影響著消費者群體。對消費者來說,企業如果承擔更多社會責任,通常會提升其對企業的認同。相關研究已經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會讓消費者在對產品和服務進行經濟層面的考慮外,還會產生其他理性思考。這是因為,企業社會責任存在溢出效應,能夠提升消費者對其產品和服務的主觀評判。需要注意的是,就消費者群體而言,對企業產生的認同感是消費者針對企業本身所形成的主觀感知,而消費者能否對產品和服務產生購買決策,往往由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的感知價值決定。當前,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問題,他們在關心產品質量、價格等因素的同時,更加看重企業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的成效。從這個角度講,消費者已成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最直接的動力源。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能夠借助消費者的力量,將企業行為提高至與主流社會規范、主流價值觀以及消費者對企業的期望相一致的水平,這既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與水平有關,還與國家主流價值觀與公眾對企業的期望有關。
一、企業社會責任及消費者認知
自現代企業產生以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就一直是實務界和學術界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尤其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企業為了贏得更好的“口碑”,然后借此提升其產品和服務的“知名度”,爭相借助多種途徑表明其對自然環境、社會發展、員工福利、公益活動以及慈善事業的關心,而這些都屬于社會責任的范疇。
(一)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是美國學者Sheldon于1924年提出的。在他看來,任何企業對商品的生產都是為了獲取利潤,但同時也要關注所處產業的內外環境之中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即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應該能夠提高所處的環境服務水平,我們常說的道德因素就包括在企業社會責任之中。1953年Bowen借助其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進行了明確——企業社會責任指的是企業按照社會發展目標與價值訴求制定出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動。但是Davis(1960)卻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屬于模糊的概念,也就是說企業的決策或者行動中至少有一部分行動與企業的直接經營利益無關,而“無關”的這一部分就與人類的利益有關,這部分被稱作“企業社會責任”。在Carroll(1983)看來,整體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指的是企業要同時承擔經濟、法律、道德以及慈善的責任(即所謂的“Carroll金字塔”),任何一個層面的缺失都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義務相背離。而在Carroll提出的企業履行責任的概念模型中,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應該對社會承擔的義務:首先,企業要承擔一定的經濟責任,這說明企業最基本的責任便是創造利潤與持續發展。其次,企業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即企業要遵守法律并以社會法律體系為框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再次,企業要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即企業需要尊重其他社會成員的權利,并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對其權利、公正和公平之期望。最后,企業要承擔更高層次的責任,即博愛和慈善的責任,企業需要更好地支持社區服務,以提升社會福利水平。從Carroll提出了全新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分析、闡釋和再定義,豐富與擴大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外延,構建起了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基本框架體系。
(二)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
消費者作為企業最為關鍵的利益相關者,是企業是否履行、如何履行社會責任最直接的感受者。Parasuraman和Zeithaml以及Berry(2014)通過研究發現,消費者會從自身的訴求出發,對企業應該做什么有著自己的判斷,即便企業為了“討好”消費者需要而做出一些努力,也不會因此而得到所有消費者的理解,因為消費者的愿望和想法會發展成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Creyer與Ross(2015)指出,消費者期望在其購買決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消費者如果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期望持續增加,對那些不履行社會責任義務的企業的容忍度就會降低。在早期,消費者因為不了解企業社會責任及其已有的履行情況,會較為重視產品質量及其相關的部分屬性,一旦消費者深入了解企業之后,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選擇是否對企業的決策、產品和服務等做出積極反應。Auger與Devinney、Louviere(2015)通過研究發現,當前時期,由于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一些企業的影響力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期望進一步增加。如果消費者認為某種特定議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們就會更加積極地搜尋與之相關的信息,然后以某種身份介入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之中。當企業沒有履行其社會責任時,消費者就會借助維權、消費抵制以及不利宣傳等方式對企業施加壓力,迫使其做出有利于消費者的反應。尤其對那些更易獲得的高質量產品,消費者更加重視其非傳統屬性,如果生產此類產品的企業沒有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其遭受“制裁”的可能性就更大。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消費者認知——基于Carroll金字塔式模型的分析
當Carroll提出其金字塔式模型時,世界范圍內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并不完善,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市場發展還處在較低水平,無論是企業抑或是消費者均未能形成明確的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內容和意義無法得到人們的廣泛認知。而在經濟發展尤其是全球化的推動下,企業社會責任理論逐漸得以完善,社會公眾與企業對企業目標形成了正確認識——從之前的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轉變成以社會價值最大化為目標。而在價值最大化的目標體系中,既包含企業自身價值也包含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與義務。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企業無法單純依靠產品優勢去占據市場,也無法通過壟斷謀取高額利潤。與此同時,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的認知與評價更為理性,企業形象與無形資產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重要性與傳統的有形資產處在同一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企業出于經濟利益會放棄對社會責任的擔當,使得社會公眾除了要求借助法律對企業之社會責任予以強制規定外,還要求企業“自覺”地站在社會道德與倫理的高度,對社會發展與消費者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由此演進成企業的內生要求。
企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或者“黑箱”,它將物質、能量和信息等資源進行整合優化,以此創造出社會需要的效益和成果。因此,企業的存在和進步需要以獲取利潤為前提,以保證其能夠借助更多的“能量”維持下去。從這個角度講,企業將利益至上或者“利益最大化”“利潤最大化”視為目標就顯得十分正常了。同時,由于大量企業對社會責任理解存在局限,它們就自然而然地把經濟責任看作是最為重要的責任,其他如法律責任、倫理責任與慈善責任等也就排在后面。比如,在美國,人們崇尚個人主義與自由,社會公眾對個人經濟與福利方面的期望,使得美國企業更加注重經濟績效,以便為自身與股東提供更多價值增值,這在美國早期發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我國,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影響十分深遠,社會責任氛圍尤為突出,如對個人修身齊家治國的道德要求,也推及到各種社會組織中,導致消費者會自動把經濟效益和企業社會責任聯系在一起。消費者在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過程中,希望企業能夠自覺遵守社會規則,并以此為前提去獲取應得的利潤。即便如此,我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依然存在著觀念滯后、相關法規不健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得消費者在和企業進行“權益博弈”的過程中處于劣勢,而這又助長了身處轉型期的中國企業在較低違規成本和不承擔社會責任也不用付出很大代價的情況下,漠視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任重而道遠。
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及其與消費者響應的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消費者響應行為的關系
在通常意義上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大多與其慈善行為和公益實踐有關,這也是普通社會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最直接也最普遍的理解。企業如能良好履行社會責任,不但能夠吸引更多消費者、獲得更為理想的營銷績效,還能為整個社會提供更多社會福利。需要注意的是,對企業來說,借助何種形式履行社會責任,關系到其社會公益目標的實現和企業營銷績效的提升——這是長期困擾企業的關鍵問題。例如,企業借助慈善行為等公益行為,可以協助企業提升其品牌價值,消費者對其品牌的評價也會因此而得到增強,尤其在品牌信任層面上,其作用更加明顯。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企業都會在制定社會責任策略的過程中,把產品質量與慈善行為結合在一起,希望提升消費者對品牌的評價與認知,發揮出強大的示范作用。此外,企業通過公益活動的開展也可以協助提升其品牌評價,雖然作用有限,但也能夠讓企業從中獲益。例如,一些企業可以通過直接捐贈行為讓自身的品牌評價得到顯著提升,雖然這一過程企業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但這種以“善”為載體的營銷模式或者慈善模式,不但可以協助企業獲得更為可觀的利潤,還能提升企業的品牌評價。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尤其在亞洲和非洲),企業的直接捐贈行為一直被視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最為有效的方式。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企業的“善因營銷”行為需要對捐贈對象進行準確定位,只有捐贈對象的選擇和企業產品保持匹配時,才能更好地提升企業的品牌價值和認可度。
(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消費者響應模式的關系
在當今社會,消費者對企業的“要求”不斷增多,促使企業主動或者被動地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成為消費者改變社會環境的一種有效方式。尤其是當企業可以通過積極行為保護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或者對員工、社會公眾等給予更多人性化關懷時,消費者就會對其產品質量和產品品牌給予更高的評價,購買行為也體現出更多的信任。這就表明,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意愿和行為不斷增加時,消費者會傾向于信任和購買那些他們認為能夠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這對身處殘酷競爭環境中的企業來說尤其應該重視。企業是為了追逐利益而生,具有對經濟利益的天然敏感性,倘若可以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加入消費者購買條件之中,就會讓企業因此產生更為強烈的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的意愿和強大驅動力。而在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內,唯有消費者才能為企業創造價值,任何不注重消費者感受的企業行為都被視為錯誤的行為,消費者的購買選擇會因此對企業產生“軟約束”。
由此可見,企業是否承擔社會責任、承擔何種以及何種程度的社會責任,關乎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和購買意愿,只有為消費者貢獻更多利益,才能對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帶來更多正面影響,企業也會因此而成為履行社會責任的受益者。需要注意的是,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我國部分企業即便已經意識到了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在實際行動方面卻與此背道而馳。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的過程中標準不一、負擔繁重、缺少激勵以及無法監督,單純依靠市場力量讓企業積極主動地履行社會責任,其效果并不理想。
(三)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消費者響應目的的關系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主要目的在于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產生正面影響,繼而對企業品牌和產品形成積極的評價,借此形成輿論,引導更多潛在消費者加入購買群體之中。一般來講,企業即便履行了社會責任,試圖通過善行贏得消費者,但是由于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受到大量因素的影響,有些因素的影響力遠超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本身,這使得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在企業的各種社會責任行為中,產品質量責任最能獲得消費者的認可。如果企業為消費者提供的是優質的產品,即便企業沒有履行更多社會責任,部分消費者還是會對企業品牌形成積極的評價,甚至會因此產生品牌信任和品牌依賴。也就是說,相對于企業其他社會責任的履行,企業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更能獲得消費者的認可,這被視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關鍵一步。因此,如果企業沒有在消費者心中形成強有力的品牌地位(比如對一些初創期的企業),就應該將提升產品質量視為最大的責任,借此樹立起更為積極、良好的品牌形象,讓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形成全新的理解。相反,如果企業提供給消費者的是低劣的產品和服務,不但無法形成持續收益,還會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由此看來,企業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是其能夠在激烈的市場中維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
三、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消費者響應的互動機理
(一)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對消費者響應的影響
1.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可以展示企業社會形象
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生存越來越艱難的當今時代,越來越多的企業寄希望于通過支出大量金錢、時間與精力于社會責任事務方面,讓企業能夠以良好的形象出現在消費者面前。而在消費者看來,企業形象不僅表現在功能層面,還涉及企業在社會環境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消費者希望企業能夠提供更低價格與更多種類的產品;另一方面,他們也要求企業可以對維持社區秩序和市場公平提供更多支持。出于這樣的思考,是否履行社會責任、履行了多少社會責任可以看作消費者對企業的重要期望與訴求。已有的實證分析表明,企業形象可以借助兩個維度加以體現,一個為企業的功能水平,一個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時至今日,這兩個維度在企業經營發展歷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同與企業生產的產品、價格的區間以及服務水平等因素直接相關;同時,也會對企業是否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網絡中承擔更多責任給予關注。比如,如果企業的功能能力較高,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提升社會福利,就會促使消費者借此產生更為理想的滿意度以及對企業和產品的忠誠度。
2.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可以產生正面影響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可以產生“光環效應”和“示范效應”,這使消費者對企業的判斷會產生直接的正面效果。這是因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讓消費者將關注點放在企業的行為方面,而這勢必會讓部分消費者忽視企業的其他層面,比如產品屬性、產品質量和產品知名度等。一旦缺少這些理性思考,消費者就會對該企業產生更強烈的認同傾向性。從這個角度講,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可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也會形成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動機。而動機一旦形成,就會在消費者心中產生相對持久、影響深遠并以此為核心的價值判斷模式。從心理學角度講,此類判斷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唯一的變化就是對其進行完善與升級。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借助實驗得出結論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可以對消費者歸因產生積極影響,尤其在歸因理論的歸屬性與穩定性維度上,可以產生較強的影響力,讓消費者有較強的意愿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埋單”。
3.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可以紓解企業困境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為其提供一種特殊的“保護機制”,尤其當企業處在危機環境中時。在此情景下,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能夠消除消費者對企業危機的負面理解,并借此產生正向調節作用,讓消費者對企業產品和品牌的評價保持在穩定狀態,對企業形象的認知也不會因其危機的產生而出現大幅變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消費者出于對企業的認可或者對企業的“同情”,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恢復對其產品的購買意愿。在此過程中,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起到了兜底作用。
(二)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響應
1.消費者關注企業主動履行社會責任行為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可以對消費者產生“光環效應”“示范效應”。但即便如此,消費者也不會不假思索地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全盤接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對消費者的感受視而不見,認為僅憑單方履行社會責任行為就能夠在消費者心中保持良好形象,就會產生反向效果。這是因為,對于越來越理性的消費者來說,他們并不會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都是出于“樸素的目的”,也不會因此而主動正面評價企業的全部公益行為。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與其戰略目標保持一致——都是為了實現更多盈利,消除競爭對手的干預——消費者就會對企業的此類行為產生反感情緒,甚至會因此而采取懲罰性措施,通過輿論傳播讓企業的聲譽不升反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消費者眼中,任何企業的形象都是通過企業能力表現與社會責任表現兩個維度予以展現的。其中,企業能力表現指的是企業在制造和傳遞產品與服務中體現出來的能力;社會責任表現指的是對企業從事社會服務行為的反應。企業形象若想得到消費者的積極響應,除了要在提升績效的基礎上強化對社會責任的履行,還應讓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與對利益的追求之間保持“獨立”。
2.消費者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擬合度
擬合度被認為是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生產線、品牌形象以及定位、目標市場進行匹配的關鍵指標。如果擬合度也高,消費者會提升對企業的好感,響應性也高,有助于強化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聯系。在消費者看來,部分企業會由于自然災難、非政府組織壓力以及遭受消費者抵制等,對自身的形象進行美化,繼而做出“負責任”的公益行為,這種行為一般被消費者視為“反應式行為”,與企業的現實目的和為社會福利做貢獻的動機并不相符,消費者一般不會因此對企業產生積極響應。唯有那些主動承擔和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才會讓消費者主動積極地響應,從而增加企業社會責任的擬合度。
3.消費者注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
在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進行響應的過程中,消費者對企業行為和動機的認知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即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能夠增進社會福利,消費者也不一定會按照企業的意愿響應,他們會“本能”地對企業行為背后的目的和企業價值觀進行猜測,然后按照猜測的結果采取相應的行動。而按照歸因理論,消費者會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歸為兩類:利己動機與公眾服務動機。如果消費者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歸為利己動機驅動時,就會對企業持以消極態度;倘若消費者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歸為社會服務驅動時,就會產生積極效果。
四、消費者響應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
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和實現是一項復雜工程,不但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還要不斷凝聚消費者的力量,讓社會責任的履行體現出可持續性,從而取得更為理想的效果。
(一)消費者響應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路徑
1.建立消費者響應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在這方面,要主動關注不同類型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能力,企業要有針對性地對不同消費者進行差別化宣傳。比如,企業借助邀請消費者對其履行社會責任表現加以測評的方式,讓消費者能夠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產生正面的認知,并借此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參照和指導。同時,企業應注重結合自身所處的行業屬性和產業性質,重點履行具有特色化的社會責任。比如,企業可以和各類新媒體平臺構建良好的合作關系,通過與媒體之間的溝通和合作,讓消費者能夠了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真實情況與真實意圖,借此提升企業的名望與品牌聲譽。
2.建立縱向(產業鏈)和橫向(全社會)的社會責任延伸機制
為了提升消費者的響應速度和維持響應狀態,企業應該與上下游企業在構建供應鏈的同時開展履行社會責任的合作,通過強化對社會責任的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產生的負面影響,確保企業和供應鏈節點上的其他企業能夠實現共同發展。對企業來說,身處復雜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之中,社會責任的履行體現在多個不同的維度上。企業除了完成產品與服務附屬的基本社會責任外,還要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高的層次上履行其社會責任。為此,企業需要從自身戰略出發,通過與其他企業的合作,將更多消費者影響因素融入其生產經營活動之中,通過多維視角對消費者的響應進行分析和研判,依據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履行差別化的社會責任。比如,除政治、經濟等宏觀責任之外,企業需要優先承擔消費者保護層面的責任,通過重視消費者滿意度和提供準確全面的產品信息,提升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同感。
3.激發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意識
在當今社會,存在一部分特殊的消費者——責任消費者,雖然這一群體所占的比例較低,但是,通過喚醒與激發這一群體能夠讓更多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意識得到釋放,能夠讓更多消費者主動踐行公民義務,以公民監督的形式促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為了實現這一點,首先要對消費者進行宣傳和教育,使之認識到責任消費的重要性,讓更多消費者認識到責任消費屬于公民的基本義務,以此支持與回饋那些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并對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予以懲罰。為此,應該不斷拓寬消費者維權和監督的渠道,讓更多消費者通過責任消費獲得物質與精神雙重收益。
(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消費者響應的互動效果分析——以在線零售業為例
實證研究證明,在線零售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會對消費者響應產生顯著的、正向的影響。不論在線零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的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能夠感知到利他動機的消費者都會對此類企業行為的響應處于高位,其程度都顯著超過感知利己動機的消費者。比如,對天貓來說,為了積極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的營銷戰略,該在線零售平臺非常觀注消費者責任。在交易過程中,天貓會重點加強網絡購物系統(阿里旺旺聊天工具)與支付方式(支付寶)的安全保障,對消費者的投訴和建議能夠進行及時處理;同時,能夠在網站界面詳細描述產品與服務信息,向消費者提供周到的購物服務和售后服務。對亞馬遜來說,這家美國最大的在線零售企業一直以來都積極承擔員工責任、法律責任與經濟責任。亞馬遜在世界范圍內通過科學管理,持續提升網站流量,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前幾名零售市場上創造出了十分可觀的網絡零售市場份額與利潤,這對緩解世界范圍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壓力,提升員工的獲得感大有裨益。無論是天貓還是亞馬遜,這類在線零售企業都在承擔著較之于其他企業更多的公益慈善責任。它們積極參與公益事業當中,以社會捐助和成立基金會等形式幫助更多社會弱勢群體,使之能夠從中獲得資金和情感的支持。同時,它們在環境保護、綠色消費以及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也做出了值得稱道的努力。
上述案例可以說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需要保證消費者對企業的正確認知,從而獲得正面和積極的評價。而滿足消費者與企業的利益訴求,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和消費者為此作出積極響應的出發點。這要求企業要深入了解消費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讓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與消費者的要求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消除消費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的懷疑,提升社會責任活動的針對性與有效性。
[1]張太海,吳茂光.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J].商業研究,2012,(12):33—39.
[2]田虹,袁海霞.企業社會責任匹配性何時對消費者品牌態度更重要——影響消費者歸因的邊界條件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3,(3):101—108.
[3]田敏,李純青,蕭慶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消費者品牌評價的影響[J].南開管理評論,2014,(6):19—29.
[4]王靜,萬鵬.企業社會責任要素的消費者認知分析——基于卡羅爾CSR金字塔結構的對比[J].中國集體經濟,2016,(3):34—36.
[5]周延風,羅文恩,肖文建.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消費者響應——消費者個人特征和價格信號的調節[J].中國工業經濟,2017,(3):62—69.
[6]肖捷,歐陽潤平.企業與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共生機理研究[J].消費經濟,2014,(10):83—86.
[7]劉娜,許正良.雙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的消費者響應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13,(9):63—65.
[8]沈鵬熠,范秀成.在線零售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消費者響應——基于中國背景的調節效應模型[J].中國軟科學,2016,(3):96—105.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SR Performance and Consumer Response
Bian Weijun,Zhao Wenlong
For some time,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widely watched by governments,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more and more countries,including China.On the issue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not only can make enterprises were motivated,a reward in the process of responsibility,but also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enterprise operating warn-any nega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target customers directly influence purchase inten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tention,and corporate interests will have great harm.The emerg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will lead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to form new thinking patterns.On the one hand,enterprises will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teg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build their own target system.On the other hand,consumers will incorporate CSR into the frame of reference of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onsumer Response;Interaction Mechanism;to Perform
F12013;F126
A
1007-905X(2017)08-0086-06
2017-05-17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4ASH001)
1.邊衛軍,男,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企業社會責任與信任問題研究;2.趙文龍,男,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社會責任研究。
編輯 凌 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