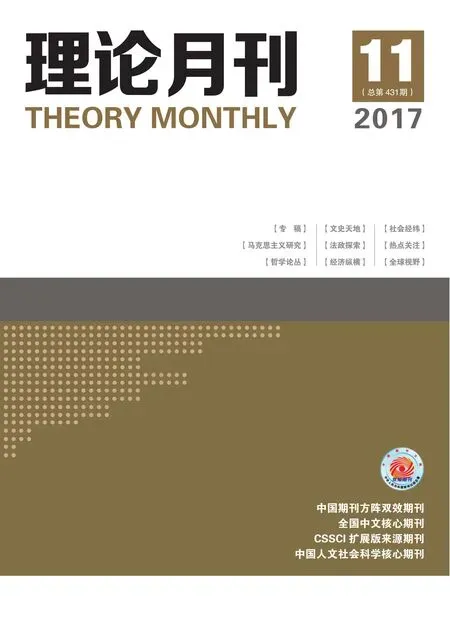清末《尚書》學者附會西學考述
□劉德州
(江蘇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清末《尚書》學者附會西學考述
□劉德州
(江蘇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隨著西學的大舉進入,以及接連不斷的外辱所帶來的刺激,清末學者成本璞、劉光蕡、李元音等人將西學知識注入《尚書》學之中,提出新解釋、新主張,迥異于舊有的考據、義理之學,藉此尋求自強之道。在此過程中,由于《尚書》自身的特點,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他們特別重視對政治相關內容的闡釋。總體來看,他們的立場是保守的,他們的學說也常有因襲前人之處,但畢竟向我們展示了經典解釋的多樣性,也是學隨世變的重要例證,而且對西學的傳播也有所促進。
尚書;西學;成本璞;劉光蕡;李元音
隨著西學的大舉進入,以及接連不斷的外辱所帶來的刺激,清末有大批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西學,藉此尋求自強之道。傳統的經學研究也因此而被注入新內容,一些經生將儒家經典與西學知識相比附,提出新解釋、新主張,迥異于舊有的考據、義理之學。但他們的根本立場仍然是維護中學,大多與當時盛極一時的西學中源說相吻合。有關清末的西學中源說,學界已有可觀的研究成果①參見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1936年;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雷中行《明清的西學中源論爭議》,蘭臺出版社2009年版。,但關注的重點多在自然科學與思想領域,對經學界著墨不多②葉純芳所著《中國經學史大綱》是少有的對此予以關注的著作(參見葉純芳《中國經學史大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83—497頁)。。不過,經學界對西學的認知也有值得關注的特色。一方面,經學研究無法脫離儒經文本,這就決定了在學習西學過程中必然要多動一番腦筋。另一方面,經學具有較強的保守性,在與西學結合時,有著更為明顯的揚中抑西色彩。本文即以成本璞、劉光蕡、李元音等人之《尚書》學為例,對清末經生的西學認知作一梳理。
1 成本璞之《九經今義》
成本璞(1877-1931),字琢如,湖南湘鄉人。 優貢生,光緒癸卯薦舉經濟特科,官浙江候補知縣。所著《九經今義》共二十八卷,刻于1908年,但成氏已于1898年在《湘報》發表《九經今義自敘》,其時業已成書。此書之命名,據成氏自稱是要“紹惠氏之舊式”[1]515,即與惠棟《九經古義》相呼應。然而兩書之旨趣實是大相徑庭。惠棟治經,惟古是求;成氏所謂“今義”,則專求與現實相關之大義。《九經今義》所言不盡與西學相系,但書中主旨仍是西學中源的論調,其《自敘》云:
歐洲諸國,越征海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封豕長蛇,薦會上國。尋其本末,匪有殊科;核其名實,遂收宏效。雖制禮作樂多慚往圣,而立體垂制,暗合古經。驟致盛強,無與倫比。懿彼洪規,諒符舊制,藐茲中土,瞠乎莫逮。博(按,當為“傳”字之訛)曰“禮失而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不亦信耶?……博觀近譯西人之書,乃知其政教、工藝之學咸出于古經[1]514。
成氏一方面承認西學“致盛強有由然也”[1]405,另一方面又認為西學皆源出儒家經典,這就促使他致力于糅合古經與西學,從而實現其經世之目的①參見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1936年;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雷中行《明清的西學中源論爭議》,蘭臺出版社2009年版。。如成氏論重商之道云:
“懋遷有無化居”,懋遷者,貿易遷徙也。懋、貿俱假音字。化,即古貨字。……貨殖之事,古已重之,為后世商學之權輿。此言水土既平,稼穡既播,急宜廣求商務,以廣招徠而給國用也。今地球各國均用商戰,政府以兵力保護商人,商人心計最精,懋遷益廣,既逐厚利,悉力以供國家。官商通氣,上下合德。蓋今日之國勢,非商無以立國也[1]405。
按,成氏釋《皋陶謨》之“懋遷有無化居”,原本舊訓②參見: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3-94頁。,但以之與西人相較,提出重商之必要性,則告別了傳統儒家重義輕利的主張。
除此之外,成本璞在闡釋《尚書》的過程中,還十分注重與西方政治的結合。例如他極力抨擊私天下的專制制度,主張實行民主,而民主之意中國古已有之。他說:“西人民主之法,除民之害也。其法由通國公舉,及上下議院議定始,以踐位期滿則退,無所私焉。此與堯舜之禪讓有以異乎?中土效之則立成篡弒之禍,西人效之則長享治平之福,其相越豈不遠哉!蓋西人沈厚篤樸,猶有古意也。 ”[1]402在他看來,堯舜禪讓體現的正是公天下之心,但后世權奸假禪讓而行篡弒,大同之治因而喪亡,反觀西人,則更好地繼承了禪讓之本意,因而能達成治平之世。在闡釋《洪范》時,他又進而批判君主專制,推崇議院民主之制,其言曰: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此西人議院之法所由昉也。西人每有大事,必謀之卿士庶人,開院會議,順民情之向背,察眾論之異同,始敢出而行之。政行而民無怨讟,事無不舉,國以大和,順民之欲也。漢置議郎、博士諸員,有事必令會議,博求古義,譏切近事。魏晉搶攘,遂廢其職,人君恣睢于上,言官結舌于下,而天下之事乃敗壞不可勝言矣[1]408!
統觀成氏所論,其實包含了三層意思:對西人的肯定,對古經的崇敬,以及對后世背離古經的不滿。這種看法可以說始終貫穿于成氏全書。成氏既秉持這一看法,同時又有著強烈的強國致治的經世目的,所以對于學術門戶之爭是完全反對的。他在書中強調:“學術之壞,莫甚于門戶之爭。今日門戶之爭有二,一曰漢宋之辨也,一曰中西之辨也。……中西之辨,尤人所龂龂持之者也。不知西學悉出于中土,但西人益致其精,中土久失其傳耳。善學者當博甄西人之書,以補吾所矩(按:‘矩’,當為‘短’字之訛),何可徇流俗之議,從而排斥之也。故善學者無漢宋之辨、中西之辨也。”[1]511門戶之爭是經學研究的常見現象,在成本璞生活的年代,漢宋之爭已經開始趨于緩和,并非成氏首倡,但他將消弭中西之爭的觀點引入經學研究還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2 劉光蕡之《尚書微》與《立政臆解》
劉光蕡(1843-1903),原名一新,字煥唐,號古愚,陜西咸陽人。舉光緒乙亥鄉試。歷主涇陽、涇干、味經、崇實諸書院,影響關中學風甚巨。劉光蕡熱衷新學,曾倡導興辦近代工業企業和新式教育,對西方科技、政體也較為熟悉。面對西學的涌入,他認為西人所論皆中國所固有,不必妄自菲薄,而應更加重視儒經,從中尋求強國之道。劉光蕡宣稱:“今西人天文地域各學均極精深,挾其圖象,以傲我中國。我中國驚為西人創得之奇,豈知皆我三千年以前之故物。經訓不明,有關于世教誠非細矣。”[2]130這一理念正是他治經的指導思想。
光蕡著述甚多,于《尚書》學則有《尚書微》與《立政臆解》。二書雖然篇幅較為短小,但觀點皆極為鮮明。《尚書微》起《西伯戡黎》,止于《召誥》,偽古文不與焉。此書當系劉氏于煙霞草堂授徒之講義,成于1899至1902年間[3]206-207。 書中對龔、魏新說及西學知識多有采納,新解頻見。即以議院制度而論,劉光蕡的關注點就與成本璞有別。他注意到《洪范》所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認為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意思,“今西國議院以與議多寡定從違,即此意”[4]6。 對于《洪范》所言君主有大疑可謀及乃心、卿士、庶人、卜筮之說,他解釋說:“然則國家有事,君臣與民之議論,固可鼎足而三。……今西國議院,以君從其議者準若干人,其法與此同。而彼不決之神,不如中法之詳密無弊也。”[4]6-7此說固然發前人所未發,表面來看頗為新穎,但其實質卻是十分陳舊。姑且不論君主意見可抵數票之說顯然不符西方議院制度,就其所言求之卜筮、決之神靈的主張,即可見其迂腐之氣。
劉光蕡在比附西學過程中,一味求新,往往有違訓詁學的原則。如論《康誥》“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云:
“要囚”,當作“勾囚”解。釋為囚之要者,則于《多方》“我其戰要囚之”不可通矣。“要囚”,即圜土“收教罷民”,今西法之拘禁若干日有財者則以財贖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謂拘禁之,使自服念其罪而悔。五六日,罪之輕者;至于旬時,罪之大者。“丕蔽要囚”,謂拘囚已蔽其辜,則大釋之,不以為罪案,使抱終身之憾也。[4]20
按,劉氏所言“勾囚”之“勾”當系勾提、拘捕之意,衡之上下文,確實文意貫通。①參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329-1330頁。但“要”何以當作“勾”解,劉氏卻未加說明,讓人不知其所以然。至于“大釋之”云云,更是添字解經,犯了訓詁學的大忌。這一解釋的基礎既然不牢靠,那么進而再與西方司法制度相比附就是出于想當然了。
相較于《尚書微》,《立政臆解》更是旗幟鮮明地比附西學,其關注重點也更為突出。據劉氏自述,此書之所以作,乃為闡發中國舊有之憲法精意,糾正盲目崇洋之心態。此書自序云:
癸卯夏初,次兒瑞焉吾隨侍至甘,讀湘鄉周氏所譯《憲法精理》,卒業,請曰:“此西人新出之精理,吾古亦有之乎?”曰:“有之。《尚書》二十八篇闡此無余蘊矣,而《立政》一篇尤重用法,謂為憲法之鼻祖,可也。……今為西人所迫,道始大明,乃求憲法于西國,是棄祖父膏腴之業而不耕,而甘行乞于市,以求延殘喘也,豈非大可痛心之事哉? ”[5]383
與此書旨趣相同的尚有劉氏所著 《學記臆解》,其自序云:“乙未歲,馬關約成,中國賠費二萬萬。予傍徨涕泗,無能為計。……舊書重讀,新解特生。蓋身世之悲有不能自已于言者,強坿經訓以告稚子,故題曰 ‘臆解’。 觀者若執古訓以繩予,則予之戚滋深矣。 ”[2]133“光蕡受時政之刺激,試圖從儒家經典中尋求自強之道,然憲法云云并非古訓所固有,故名其書曰‘臆解’”。
為論證《立政》為憲法之鼻祖,劉氏著重對官制進行了新的詮釋:“西國憲法全以三權相維持,謂主治、行政、議法三權也。常伯如西國之君相及上議院,勛貴為之,故曰伯。伯,長也,把也,謂主持政事也。常任即西國行政之官,謂常任事也。準人則西國下議院,以國人之公論議定憲法而行之,準人情以為法也。 ”[5]384按,劉氏對三者職責的論述或離實際不遠,即如顧頡剛所言:“‘準’的意義是公平,‘準人’當是司法的長官;‘任’是執掌政務的長官,故云‘事’;‘伯’是管理民事的長官,故云‘牧’。”[6]1663然而他對憲法的理解是十分片面和膚淺的。西方實行憲法,最強調的是把憲法作為國家運行的首要準則。中國古代絕無這一類似準則,劉氏僅憑官員分工來論證憲法古已有之,失之牽強。
3 李元音之《十三經西學通義》
李元音,湖南平江人,生平不詳。著有《十三經西學通義》,該書成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共十四卷,專取十三經中與西學相合處詳論之。觀該書自序云:
夫國家當積弱之候,又值人心思亂之秋,其暴動由內地起者如彼,其風潮由外域來者如此,偽舊偽新,交相為害。然則如之何?曰:歸本于經,足以勝之。西人稱地球文明之祖國有五,而中國居首,是新莫新于中國矣。抑西國之政學紕繆者,何一非吾五帝三王孔孟所屏拒者乎!其完備者,何一非吾五帝三王孔孟所已有者乎!是中國之新,又莫新于群經矣。……意五帝三王之世,中國之學說政說,凡經籍精意,必有流傳西土者,豈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后然哉!……然則以經義發明西學,將西學準諸經義,通中外,融古今,開風氣,正人心,莫善于此[7]518-519。
由是觀之,李氏以為西學之精意皆中國所固有,欲救國家之衰微,當以經學為本,糅合經義與西學,以求強國之道。就此亦可看出,李氏對中國學術有著極為強烈的自豪感。雖然清末的中國已遠遠落后于西方,但在李元音看來,這絕非古圣賢學說已不適用于今日,“世之妄人,心醉歐美,見彼中之政治厘然秩然,遂詆中國之政治事事不如。夫謂今日中國之政治不如西國可也,謂中國古先帝王之政治不如西國,不可也”[7]542。
觀李氏于書中所引西學之書,如《泰西新史攬要》《新加坡風土記》《政治學》《經濟大意》《教育原理》《理化概要》等,達數十種之多,可知其人于西學知識并非得自道聽途說,而是確有深研。不過他對西學知識的學習和運用都有一個明確的前提,即西學中源之說,觀其所云“今觀其(西人)政治之善者,或得中國堯舜三代之意,豈彼中所能有此乎? 其自中土流傳無可疑”[7]539,這種武斷的話語鮮明地體現出他的態度。所以他雖然承認西學的巨大功用,但卻要千方百計地從儒家經典中找出其“源頭”,如論《堯典》云:
數人共一事則才絀(按,當為“詘”之訛)而事敗,一人治數事則才絀而事亦敗。欲救其失,莫若議政、行政分任其人。西國各部長以一人,其有興革,議院集議其得失,然后下之各部,令其推行,故其慮周而事易集也。西人之法如此,吾觀于虞廷之制,以為頗有合也。彼辟門之典,非議政之意乎?宅揆之使,非行政之事乎?詢謀則以僉同為善,揆度則以總理為宜,既不患其攬權,復不憂其掣肘。西人得此意矣,故自百年以來百廢俱舉也[7]540。
李元音對西方政治特點的把握是較為準確的,不過此處所論多襲自麥孟華之 《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此文于1897年發表于《時務報》,其中有云:
數人共一事則才屈而事敗,一人治數事則才絀而事亦敗。孰與人事其事之為愈乎?曰:庶務繁擾,固非一人耳目才智所可周也。如是,則莫若議政、行政分任其人。西國各部長以一人,其有興革,議院集議其得失,然后下之各部,令其推行,故慮事周而集事速。令略仿其意,修虞帝辟門之典,復漢代議郎之制,精選通達中外之士,集之內廷,熟審機宜,詳慮利弊,計議既定,下部施行,詢謀則群策無遺,措辦則一夫專制,既不患其攬權,復不憂其狹掣,數年之間,百廢俱舉[8]22。
比較李、麥二人之說,相似點頗多,惟李氏更注重從《尚書》中找尋與西學相合之處,以佐成其學術觀點。
對于憲法、議院之說,李元音亦有詳論。他說:“虞夏商周雖為專制政體,而君民同受治于天之下,則不盡專制也。夫中國古代所謂天道,猶歐洲今世所謂憲法耳。雖憲法切實而天道廣遠,不盡相同,然西國之法律亦必本于天然之理。 ”[7]542《尚書》中所言天道與西人所言憲法差異甚巨,一則宏闊幽遠,一則細密切實。李氏雖然注意到這一差異,但仍強加比附,不但流于附會,而且也無益于現實。李元音論議院之制則云:
議院于《書》有征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書》雖無議院之名,而《舜典》言“詢于四岳,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大禹謨》言“詢謀僉同”,《洪范》言“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所謂詢謀者,即謀議之謂也。言四岳,言卿士,如西國上議院人也。言庶人,如西國下議院人也。言四目、四聰,言僉同,則兼上下議院言之。蓋唐虞三代之時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意也[7]543。
此說較之成本璞、劉光蕡所論更加詳細,畢竟注意到了西方議院有上下之分。不過這也并非李元音所創,最早提出此說的似乎是梁啟超,其 《古議院考》①此文撰成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云:“問:‘子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從同之跡,敢問議院于古有征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書》曰“詢謀僉同”,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洪范》之卿士……上議院也;《洪范》之庶人……下議院也。 ’”[9]94—95
4 西政為要:比附西學的重點所在
成本璞、劉光蕡、李元音三人在以西學比附《尚書》的過程中,都自覺維護著中學的尊嚴,但其看待西學與儒家經典之關系的態度,卻有著細微的不同。劉光蕡只是認為西學所言皆中國所固有,而成、李二氏則旗幟鮮明地主張西學源出中國。李元音甚至還不厭其煩地在書中論證西學中源的途徑,如因《禹貢》言及昆侖而論曰:“夫印度為五洲之中原,昆侖寔地脈之群祖,往古圣神必多經營擘畫于其間者,不獨中國為然,即古西國亦然也。……竊意當日印度、昆侖以西,埃及希臘以東,浸淫圣澤,沾丐余波,漸有種族遷徙,以為制作萌芽。不然何以彼中政學往往與古中國相合耶?”[7]545-546李氏復以“聲教訖于四海”“西戎即序”[7]548證成此說。在之前學者提出的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說②參見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1936年。基礎上,李元音又進一步豐富了中學西傳的論據支撐。
如果撇開這一細微差異,專就書中的具體內容來看,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共性,即十分注重對政治相關內容的闡發,而這相較于之前的西學中源論來講,內容更加豐富。西學中源論自明末清初即已有之,但當時熊明遇、王錫闡、梅文鼎等人的學說多局限于天文歷法、數術儀器,較為單一。甚至光緒年間成書的《格致古微》(“此書屬草于乙未,補纂于丙申”[10]56)也只是于“光學、化學、重學、力學”[10]52等科技注意較多,于政治不加關心。反觀成、劉、李三人闡釋《尚書》,則于政治言之極詳。究其原因,或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其一,《尚書》與政治關系密切③朱熹曰:“《書》以道政事”(《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97頁)。崔述亦云:“《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于《尚書》”(《崔東壁遺書·豐鎬考信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頁)。。正如李元音所言:“古先帝王之政治莫備于《尚書》”[7]542,相較于他經,《尚書》與政治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儒經內容,各有偏重。《周易》最便于與自然科技知識相聯系,因此成本璞說:“西人之水學、火學、電學、汽學、力學、重學,皆出于《易》也。 ”[1]400而《尚書》雖然也涉及歷法、地理等,但在儒生看來,“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11]1才是其核心內容。即使《周禮》,也僅記有周一代之官制,在儒生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要遜于備載虞廷三代之政事的 《尚書》。宣統年間,楊壽昌編成《書經大義》,全書專論民政。卷首即云:
吾讀《尚書》,見其言民政至詳。立君以為民也,設官分職以為民也,《舜典》命官,箕子陳疇,物質精神兼包并舉,凡外國一切強國利民之術,及其行政組織之機關所以成今日文明之治者,吾中國數千年前早已舉其端倪,握其樞要。而莽莽神州,沈沈古籍,其理未宣,其用未究,遂使外人得以其術陵我,而吾國民亦且悔政治之苦窳,棄經學為無用。嗚呼!是豈非吾輩對先圣而有責任者與[12]1?
楊氏所謂民政,涵蓋極廣,一國之政事幾乎全部囊括在內。其原因在于楊氏主張以民為中心,國之政事皆與民相關。楊氏認為外國之機關、制度早已具于《尚書》之中。無獨有偶,光緒年間,徐天璋撰成《尚書句解考正》,亦宣稱:“斯時士競維新,高談西學,幾于人誹堯舜,世薄湯武,謂中學無補于治,不若西學進于富強。焉知平地成天,內安外攘,《尚書》實政治之基礎、西學之淵泉,五大洲中所學,無一不自我中華始哉! ”[13]3-4觀此可知《尚書》在溝通西學過程中的獨特地位。
其二,清末政治改革的呼聲極高。洋務運動的失敗使大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單純學習西方的器物、科技是無法達到強國的目的的,于是政治改革呼聲日高。甚至在洋務運動后期,鄭觀應、王韜等人就已要求仿照西法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教法度的全面變革[14]。1896年,梁啟超在所著《變法通議》中批評洋務運動說:“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進而提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15]8-10成本璞認為此前學習西人,只是“徒襲西法之皮毛”,因而主張“變法宜全變,宜舉其大經大法如官制、兵制、科舉、學校之類而先變之,而次及于細目末節。圖治有本末,收效有遲速也”[1]510。而作為士林領袖的張之洞于1898年撰成《勸學篇》,提出:“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 ”[16]2此說一方面起到了明顯的號召作用①李元音于《十三經西學通義敘》中極為推重張氏《勸學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時人已認識到學習西方政治的必要性。
雖然成本璞等人對西學的關注已擴展至政治層面,并進而提出改革的主張,但將希望寄托于2000多年前的經書,歸根結底仍未擺脫今不如古的落后觀念,本質上仍是“復歸三代”的陳舊思路。正如成本璞所宣稱的,“聊述西人之事,以古經相比附,冀以拒诐說于未興,回狂瀾于既倒,匪云用夷以變夏,良思挈今以返古”[1]515。所以仍難逃梁啟超“名為開新,實則守舊”[17]71的批評。此外,他們的一些觀點往往因襲前人,缺少自己的發明。如陳熾早在1893年為《盛世危言》作序時就提出“倚商立國,《洪范》八政之遺也。……議員得“庶人在官”之意。……罪人罰鍰,實始《呂刑》”[18]304,而其后成、劉、李三人仍不厭其煩地詳加論述,但其核心內容并未超越前人。
從經學的角度來看,后世對他們的評價也不高。傳統的經學研究不外義理、考據兩途,成本璞等人的著作則被認為乖離了正途,如倫明評《尚書微》云:“至于附會泰西學說政制,尤非詁經之體”[19]270。 所以后世的經學史著作往往將他們摒斥在外。不過,本文的主要目的并非批判這些治經方法和理論觀點,而是著眼于傳統經學家在時代巨變中的一種應對策略,以及他們之間的前后傳承。總體來看,他們畢竟向我們展示了經典解釋的多樣性,也是學隨世變的重要例證,研治經學史者對此不可不察。同時,由于清廷積重難返,他們沒能挽救其滅亡的命運,但他們主動了解西方,針砭時弊,對西學的傳播是有積極意義的,對此我們也應予以承認。
[1]成本璞.九經今義[M]//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張鵬一.劉古愚年譜[M].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1989.
[4]劉光蕡.尚書微[M]//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劉光蕡.立政臆解[M]//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6]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5.
[7]李元音.十三經西學通義[M]//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8]麥孟華.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C]//陳忠倚.皇朝經世文編三編.上海:上海書局,1902.
[9]梁啟超.古議院考[C]//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10]王仁俊.格致古微[M]//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1]蔡沈.書集傳[M].錢宗武,錢忠弼,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12]楊壽昌.書經大義[M].宣統間鉛印本.
[13]徐天璋.尚書句解考正[M]//晚清四部叢刊.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10.
[14]丁偉志.“中體西用”論在洋務運動時期的形成與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1994(1).
[15]梁啟超.變法通議[C]//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16]張之洞.勸學篇[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17]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18]陳熾.盛世危言序[C]//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19]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M].北京:中華書局,1993.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1.011
K231
A
1004-0544(2017)11-0062-05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4CZS003)。
劉德州(1985-),男,山東濟寧人,歷史學博士,江蘇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李利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