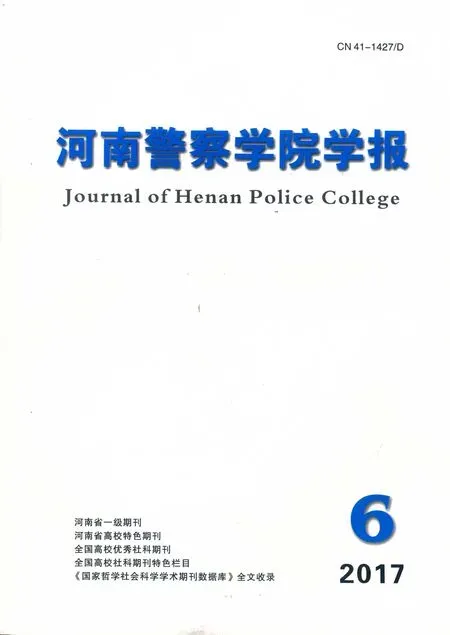風能進、雨能進、警察不能進
——警察權與住宅權關系的合理重構
沈國琴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100038)
風能進、雨能進、警察不能進
——警察權與住宅權關系的合理重構
沈國琴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100038)
在執法實踐中,經常與住宅權發生關系的公權力無疑是警察權。要合理構建警察權與住宅權之間的關系必須充分考慮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條件、時間、程序、方式、相對人的意愿等要素,甚至對于何謂“住宅”也應做審慎的判斷。完善的制度為警察執法提供合理的指引,但深入分析我國關于警察權與住宅權關系的法律制度,會發現其中尚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這主要表現在:關于“住宅”的法律用語混亂,有“住所”、“住處”以及“場所”等不同的表述;警察進入住宅的法律定位不科學,出現錯位的現象;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制度設計存在重大缺失等。針對上述問題,有必要在制度上進行調整與完善,最終推進警察權與住宅權之間合理關系的形成。
警察權;住宅權;搜查; 檢查; 監控
法諺常說:“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其意是指,哪怕是破陋的小屋,風可以刮進來,雨可以下進來,但是國王卻不得隨意進入。根據法律授權,有機會常常與住宅權相遇的是警察權,對于警察權而言,這一法諺當然適用,也更應被記住,“風能進,雨能進,警察不能進”。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高技術手段的運用,這一法諺也被賦予時代的嶄新意義,有待我們重新全面地認識與界定。檢視我國賦權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法律制度,不僅存在著面對警察權時對住宅權保護不周的問題,也存在著法律的不科學規定導致面對住宅權與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發生沖突時,無法發揮警察權的積極作用的問題。鑒于以上問題,有必要對警察權與住宅權的關系進行全面理性思考,重新構建警察權與住宅權之間的合理關系。
一、當前制度中警察權與住宅權的關系:混亂、錯位與缺失
在我國,對警察權與住宅權關系進行規定的法律規范涉及多部,其中進行明確規定的有《治安管理處罰法》《人民警察法》《刑事訴訟法》等,與這些法相呼應,公安部出臺的《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也有相關規定。除了有明確規定的法律規范之外,《反家庭暴力法》《行政強制法》中也暗含了警察權與住宅權之間的關系。綜觀這些法律規定,可以發現我國整個制度中關于警察權與住宅權的規定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用語混亂的問題較為突出
“住宅權”中的“住宅”這一法律術語在我國憲法中有明確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是,《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范中并沒有“住宅”這一術語,*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也有一處使用了“住宅”,其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了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的情形,“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體的”。很顯然,這主要是針對個人侵入他人住宅時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情形而規定的,并不涉及警察權與住宅權之間的關系。而是使用了“住所”、“住處”與“場所”等名稱。《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使用的是“住所”,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公安機關對與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可以進行檢查。……對確有必要立即進行檢查的,人民警察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當場檢查,但檢查公民住所應當出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開具的檢查證明文件”。《人民警察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保持了一致,也采用了“住所”的表述。*《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條對警察行為的禁止性規定之一是,“非法剝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體、物品、住所或者場所”。這里使用的是“住所”一詞。《刑事訴訟法》則更為獨特,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述,其第一百三十四條對搜查進行規定時,使用的是“住處”,該條規定:“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但是技術偵查措施中使用的是“場所”。該法第二編第二章第八節對技術偵查措施進行規定時未觸及技術偵查措施的對象,但根據《公安部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技術偵查措施包括場所監控,*《公安部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五十五條規定:“技術偵查措施是指由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技術偵查的部門實施的記錄監控、行蹤監控、通信監控、場所監控等措施。”顯然住宅包含在了“場所”之中。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發現,“住所”、“住處”與“場所”三個詞語的使用都試圖表達對住宅權的保護,但是它們的含義卻與“住宅”相去甚遠。先來看看“住所”,該詞的使用可以找到其明確的法律概念界定。其來自于民法。2017年通過的《民法總則》第二十五條規定,“自然人以戶籍登記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記記載的居所為住所;經常居所與住所不一致的,經常居所視為住所”。*1986年通過的《民法通則》中也有對住所的規定,“公民以他的戶籍所在地的居住地為住所,經常居住地與住所不一致的,經常居住地視為住所”。《民法總則》與《民法通則》相比,其關于住所的規定相對明確、科學,除增加了其他有效身份登記記載的居所亦為住所之外,特別強調住所是指居所,而不是指居住地。一般而言,民法上所確立的住所往往是為了確定訴訟管轄地、債務清償地或債務履行地。憲法上規定的住宅權中的“住宅”與民法上所規定的“住所”的功能指向完全不同,范圍也相差很大。民法上所規定的住所范圍極為狹窄,在我國僅為登記居所和經常居所,*何謂“經常居所”,尚無明確司法解釋。不過對何謂“經常居住地”有過司法解釋,可視為對經常居所的理解。經常居住地就是“公民離開住所地最后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醫院治病的除外”。這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的規定。2013年修改之后的《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則規定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離開住所地至起訴時已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醫的地方除外”。若以此為憲法上住宅權保護的“住宅”的范圍,顯然對于警察進入住宅的權力過于放縱。
“住處”的使用找不到明確的法律概念界定,也無司法解釋。從字面來看,這一詞簡單易懂。“住處”就是指“居住的地方”,這一詞大大拓展了住所的范圍,不論戶籍、不論有無產權、不論長住還是短住,不論多人居住還是一人居住,只要是居住的地方都可以稱為“住處”。但這只是學理解釋,由于沒有明確的正式解釋,其范圍有多大在制度上并不明確。
“場所”的使用同樣也找不到明確的法律概念界定,也無司法解釋。只有學者解釋,“將對住處、其他有關地方的搜查歸類為場所搜查”[1]。這意味著,場所包含了個人的住處,也包含了公共場所。
由上觀之,立法者在規定“住宅權”保護時術語使用較為混亂,導致法律之間的不統一,甚至出現法律內部的不統一,這對警察權與住宅權合理關系的形成是極為不利的。
(二)警察進入住宅的法律定位并不科學,出現錯位的現象
一般來講,警察權進入公民住宅至少有四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警察權以物理方式進行公民住宅進行刑事搜查。第二種情形是警察權通過技術手段進入公民住宅進行刑事偵查。利用技術手段對公民住宅進行監聽,監控當屬此類。第三種情形是警察行使行政職權對公民住宅進行檢查。警察搜查以犯罪嫌疑為前提,而警察行政檢查則主要以違法治安管理為前提,這是我國警察權二元構造模式所形成的獨特結構。第四種情形是警察因履行救助危難的職責而進入公民住宅對公民的生命與人身安全進行保護。
就這四種情形來看,前兩種均為警察實現刑事偵查的目的而與住宅權發生關系,一般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之中,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均做了相應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規定這兩種類型的目的來看,它們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中是恰當的。現有的制度存在法律定位不科學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三種情形與第四種情形。這兩種情形都規定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從對警察權的定位而言此種規定是不科學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是圍繞懲治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而做出的規定,警察住宅檢查前提也要求必須“與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有關”,但是分析第四種情形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情形中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目的是排除危險,保護住宅內人的生命與安全。諾瓦克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家公約》進行解讀時也曾提到搜查之外基于救助而對公民住宅的進入,“房屋搜查不能被濫用,以至于產生超出其所要達到之特定目的的騷擾。除了房屋搜查之外,在災難(火災、洪水、地震得等)期間進入私人住宅也完全是允許的”[2]302。顯然,在住宅內人的生命與安全遭受威脅時,警察進入公民住宅與基于對違法行為的查明而進入公民住宅的行為目的完全不同,這決定了對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性質,進入的條件、進入的程序等規定也是完全不同的。我國籠統的把兩種類型都規定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二者的差異,導致在實踐中一方面無法充分發揮警察的積極救助職責,另一方面未能有效制約警察進入公民住宅進行行政檢查這一龐大的可能侵害相對人權利的警察權。
(三)關于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制度設計存在重大缺失
警察搜查、技術監控或檢查住宅是警察進入住宅的常見行為,其目的在于針對違法犯罪嫌疑搜集證據。對于這類警察行為,制度設計上一般會考慮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要避免警察權濫用的問題,另一方面保證警察權能盡快查明案件事實,有效率地偵破刑事案件或者查明治安違法行為。制度設計往往在這些層面展開,仔細分析我國相關的制度,可以發現為實現前述目的而設計的制度尚有重大缺失:
一是對警察權濫用的約束制度設計不足。避免警察權的濫用并非絕對禁止警察進入公民住宅,而是限制警察權的任性,減少其進入公民住宅的任意性。因此,對于警察進入公民住宅往往從正當理由、正當程序、合理的時間和期限等方面進行限制和約束。住宅權是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它與其他場所,尤其是公共場所存在著重大區別。但是,我國制度設計中,并沒有特別關注住宅與其他地方的差別,未給予其特別保護。如,《刑事訴訟法》中規定刑事偵查時將“人的身體、物品、住處與其他有關的地方”并列起來進行規定,與其他有關的地方相比,住處并沒有獲得特別關注,未獲得特別的保護。*在住宅內適用技術偵查措施也有類似的情況,根據《公安部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關于“技術偵查措施”的界定,技術偵查措施包括“記錄監控、行蹤監控、通信監控、場所監控等措施”,場所監控包含了住宅監控,這里也未將住宅與公共場所區分開來。與《刑事訴訟法》相比,《治安管理處罰法》對行政檢查的規定有了對住宅的特別規定,這特別值得肯定。但是這主要是針對緊急情形下進入公民的住宅而言的,對于非緊急情形下的行政檢查并未對“住宅”與“其他場所”進行區分。
并且,對于住宅搜查、住宅技術監控以及住宅檢查制度中,正當理由的規定也是有所欠缺的,在住宅搜查中把搜查的目的等同于搜查的理由。《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搜查的目的是“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刑事訴訟法》中在規定搜查時強調其目的:“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公安部發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訴訟程序規定》中對此條進行了細化,但主要談搜查的程序,目的上仍然采用了同樣的表述,“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搜查目的是統一的,抽象的,搜查理由則應是具體的,有明確針對性的。國內的研究學者在分析我國搜查制度存在的問題時即指出,“對搜查證上應具體記載哪些事項,《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都只字未提”,“對于搜查的適用條件,其規定基本等同于立案條件,偵查人員無須‘合理根據’就可請求對懷疑對象進行搜查”[3]。場所監控中存在類似的問題,其啟動的理由在《刑事訴訟法》上僅僅規定為針對一些重罪,“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即可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這賦予了警察過多的裁量權。警察行政檢查權的行使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只要是與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有關的場所就可以進行檢查,并無檢查理由的明確規定。
警察進入公民住宅進行搜查、技術監控與檢查的程序規定也受到不少批判。我國的搜查與檢查的程序問題在于將審查、批準的權力和執行的權力合在了一起,均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行使,缺少外部的監督力量。“通過簽發搜查證啟動的搜查行為是否合法并無法律監督……,這顯然違反強制偵查法定原則。另外對搜查證的簽發存在公權力恣意的情況。在實踐中只要可迅速收集證據、有利于案件偵查,便可簽發搜查證,失去了偵查以審判為中心合理保障人權的宗旨,很可能對公民權利造成侵害。”[4]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檢查證的簽發、通過技術手段對場所進行監控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并無外在制約性力量介入。
二是,在無證搜查制度中缺失“同意搜查”制度,缺失無證檢查制度的規定,更未關注“同意檢查”制度的設計。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警察搜查的規定,未明確確立同意之下的“搜查”導致即使基于“同意”之下的無證搜查所獲取的證據也處于“非法”狀態,這忽視了住宅權人的意志,降低了警察搜集證據的效率,也人為封閉了警察與相對人耐心平和商討的渠道。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也無“無證檢查”的規定,“同意檢查”制度更未規定。其實行政檢查僅僅針對治安違法行為,當事人與警察之間的對立性并不強,征詢當事人“同意”進行檢查既節約警察資源,也尊重了當事人意愿,在制度設計時完全可以考慮。
二、警察權與住宅權關系合理重構的理論基礎
通過前述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警察權與住宅權關系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需要對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制度進行完善,予以重構。合理重構二者之間的關系建立在對警察權與住宅權恰當認識的基礎之上。
(一)住宅權作為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對普通法的要求
我國憲法上規定了住宅權的內容,明確表明了憲法的態度,是把住宅權作為基本權利來對待的,而基本權利“具有對抗國家權力的意義,要求國家權力在做出任何立法時都必須考慮不得以不正當的理由剝奪和損害這些權利,因此,基本權利的生存是通過憲法約束各種普通法律而獲得保障的”[5]。住宅權作為基本權利要獲得其他普通立法的尊重,首要的一點就應當是普通立法與憲法關于“住宅”這一概念的表述應當一致,普通法在具體化憲法上的住宅權時不能擅自縮減住宅權保護的范圍,不能降低住宅權保護的力度。如前文所述,我國相關的立法中關于“住宅”這一概念的使用是混亂的,出現了對住宅的不同表述,分別有“住所”、“住處”、“場所”等概念。這些概念與“住宅”的含義并不相同,無法承擔起保護住宅權這一基本權利的重任。從憲法與普通法的關系而言,當普通法的規定與憲法不一致時,應當服從憲法的規定,從憲法到普通統一使用“住宅”一詞更為恰當。
憲法的“住宅權”在普通法中的具體化意味著有了具體制度的保障,但是“住宅”這一概念本身若不能清晰表達,仍然會帶來諸多困惑與誤解,因此住宅權中“住宅”的范圍應當明確界定。要對“住宅”進行明確界定,就得探尋住宅權本身背后的價值取向。以美國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確定“住宅”范圍時,住宅權背后的價值取向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隨著住宅權背后個人隱私價值的確立,美國住宅權中“住宅”的范圍急劇擴大。1967年,卡茨訴美國(katz v.United States)案的判決中明確提出了“合理的隱私期待”標準,這使得住宅的范圍甚至擴張至電話亭。該案判決指出,“封閉的電話亭類似于家,而非戶外,處于其中的人享有憲法所保護的合理的隱私預期”。*Katz v.United States, 389 U.S.361(1967).總體來看,發展至今,在美國,基于個人隱私價值而形成的住宅范圍不僅包含了自己所有或者占有的住宅以及屬于住宅的附屬空間;包含臨時居住的地方,如旅館;而且還包含與外界相對隔離,個人在其中具有合理隱私期待的地方,如電話亭等。我國屬于成文法的國家,并不具備通過判例確定概念含義的傳統,不過可以通過憲法解釋或者法律解釋的方式推進概念的明確化、具體化。我國“住宅權”中“住宅”的范圍的確定也需要探尋住宅權背后的價值。從我國憲法文本的整體內容來看,支撐住宅權的是對住宅內人的保護,而非對住宅這一“物”本身的保護,關于住宅這一私有財產“物”的意義上的保護是放在憲法第十三條關于“財產權”保護的框架之內的,這就形成了“財產權”與“住宅權”保護價值的分流,財產權保護房屋的財產價值,住宅權保護房屋之內人的安全、自由、尊嚴或者隱私等。我國現行憲法制定時草案修改說明對住宅權背后的價值基礎交代得非常清楚,彭真同志1982年曾經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指出:“為了切實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草案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和誹謗;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侵入。”*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真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其中對住宅權的保護目的作了明確的說明。in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302.htm.從這一說明可以看出,“人身權利和人格尊嚴”是住宅權的價值基礎,無論怎樣的住處,是長期居住的,還是短期棲身的,無論是富麗堂皇的,還是破敗不堪的,身居其處,其中都安放著個人的安全、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尊嚴。這也就意味著,住宅是給人以合理的安全、自由與個人尊嚴的預期的地方。這些價值基礎應成為我國判斷“住宅”的核心標準。另外,住宅本身“物理”上所具有的“與外界相對隔離”這一得到普遍承認的標準也是重要的判斷依據。基于“個人的安全、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尊嚴的合理期待”以及“與外界相對隔離”這兩個標準,電話亭雖未必能納入其中,但至少以下場所可以納入“住宅”的范圍:自己所有或者自己以租住、借用等方式占用的房屋;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等;*2000年11月23日發布的《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問題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指出:“入戶搶劫”中的“戶”是指“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在確立住宅范圍時,這一解釋能夠提供極好的思考路徑。用于個人生活時段的商住兩用場所;個人投宿的賓館等。
(二)住宅權的“權利”屬性之于制度設計的意義
從憲法角度而言,警察進入公民的住宅必須有正當理由與正當程序。在法律明確規定的正當理由、正當程序之外,也就是“有證進入”公民住宅之外,是否制度上也有必要設計“同意”進入這類“無證進入”公民住宅的情形。在很多國家的制度中,“同意”本身具有替代正當理由與正當程序的作用,美國聯邦法院在 1921 年對 Amos v.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決確立了此種觀念,認為經被告同意而進行的搜查無須具備憲法第四修正案中要求的司法令狀和正當理由。*Amos v.United States,255 U.S.313(1921).那么,為什么當事人的“同意”會為警察進入住宅作“合法性”背書呢?有學者對此進行了學理上的總結,認為有三種理論上的論證,一是無合理隱私期待說;二是權利拋棄說;三是規范政府行為說。*這三種理論的立論在于:無合理隱私期待說強調相對人同意偵查機關搜查后,相對人對隱私權的合理期待已經喪失;權利拋棄說則認為相對人同意意味著對憲法第四修正案賦予的不受不合理搜查、扣押這一權利進行了處分,即拋棄了該項權利;規范政府行為說認為,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進行不合理的搜查扣押,其目的在于防止政府的違法搜查行為侵害公民個人的合法權利,而在個人同意的前提下,公民出于自愿,同意或授權警察搜查,沒有傷害公民隱私或人格,所以政府的行為并非不合理的搜查,不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應當被認可。參見宋志軍: 《同意搜查制度比較研究》,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這三種理論均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均具有解釋力不足的問題。“無合理隱私期待說”與“權利拋棄說”的理論依據基本類似,都試圖從個人權利可以放棄的角度進行論證,但是個人放棄權利是否就一定意味著賦權公權力進入公民住宅呢?這種邏輯關系并非必然;“規范政府行為說”的解釋力也不足,個人的同意減少了公權力與個人之間的對抗關系,但無論如何都無法直接規范政府的行為。在警察進入公民住宅時建立同意制度,其實是對公民的權利的尊重,這種權利中包含了授予他人進入住宅的權利,其實是權利的授予,而非權利的拋棄。這種制度的設計是對公民自主意識的尊重,是對公民個人的合理預期的尊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警察權的合法進入是“制度預期之外個人預期的產物”,是公民對公權力的授權。
根據憲法原理,一般所涉及的“正當理由”與“正當程序”是向當事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制度,通過整個制度預期實現每個個體的合理預期;在這之外,同樣允許只基于個體能力而形成的“個人預期”,當理性的個人通過自己判斷和分析同意警察進入公民住宅時,其應當能夠預見到這種同意而帶來的后果,形成個人的合理預期,其實這就等于是用自己的授權代替了有權機關的授權。這是警察權在住宅主人同意之下能夠正當進入其住宅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因此形成了同意之下“無證搜查”或者“無證檢查”為合法行為的制度。“無證搜查”或者“無證檢查”制度不僅充分尊重相對人的自主意志,而且能夠極大地提高警察行為的效率,這種制度設計對于疏解現實中警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警察權作為特殊公權力形式與住宅權的關聯性
警察權是一種特殊的公權力形式,在所有行政權中具有最強的強制力,甚至可以對個人的人身進行強制,并享有配備與使用武器的權力,這使得警察權具備利用其強制手段保護公民的生命、人身安全以及財產的能力,但同時另一方面,也帶來人們對警察權濫用的極大恐懼,一旦濫用,公民的權利就可能會遭受致命的打擊。因此,對其進行合理的約束與限制,保證其造福于人們而不是威脅人們的權利便成為必然。正是警察權的這些特性,使其經常與公民的住宅權發生關系。這種關系往往形成兩種不同的類型,基于不同的類型應考慮不同的制度設計。
第一類型是警察權基于保護人的生命與安全的職責而進入公民的住宅。我國《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警察因此需要承擔救助的職責,現實生活中需要警察救助的情形非常多,因此需要區分不同的情形進行具體分析。一旦與住宅發生關系時,警察在面對公民救助要求時就需要謹慎平衡住宅權與生命權,人身安全權以及財產權之間的關系,很顯然,與住宅權相比,生命權與人身安全權的利益要遠遠超過住宅權,但是財產權的利益則低于住宅權。在生命與人身安全遭受巨大危險時,警察應當承擔起進入住宅進行保護的職責。并且從現代社會公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來看,個人的生命與人身安全獲得公權力,主要是指警察權的保護已經成為公民權利的內容之一。在傳統社會,雖然國家為維護社會秩序,在排除對個人生命、人身安全造成的危險因素方面享有了壟斷權,但是國家并不因此而承擔保護個人生命與人身安全的責任,法定的國家職責尚未被提出來,就國家而言國家職權與國家職責并不統一,因此,個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保護尚未作為權利形式而存在,充其量是國家權力行使的副產品而已,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反射利益。但是進入近代后,人們不僅關注克服龐大的國家權力侵害個人權利之虞,而且開始關注個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保護問題,要求國家對個人生命安全、人身安全負有安全保護的職責,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保護已經成長為一種權利,而不再是一種副產品。這就意味著,當住宅內人的生命、人身安全遭受威脅時,警察進行救助成為法定職責,如果不履行該職責,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超級瑪麗”案就真實地反映了這種觀念。*“超級瑪麗案”的具體過程如下:“超級瑪麗”演唱組合是由兩位女孩羅驚與韓萱組成的。2006年3月21日凌晨0時30分左右,兩女孩的朋友報警兩女孩可能在出租屋內煤氣中毒,警察接警后不清楚出租房內的具體情況,未敢貿然強行進入房間,直至當日清晨8時許通過電話聯系上房東,在房東通知下由持有鑰匙的鄰居打開屋門。發現屋內彌漫大量煤氣,羅驚、韓萱已經昏迷,經醫院診斷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最終結果是,一人死亡,一人成為植物人。超級瑪麗的家屬認為警方存在違法不作為,未能對二人進行及時救助導致二人媒體中毒事件發生。后公安機關向二人家屬支付200萬元補償款,家屬撤回了對公安機關的行政訴訟。具體參見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7/11/id/ 276239.shtml;以及http:// blog.sina.com.cn/ s/blog_492a2cb401017t30.html,訪問時間2016年10月1日。總之,無論從警察機關的職責來看,還是從公民生命權、人身安全權與住宅權發生關系的優先性保護特征來看,以及從生命權以及人身安全權的權利屬性來看,當住宅內人的生命與人身安全遭受危險時,警察有權也有責任進入住宅進行救助,并且由于是在緊急情形下對生命、人身安全的保護,因此,應當更多強調效率,在程序設計上不宜復雜,并尊重救助現場實施救助的警察的判斷。
第二種類型是為偵破刑事案件或者查明行政案件而對住宅展開的搜查、檢查或者技術監控。這種類型中,警察進入公民住宅往往是因為有違法或者犯罪嫌疑需要進一步核實、查證,雖然這里目的涉及對犯罪違法行為偵破或查明的國家利益,但是這種國家利益實現的邏輯是:警察進入住宅是建立在存在線索或者證據顯示有必要進入住宅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警察的主觀臆斷或者任意的猜測。如果這樣,個人就失去了構筑與外界相對隔離的宅的意義。如前文所言,住宅的背后包含諸多人類社會基本的價值要求,諸如個人安全、個人自由與個人尊嚴等。無論如何,支撐住宅權的這些價值都要求警察必須審慎地進入公民的住宅,特別要求比進入其他場所更加慎重。這種慎重的要求體現在法律上就是必須有正當的理由,正當的程序以及合理的期限。
隨著高技術手段的發展,刑事案件偵破時技術手段的使用尤其值得關注。技術手段突破了傳統肉眼所見不可再現的特點,其所形成的電子資料不僅可以遠距離為他人當時所察看,而且還可以儲存起來,不斷地重復、再現,甚至可以放慢、可以定格,因此,各種細節都可被反復展現,反復收聽。另外,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電子資料的復制和傳播變得越來越簡便,只要小小的一個U盤就可以把可視、可聞的資料全部傳播出去。并且隨著網絡的普及,一旦電子資料被上傳至網絡空間,其傳播廣度和速度往往極為驚人,不受地域、距離、時間等諸多條件的限制,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傳播出去,進入到網民的視野中。由此看來,住宅的技術監控與傳統的住宅搜查相比,有自身的特點,并且一旦濫用會給個人帶來更大的傷害。因此,一方面,對于住宅的技術監控應當考慮其自身特點,形成與之相應的約束警察權濫用的制度,如監控所獲取的視頻或者聽頻資料的保存、使用等都應當有專門的規定;另一方面,正確認識技術手段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對警察采用住宅監控的行為給予更為嚴格的控制。
三、警察權與住宅權關系合理重構的路徑
針對我國當前制度中不合理的警察權和住宅權關系,應當重新調整和完善。在這之前,首先應當實現憲法與普通法中關于“住宅”名稱與范圍的統一, 拋棄“住所”、“住處”以及“場所”等詞語的隨意使用,統一使用“住宅”一詞,并作出必要的解釋。
在“住宅”一詞使用統一的前提下對相關制度進行調整和完善,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警察履行進入住宅救助生命、人身安全救助職責的制度重構
現有制度關于警察進入住宅救助生命、人身安全的職責的明確規定出現在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中,其中規定的“立即檢查”即包含此種情形,要求“檢查公民住所的,必須有證據表明或者有群眾報警公民住所內正在發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或者違法存放危險物質,不立即檢查可能會對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財產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從其規定的內容及其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位置來看,這里立即檢查的規定是對《治安管理處罰法》中關于對住宅進行“立即檢查”規定的具體化,明確了對住宅進行“立即檢查”的法定條件。很明顯,其中關于為保護個人人身安全目的而進入公民住宅的行為與住宅行政檢查行為不同,這種行為并非基于當事人的違法行為或者違法嫌疑而啟動的,純粹是警察基于“救助”職責而展開的。因此,將其與行政檢查行為混同在一起極易造成制度上的混淆。因此,筆者建議對于警察因保護公民生命、人身安全進入公民住宅進行救助的行為應當放在《人民警察法》中規定,而不是與其他住宅行政檢查一起規定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警察進入住宅進行救助是因為住宅內人員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遭受危險之時,處于緊急情形之下,因此,程序上的設置不能太過復雜。《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立即對住宅進行檢查時特別強調其程序上的嚴格性,要求必須出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開具的檢查證明文件。這其實混淆了住宅內緊急救助與基于違法事實查明的行政檢查行為之間的區別,對警察權造成了不恰當的羈絆。這種無助于警察權制約的“檢查證”制度往往會延誤時間,錯過進入住宅救助生命的最佳時間。約束住宅內緊急救助的核心是“啟動條件”的合理設置,該“啟動條件”應當包含兩方面的內容:(1)當事人報警或第三人報警,或者有證據表明公民住宅內正發生公民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案件或者事件;(2)第三人報警的內容或者證據顯示的線索使警察獲得合理的懷疑,懷疑住宅內的人正在遭受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威脅。
當事人自己報警尋求救助的情形相對較為簡單,可看作是當事人對警察進入住宅的授權。
第三人報警求助情形較為復雜,警察是否有權進入公民的住宅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主要分析要素包括三方面,一是報警救助的對象是什么;二是報警救助者與住宅之內的人員是什么關系;三是所獲得的信息是否能夠使警察獲得合理的懷疑,懷疑住宅內的人正在遭受生命安全或者人身安全的威脅。若涉及住宅之內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之外的其他權益,則不能只根據求助人的求助而進入公民住宅;若涉及住宅之內人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則必須盡快查明申請者身份,弄清申請救助者與住宅之內人員的關系,分析評判相關信息能否形成合理的懷疑。為保證第三人慎重對待自己報警所涉內容的真實性,應當履行書面簽署申請書的手續,申請書中寫明申請人與住宅之內人員的關系,申請所依據的事實以及不實報警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第三人書面申請不僅可以保證警察進入公民住宅的理由具有正當性,保證其并非基于任意的猜想而進入公民的住宅,而且可以保證求助者慎重啟動救助程序。此種情形之下其實存在著生命安全、人身安全與住宅權之間的沖突問題,這種沖突的解決應當遵循“生命安全、人身安全優先”的原則,“救助中的情形千差萬別,理論的想象永遠都難以趕得上實踐的豐富,但無論什么樣的差別,都必須恪守生命安全第一的原則。如果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同時需要救助,則優先救助生命”[6]。
無任何人申請救助,但是有證據表明證公民住宅內正發生公民生命安全、人身安全的案件或者事件的情形,則要求警察必須有充分的證據線索,并且這些證據線索不能僅僅是使人懷疑住宅內人的生命、人身安全遭受威脅,而是應當使人確信這一點。因此,對其證據的證明力要求非常高,也意味著在這種情形下,警察判斷是否進入公民住宅進行救助必須特別慎重。
(二)“同意搜查住宅”、“同意檢查住宅”的制度設計
在無證搜查或者無證檢查制度中,相對人的同意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警察搜查的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法》中關于警察行政檢查的規定,均未明確確立同意之下的“搜查”和同意之下的“檢查”制度,導致即使基于“同意”之下的搜查或者檢查所獲取的證據也處于“非法”狀態。很多國家刑事訴訟法之中設計了“同意搜查”的制度,*具體各國關于同意搜查制度的內容可參見宋志軍: 《同意搜查制度比較研究》,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已成為警察“無證搜查”的重要內容之一。筆者建議,應當學習這一制度,在相關的法律制度完善中,應當給“同意搜查住宅”、“同意檢查住宅”制度一席之地。
同意之下“無證搜查住宅”或者“無證檢查住宅”制度中相對人的“同意”是極為重要的,相當于相對人發去的“授權”指令,因此對于“同意”這一意識表示必須確定其明確的判斷依據。對于搜查制度中同意之下的搜查,學界多有探討,提出同意必須滿足的條件,“(1)警察必須首先向預搜查者表明身份和搜查意圖。(2)同意必須是自愿的而不是受脅迫的,無論這種脅迫是明示的還是暗示的。(3)公民個人的同意必須是明智的而不是受欺騙的”[7]。這基本上能夠說明“同意”的核心內容,一方面,要求警方必須承擔告知義務,這能夠保證相對人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形下做出的決定;另一方面,要求相對人的“同意”必須是自由、自愿、自主地做出的理性判斷,不是在受到公權力的“壓力”、“威脅”、“欺騙”、“誘惑”等情形之下做出的。除此之外,還應當要求做出理性判斷的相對人必須是有判斷能力、意識到行為的意義和后果并且能夠承擔行為后果的理性的個體。符合這些條件,才能保證基于對相對人自主意識尊重基礎上的“同意搜查”制度不違背其制度設計的本意。當然,這些要求同樣適用于警察行政檢查時獲得相對人的同意而進行的檢查行為。
當然,在“同意搜查”、“同意檢查”的制度設計中,應當保持對非自愿“同意”以必要的警惕,設計出周嚴的制度體系,避免其淪為警察任意進入公民住宅的堂皇借口。
(三)警察以物理方式進入公民住宅進行“搜查”或者“檢查”制度的完善方向
警察以物理方式進入公民住宅進行“搜查”或者“檢查”時,最需要警惕的是警察的任意“搜查”或“檢查”。為了避免警察的任意而為,正當理由、正當程序、合理時間都是制約警察搜查住宅或者檢查住宅制度中重要的內容。我國雖然在相關制度中也涉及了這些內容,但規定仍非常粗陋,難以適應對住宅權保護的需要,因此,應在相關制度中予以完善。
從正當理由來看,我國住宅搜查制度中,把“搜查目的”等同于“搜查理由”,導致啟動條件過于寬泛,達不到制約的效果。從美國、英國的發展情況來看,有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美國要求啟動搜查的條件是必須具有“合理的理由”,即“當官員掌握有可能合理地相信其真實的信息,根據這些信息所獲悉的事實和情況本身足以使有合理謹慎的人相信犯罪已經發生或者正在實施時,合理根據就存在了”。*Carroll V.U.S., 267U.S 132, 162(1925).對于住宅搜查而言,“合理的理由”的“合理”要求更高,美國刑事訴訟法學者阿希爾·里德·阿馬教授曾對此作出過解釋,比如“對機場的搜查,考慮飛機的爆炸,——有時0.1%就夠多了——而其他時候100%仍是不合理的。(即使政府確切地知道,誠實的亞伯的商業記錄在他的臥室中,包含了一個關于貝蒂和卡羅爾之間的訴訟的記錄,一項與傳票相反的突襲搜查——將典型地是不合理的。)常識告訴我們,除了可能性之外,要注意發現下列問題的重要性,即:政府要尋找什么,搜查的侵擾性、搜查目標的確定性,以及達到搜查目的的其他可利用的方式,等等”[8]。可見,這種更高比例的“合理理由”要求警察在進入住宅時應進行多方面分析和判斷,保證其進入住宅的理由是充分的,合理的,不過這往往賦予警察較大的裁量權。英國則收縮了警察的裁量權,針對住宅搜查確立了獨特標準,“對搜查人身或車輛采用了‘合理的根據懷疑’,對住宅采用了‘合理的根據相信’。……‘懷疑’與‘相信’是對搜查理由規定了不同程度的證明標準,‘相信’比‘懷疑’證明標準高”[9]。“合理的根據懷疑”與“合理的根據相信”表現出證明標準上的極大的差別,引起懷疑與讓人相信相比,二者所需要的證據信息相差較大,前者只強調警方所掌握的信息線索能讓有理性的人懷疑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犯罪就可以了,而后者則要求信息線索不僅讓人懷疑,而且在懷疑的基礎上繼續證明,直至達到說服有理性的人相信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犯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機動車和人的可移動性,若要等到“合理的根據相信”才能達到搜查標準的話,機動車和人可能早已杳無蹤跡。而住宅則不同,其不僅不能移動,而且其中包含了居于住宅內的人的自由、安全、尊嚴與隱私等價值,對其搜查必須特別地慎重,達到“合理的根據相信”的標準能夠減少對住宅內的人的侵擾,同時也不必顧慮住宅移動而失去搜查的對象。
我國住宅搜查制度也應當逐步確立搜查理由制度,減少警察啟動搜查的任意性。英國的制度對我國警察而言,要求過嚴,恐一時難以適應,學習美國的經驗建立“合理的理由”制度是可以被接受的。要求警察在客觀上收集到一定的證據,并在此基礎上使一般理性人認為可能或者大致相信,懷疑犯罪已發生或正在實施時,警察才可以進行住宅搜查。這應當是對警察進入住宅進行搜查的基本前提,否則警察憑什么理由進入住宅?
從正當程序來看,我國住宅搜查與住宅檢查的程序問題在于審查、批準的權力和執行的權力合在了一起,均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行使,缺少外部的監督力量。不獨住宅搜查和住宅檢查存在此問題,其他類型的搜查與檢查均在這方面受到批判。在程序上,學界多主張建立“司法令狀”制度。這種改革思路對住宅搜查或者住宅檢查尤其是重要的,由獨立第三方進行事前審查、批準,這能有效減少警察權對公民住宅的隨意侵入。
從住宅搜查時間或者住宅檢查時間來看,很多國家對物理方式侵入公民住宅在時間方面有法律限制。有些國家直接在憲法中規定夜間住宅的特別保護,如玻利維亞、危地馬拉等國家的憲法;有些國家則在刑事訴訟法中在規定搜查時明確規定對其夜間搜查住宅的限制,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夜間不得搜查住宅,要求搜查住宅必須在早 6 時之后至晚 21 時之間進行。*當然,這些國家夜晚不得進入住宅進行搜查進行是原則規定,也規定例外情況可以突破。如法國規定的例外是從白天已經開始的搜查,或從房屋內發出呼救以及法律有規定的某些特殊情況。我國現行法律對于住宅的夜間保護問題均未置一詞,沒有明確的法律立場。對此問題我國的相關制度設計也應當有所考慮,設計與保護住宅內“個人的安全、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尊嚴”相關的搜查制度和檢查制度。
(四)警察技術監控公民住宅制度的完善方向
在人類立憲之處,尚未出現侵入住宅的高技術,因此當這類技術出現并被公權力所采用時,基于憲法基本權利的要求對其進行約束和防范成為必要,國際人權研究專家曼弗雷德·諾瓦克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家公約》第17條第1款提供的保護針對的是對住宅的任意或非法干預。“任何未經被影響的個人的同意而發生的,對可以解釋為‘住宅’這一術語的范圍的侵犯都屬于干預。這適用于強行或者秘密的侵入以及電監視行為、監聽裝置、隱藏的錄像機等等。”[2]301對于公民住宅的技術監控進行約束和防范需要考慮技術手段的特殊性,設置相應的制度。技術手段一旦被濫用,會給公民權利帶來更大的危害。正是基于這種觀念,一般對技術監控,尤其是針對住宅的技術監控設置更為嚴格的制度控制。
從各國的發展狀況老看,針對住宅的技術監控啟動要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法定重罪;二是“窮盡原則”。如德國《基本法》第13條第3項規定,“根據事實懷疑有人犯法律列舉規定之特定重罪,而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查明事實者,為訴追犯罪,得根據法院之命令,以科技設備對該犯罪嫌疑人的住宅進行監聽”。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規定了技術偵查措施啟動的條件,對“法定重罪”才可啟動的原則予以確立。*《刑事訴訟法》區分了公安機關偵查和檢察機關偵查的不同,規定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必須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才可啟動技術偵查措施;檢察機關偵查的案件必須是“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才可啟動技術偵查措施。但是,“窮盡原則”并未能確立,僅僅規定“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即可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這一規定受到學者的批判,被認為,“這一用語含義過于寬泛,可以理解為采取其他偵查措施無效、低效而‘需要’技術偵查時,甚至也可以理解為我國公安機關采用技術偵查措施不受最后手段原則的限制”[10]。與其他偵查措施相比,技術偵查措施帶給個人的壓力、恐慌、不安全感更為強烈,對住宅的技術偵查給人帶來的不安與恐懼更甚,這也是各國強調“窮盡原則”的前提所在。我國針對住宅的技術監控制度的完善也有必要考慮增加“窮盡原則”,即必須窮盡了其他偵查手段仍然無效或者低效時才可以使用技術偵查手段。
至于通過程序控制警察對住宅技術監控措施的使用,則與以物理方式進入公民住宅的程序要求類似,建立獨立于警察的第三方控制的方式更有助于約束警察權的濫用。
另外,考慮到進入公民住宅的監聽或者監控具有不間斷、可持續性特點,如長期使用則會獲取被監視對象方方面面的信息。通過限制監聽或者監視的時間長度來對警察權進入公民住宅進行限制成為至關重要的。從各國的規定來看,監聽或者監視均有時限上的限制,但是對住宅內監聽或者監視則在時限上要遠低于其他場所的監聽或者監視。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一般監聽為3個月,但是對私人住宅談話進行監聽的最長期限則縮短至4個星期,當期滿后,采用監聽措施的情形若依然存在,雖可以申請延長,但是每次可以申請延長也不得超過4個星期。我國當前的制度僅規定,技術偵查的首次適用期限為三個月,根據偵查的需要可以多次延長,并無最長適用期限的限制,也沒有公民住宅監控時限的特別規定,對于住宅內人的自由、尊嚴與隱私保護不夠充分。隨著技術手段的發展,使用技術手段對公民住宅進行偵查較之以前愈來愈多,有必要及時針對住宅這一特殊的空間,規定較短的監控期限,以避免公民的住宅權遭受過度侵擾。
[1]劉方權.人身搜查和場所搜查的比較——域外法治的簡單考察[J].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05(3):25-29.
[2][奧]曼弗雷德·諾瓦克.民權公約評注(上)[M].畢小青,孫世彥,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3]李超峰,邢永杰.我國搜查制度的運行現狀、問題及完善[J].江西社會科學,2014(2): 158-164.
[4]王弘寧.我國搜查與扣押制度的完善——從中美搜查與扣押制度比較研究談起[J].法學雜志,2016(7):134-140.
[5]沈國琴,田雙銘.民法參照背景下憲法的根本法屬性分析 [J].晉中學院學報,2016(5):54-60.
[6]程華,沈國琴.警察行政救助權的有效行使及法律規制探析[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95-102.
[7]劉方權.論搜查[C]//陳興良.刑事法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510.
[8]阿希爾·里德·阿馬.憲法與刑事訴訟法基本原理[M].房保國,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60.
[9]劉金友,郭華.搜查理由及其證明標準比較研究[J].法學論壇.2004(4):9-20.
[10]王東.技術偵查的法律規制[J].法學研究.2014(5):273-283.
(責任編輯:岳凱敏)
GiveAdmittancetoAllButthePolice——ReasonableReconstruc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olicePowerandHousingRight
SHEN Guo-qin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8, China)
It is police power that often relates with the housing right in law enforcement.When we try to set up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the police power and the housing right, we should consider the condition, time, procedure, method and the will of the relative person.It should be prudently judged what is house.The perfect system can guide the police to reasonably enforce the law.There are many imperfections about the syst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power and the housing right.First, the terminology of house which is used in the common law is called confusedly as “domicile”, “dwelling” or “place”.Second, the nature of the conduct of the police entering the house is inaccurate.Third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the system of the police entering the civil housing.In order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power and the housing right.
the police power;the housing right;search;inspect; monitor
2017-09-12
司法部課題“憲法規制下的警察權研究”(16SFB2012)的階段性成果。
沈國琴(1972— ),女,山西屯留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憲法學、行政法學。
D631
A
1008-2433(2017)06-00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