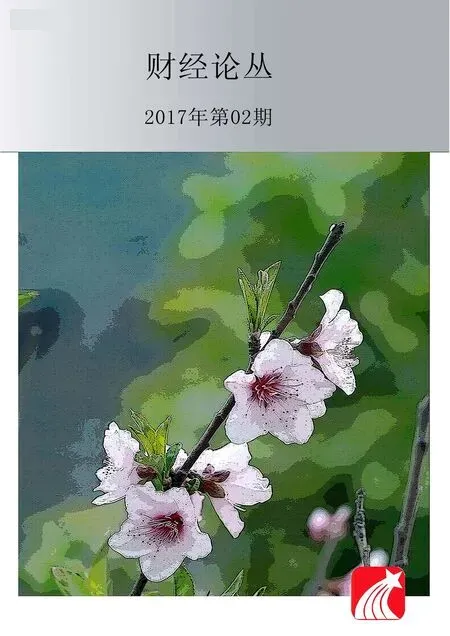跨區梯度轉移抑或域內產業深化
——基于2003~2013年全國和長三角分區數據的產業轉移分析
張明之,謝 浩
(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3)
跨區梯度轉移抑或域內產業深化
——基于2003~2013年全國和長三角分區數據的產業轉移分析
張明之,謝 浩
(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3)
本文對2003~2013年的低梯度地區的制造業行業中類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產業梯度是影響區域產業轉移的第一變量。而進一步關于長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細化數據顯示,在空間方面,同梯度地區之間邊際產業的域內轉移往往強于域外轉移;在時序方面,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早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在結構方面,高、低梯度地區因產業轉移整體上步入產業結構上升通道,特別是制造業在高梯度地區呈現明顯的逆梯度集聚或轉移趨勢。為此,高梯度地區可通過漸次擴大區域經濟聯系的方式拓展域內產業空間轉移范圍,低梯度地區可通過有所側重地構建地區產業高地的方式為向域內更低梯度地區轉移產業積蓄產業勢能。
產業轉移;長三角;產業梯度
一、問題的提出與國內研究現狀
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第一批次大規模的全球產業轉移,使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等相對后發卻擁有顯著比較優勢的國家或地區通過大量承接來自北美、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邊際產業而相繼成為新型工業化國家。80年代全球產業轉移的重心開始向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等更具比較優勢的國家或地區傾斜,一大批新型經濟體應運而生。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特別是長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無疑成為這一波次全球產業轉移的最大接受地區。但自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國內供給方面的勞動力、土地成本等比較優勢正加速削弱,需求方面的全球市場持續疲軟、動力仍不足,國內和國際多重因素正加快長三角等先發地區邊際產業外移。
關于產業轉移的早期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以國際產業轉移為視角,經典的產業轉移理論主要包括赤松要的“雁陣模型”理論、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1][2],這些理論較為系統地解釋了國際產業的梯度性轉移趨勢,即邊際產業“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漸次轉移”的一般規律。
我國學者對產業轉移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既有關于我國東部地區對接全球價值鏈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和立足國內價值鏈轉移域內邊際產業的模式選擇方面的思考[3],也有僅以長三角等先發地區內部“中心-邊緣”結構為出發點分析上海與浙江、江蘇之間“雁行形態”的研究[4],而從整個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結構出發解讀產業轉移特別是制造業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可能性和現實障礙的研究則主要于2008年之后密集出現[5]。在早期的研究中,結合我國產業經濟發展實際對產業轉移進行定性分析的居多,2010年之后的研究更加注重從實證層面對產業轉移進行分析。雖然國內學者關于產業轉移的研究的起步總體較晚,但從概念界定、影響因子甄選、模型構建、轉移效應分析到發展前景展望的討論和研究還是比較全面的,這也為本文進一步立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特點研究產業梯度轉移的特征和模式等提供了基礎。
關于產業轉移的概念界定,本文主要引用陳剛(2006)關于產業轉移的宏觀概括:一定時期內由于區域間產業競爭優勢消長轉換而導致的產業區位的重新選擇的結果,也是產業發展在空間上的重構[6]。相比較于部分學者狹義地認為產業轉移只是產(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部分或全部的遷移,產業生產份額在產業上和區位上的相對消長更能體現產業轉移的實際經濟意義。基于此,多數研究以赫芬達爾指數、區位熵和產業絕對份額來測度產業轉移,但在區域分類、數據口徑和時間劃分等方面的選擇側重不同,得出的研究結果也不盡相同。Wen(2004)、馮根福(2010)等人認為東部地區產業沒有轉移,劉紅光(2011)也指出產業轉移并不明顯[7]。楊亞平等(2013)基于對全國大中城市2000~2010年的數據分析,認為我國東部地區的產業外移趨勢明顯,而中部地區在承接產業上表現突出[5]。陳建軍(2007)則強調東部地區內部的產業轉移更加明顯(如省內轉移現象)[4]。劉紅光等(2014)的研究基于2007~2010年省際數據,指出產業轉移因為產業的不同呈現不同的產業轉移方向、不同的轉移模式和不同的轉移速度,但總體符合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的規律[7]。結合新地理經濟學的發展,胡安俊和孫久文(2014)在利用三位數制造業細化數據對中國四大地區的“產業轉移量”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察,認為高替代彈性產業轉移先于低替代彈性產業,在轉移方式上前者傾向于擴展擴散式轉移,后者傾向于等級擴散式轉移[8]。
在產業轉移概念方面,本文傾向于陳剛等人關于產業轉移的定義,認為廣義的產業轉移表現為產業生產份額在產業和區位上的相對優勢的消長。既然是產業優勢的相對性的消長,必然包括邊際產業向外擴散的可能性和部分產業在互動過程中進一步集聚的可能性(后者的典型代表可能來自高端制造業及與生產性服務業聯系緊密的制造業)。為更真實地反映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情況,一方面,在數據口徑上實行漸次收窄,數據處理從制造業21個行業大類逐漸向176個行業中類細化(后者與胡安俊的169個三位數制造業的數據口徑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不再限于現有研究在地理空間上的東部、中部和西部(或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的區域劃分方式(因為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也非勻質經濟結構,區域梯度高低有別),借鑒錢納里等人關于工業化進程的劃分方法,對我國30個省(市)(除西藏外)進行產業梯度分區,并在關于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分析中進一步深入到對三省一市33個市級地區的梯度分類,以此在更加細化的數據分析中考察我國區域產業轉移的一般規律。
二、理論基礎與基本假設
(一)產業梯度轉移的基本設想與梯度劃分
世界經濟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在國際分工中體現為“中心-外圍”的二元結構。中心和外圍地區主要通過全球價值鏈實現產業分工和經濟互動。在經歷產業或產品的成熟階段之后[2],“中心”地區的邊際產業便會向后發地區“選擇性”轉移。此后,相關產業在“外圍”地區重新經歷一個產業(品)生命周期,并逐漸向域內次外圍地區“擴散”。產業的區域轉移往往遵循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的規律。為此,本文首先對照霍利斯?錢納里等(1988)的工業階段劃分標準[9],根據2010年全國30個省(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將區域經濟的產業梯度由高到低分為梯度Ⅰ、Ⅱ和Ⅲ區*鑒于我國的人口統計每五年普查一次,本文采用各省(市)的2010年地區生產總值除以2010年年末地區人口數量作為區域經濟梯度劃分的標準。。在理論上,梯度區之間相鄰性與地理空間上的毗鄰性不相關,如環繞上海等經濟中心區的次梯度地區在經濟空間上可能是江蘇、浙江,也有可能是山東等地。具體劃分詳見表1所示。

表1 2010年我國主要省(市)的區域梯度劃分
注:* 用來說明內蒙古因為資源型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突出位置,在分類處理時對其進行了“降級”處理,其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本應在Ⅱ區。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
假設一:區域經濟中心地區的邊際產業按照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依次轉移,也是區域產業轉移的主要趨勢。
(二)產業梯度轉移的影響因素
邊際產業的梯度轉移源于中心或高梯度地區要素成本、市場競爭和產業需求等因素對產業的擠出效應,從而為產業的區域梯度轉移創造了供給。因為利潤空間不斷壓縮、市場份額縮小,一部分產業要素轉而向更有比較優勢的經濟空間尋找生存可能。低梯度地區的經濟規模、要素成本、人力資本和產業基礎等作為承接產業轉移的條件對不同產業都有吸引力,程度高低可能不同[10]。成本導向型產業對要素成本更加敏感,市場導向型產業對本地市場和穩定的域外市場的規模大小更加關注。但如何轉移、轉移量的大小不僅決定于上述幾方面,高低梯度之間的區域經濟聯系強弱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交通運輸設施建設狀況)[4]。上述因素在同梯度地區的非均衡性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產業梯度轉移的方向和規模。
假設二:經濟可達性、產業基礎和要素成本等均是區域產業梯度轉移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產業梯度轉移的實證分析
(一)產業轉移的測量
國內外研究主要通過赫芬達爾指數、區位熵和產業絕對份額對產業集聚和擴散進行量化測算。鑒于本文關于產業轉移的范圍的預設(即產業轉移主要表現為產業份額在經濟空間或產業空間上的變化),我們在產業轉移測量上傾向于采用產業相對轉移指標,并通過工業總產值的相對份額變化來解釋區域產業轉移,即
(1)
其中,Y表示t0-t1期間A地區i產業占全國i產業總產值比重的變化,以表示在此期間該地區i產業的產業轉移量,正為轉入,負為轉出;y(Ai,t1)表示t1時間A地區i產業占全國i產業總產值的比重,y(Ai,t0)表示t0時間A地區i產業占全國i產業總產值的比重;Ai,t1和Ai,t0分別為t1、t0時間A地區i產業的工業總產值,Gi,t1和Gi,t0分別表示t1、t0時間全國i產業的總產值。表2為根據公式(1)測算的2003~2013年我國高、低梯度地區之間相對產業轉移情況。圖1顯示,2003~2013年梯度Ⅰ區28個行業大類中有21個行業的產業相對比重為負值(表中的相應節點在0.00%以下),表明對應產業比重在該區出現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對應轉移在梯度Ⅱ、Ⅲ區的相對產業比重卻呈現相應的上升,且梯度Ⅱ區的產業承接量總體高于梯度Ⅲ區。雖沒有細化到將3個梯度區在行業中類別層面進行數據比較,但區域經濟的梯度轉移趨勢已在整體上基本顯現,這也為下一步的細化分析提供了前提。

圖1 2003~2013年全國三大梯度區制造業轉移情況*限于篇幅,文中僅列出28個行業大類產業相對份額轉移情況,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統計數據庫和各省(市)統計年鑒。
(二)產業梯度轉移的模型、變量和數據
1.產業梯度轉移回歸模型。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學界關于構建產業轉移模型的嘗試不少。多元回歸模型的構建是學界的常用方法。除模型中關于如何測量產業轉移方法不同外,自變量的選擇大同小異,主要區別是其被解釋的方法。類似地,本文傾向于采用多元回歸的方法對區域經濟的產業梯度轉移的影響因素展開分析,與學界的主要研究進行比較,以此發現各個因子的影響大小,重點考察產業梯度、空間可達性、產業基礎、要素成本和對外開放等因素在產業轉移中的影響,具體的研究模型如下:
Y=(+αXcytd+βXjjkd+δXcyjc+εXyscb+γXsckf+μ
(2)
其中,Y表示各地區的相對產業轉移量,X為系列自變量,其他字母為常數項、變量系數和誤差項。
2.影響因子選取和數據構成。本文主要研究產業梯度、空間可達性、產業基礎、要素成本和市場開放程度對產業梯度轉移的影響,分別表示為Xcytd、Xjjkd、Xcyjc、Xyscb和Xdwkf。為便于測算,本文著重對上述變量的重要特征進行反映,如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解釋產業梯度變量、地區貨運量占全國的比重解釋經濟空間可達性、當地相應行業占全國行業產值比重表示區域經濟的產業基礎、當地相應行業從業人員平均工資表示要素成本變量、外商投資占當地相應行業總產值比重表示地區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數據主要來自2003和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及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選取各地區176個行業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5000多個細化數據。回歸模型側重對30個省(市)的產業轉移情況進行分析,第四部分則重點對長三角地區產業轉移予以細化數據驗證時,區域經濟數據的選取口徑縮小并細化到地市級城市。
(三)回歸結果的簡要分析
前文針對全國30個省(市)的28個行業大類2003~2013年的分梯度相對產業轉移量進行了較為宏觀的分析,并指出產業的顯著梯度轉移趨勢。實證部分將依此進一步分析產業轉移的條件,并在回歸模型“逐步”分析部分著重研究產業梯度、經濟可達性和產業基礎等因素對處于梯度Ⅱ和Ⅲ區的25個省(市)的產業轉移產生的影響(相關結果見表2所示)。為確保擬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進一步對每組變量中的極端數據進行一般化處理(極端大值乘以120%或極端小值乘以80%)后再重新估計,估計結果仍然穩健。另外,通過對比回歸結果中R2、DW值等數據,我們發現模型具有強擬合性,變量之間的自相關性弱。

表2 回歸模型的系數和驗證參數
注:括號中數字為T值;* 、** 分別表示在5%和1%的水平下顯著。
從模型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除要素成本與區域產業梯度轉移之間呈現明顯的負相關外,其他因素均與產業梯度轉移之間呈現較強的正相關性,這與假設2整體上相吻合。其中,產業梯度、經濟可達性對梯度Ⅰ區之外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整體影響最大,產業基礎、對外開放和要素成本對產業轉移的影響次之。總體看來,區域產業轉移具有很強的梯度轉移特征,且越是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越遵循梯度轉移規律,如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行業大類中的行業。區域產業轉移的這一特征與國際產業轉移順梯度轉移趨勢總體一致。與國際產業轉移并非漫無目的地在后發地區選擇產業轉移受體一樣,區域產業轉移的方向和規模在很大程度上還受產業基礎、要素成本和區位優勢的影響。實證結果初步顯示,即使在產業梯度大致相同的地區,低梯度地區承接產業轉移也厚薄不一,產業梯度基本一致的江西、四川和安徽等Ⅲ區的省(市)及遼寧、福建和山東等Ⅱ區的省(市)因經濟區位和產業基礎等方面的優勢而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在相應梯度地區分別擁有更多的產業份額。關于要素成本對產業轉移的影響,比較明顯的趨勢是橡膠制造、塑料制造、調味品、發酵制品制造和方便食品制造等勞動及資源密集型產業正加速向低梯度地區轉移。在對外開放方面,與外商投資對早期沿海地區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作用一樣,其對低梯度地區承接區域產業轉移也產生積極影響,如因特爾、惠普、聯合利華和富士康等公司在轉移過程中加速向成都和重慶等地區轉移產能。
正如回歸模型中驗證的那樣,對發展非均衡的區域經濟來說,沿梯度依次轉移是區域產業轉移的重要空間特征和轉移趨勢。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經濟發展先發地區雖在整體上居于全國經濟的領頭雁位置,但其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先發地區內部發展也呈現明顯的非均衡發展特征。產業轉移主要來自高梯度地區,但承接地除域外低梯度地區,還有可能是域內的相對低梯度地區。因為域內城市間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其在產業轉移中的地位比較特殊,這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地方。
四、對長三角產業轉移的細化數據驗證
為進一步了解區域產業轉移的方向、規模和趨勢形成,除上述較為宏觀的產業轉移分析外,本文還將結合身處梯度Ⅰ區的長三角的域內產業轉移對其展開細化數據驗證*在長三角地區,只有上海、江蘇和浙江整體上屬于全國范圍的梯度Ⅰ區,因安徽的合肥、蕪湖和馬鞍山與中心區的經濟聯系緊密,故將其一并納入分析框架。。首先根據2010年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對長三角33個地市級城市的產業梯度進行大致劃分(結果見表3所示)。以此作為長三角地區產業梯度轉移的梯度劃分基礎,我們進一步對2003~2013年長三角的產業轉移情況予以細化分析,并將其與全國范圍的產業梯度轉移數據進行對比(見表4所示)*由于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和浙江整體上處于全國范圍的梯度Ⅰ區,但將江蘇、浙江兩省的數據細化到地市級單位時,其產業梯度的范圍則擴展到Ⅰ、Ⅱ區。考慮到長三角域內Ⅲ區主要是安徽省內的城市(除合肥、蕪湖和馬鞍山外),長三角地區域內Ⅰ、Ⅱ區的轉移量是長三角地區對全國Ⅰ區的某一行業產業轉移的貢獻,如塑料制品業全國Ⅰ區-47%的轉移量有近36%來自長三角域內Ⅰ、Ⅱ區的轉移。,以更深入、細化地了解區域產業梯度轉移的空間、時序和結構特征。

表3 2010年長三角域內城市梯度劃分

表4 2003~2013年長三角地區與全國產業梯度轉移情況對比 單位:%
注:篇幅所限,表中僅列出長三角地區產業梯度轉移量最大的10個行業和集聚趨勢最明顯的3個行業,并與全國的產業梯度轉移量進行比較。
(一)空間特征:在經濟空間上由高到低梯度轉移,在地理空間上由中心到外圍漸次擴散
上述產業梯度轉移回歸模型對產業轉移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梳理和驗證,發現產業梯度和經濟可達性都是區域產業轉移的重要影響變量,這一結論在對長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分析中進一步顯現。一方面,經濟空間上產業“從高梯度向低梯度轉移”的特征明顯。例如,通用零部件制造業,從梯度Ⅰ區轉移出來的產業,產業Ⅱ區承接量明顯多于Ⅲ區;塑料制品業,梯度Ⅰ、Ⅱ區的產業轉移量都是負的,只有梯度Ⅲ區轉移量是正的,說明處于經濟空間的梯度Ⅲ區是梯度Ⅰ、Ⅱ區中屬于邊際產業的塑料制品業的主要承接地。另一方面,地理空間上產業轉移的“從中心向外圍漸次擴散”的特征在長三角與全國的數據對比中凸顯出來。受經濟可達性影響,長三角地區處于全國經濟的相對中心位置,域內的產業轉移具有明顯的地理上的毗鄰性,即域內轉移強于域外轉移。此外,在方便食品制造業、家用紡織制成品制造業中,長三角域內Ⅱ、Ⅲ區基本吸納了域內Ⅰ區的轉移產業(需要強調的是,除安徽省部分相對后發城市外,長三角地區的大多數城市處于梯度Ⅱ區以上),這也說明處于同一梯度的域內地區因與產業轉移地有更強的經濟聯系而在區域產業梯度轉移中占有更多份額。
(二)時序特征:勞動密集型產業先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
在表4中,產業轉移量最大的10個行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心或高梯度地區的最大轉移幅度接近40%。這類產業往往在早期就已在中心或高梯度地區完成產業成熟期,并于2003~2013年進入最大轉移階段。區域產業梯度轉移并非同時發生,有時會呈現錯位轉移。總體趨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較早,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較晚。數據顯示,2008年前后是區域產業轉移的重要節點。為進一步了解產業轉移的時序性特征,我們選取2008年的產業中類截面數據對2003~2013年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數據進行分割,結果發現大多數產業的轉移主要發生在2008年之前,其中的典型代表是長三角的紡織服裝制造業,轉移較早且其域外轉移趨勢明顯;高梯度地區的農副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類產業在2008年之前已轉移完畢,產業份額基本穩定在滿足本地市場需求水平;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代表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在2008年之前一直向高梯度地區集中,直至2008年前后才逐漸呈現外移端倪。
(三)結構特征: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差距收窄趨勢,產業結構總體進入上升通道
2003~2013年長三角地區產業梯度轉移趨勢明顯,全國范圍的邊際產業也呈現明顯的梯度轉移趨勢。域內、域外不同梯度之間的這種產業互動的直接結果是邊際產業在高梯度地區相對份額縮小,并在低梯度地區實現擴張。此消彼長之間,低梯度地區相繼實現工業總產值的絕對增加,并進一步貢獻當地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增長,高低梯度之間的發展差距呈現不斷收窄趨勢。同樣地,高梯度地區的產業結構也在產業互動中實現了升級。從表4中可以看出,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規模從諸如長三角之類的高梯度地區漸次抽離,高附加值產業在產業轉移中呈現“逆梯度聚集”的現象。一方面,這是計算機、通信設備和專用設備制造等資本-技術集中產業在區域內的規模化集聚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低梯度地區的企業逐步將自己的研發中心、營銷中心和公司總部轉移至中心城市的結果[11]。正是這種逆向轉移或集聚主導了高梯度地區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趨勢,高梯度地區制造業附加值比重也因此在全球價值鏈中呈現明顯擴大趨勢。
五、結論與啟示
以2003~2013年全國范圍的產業梯度轉移回歸模型對產業轉移的影響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產業梯度是影響產業轉移的第一變量。自2003年以來,產業梯度轉移在全國和區域經濟范圍內頗為明顯。然而,即使高梯度地區的邊際產業已開始了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但長三角等高梯度地區仍是轉移產業的優勢集聚地(域內制造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從2003年的64%降至2013年的49%)*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3和2013年制造業數據計算而得。。另外,本文特別將錢納里的發展階段區分標準引入區域梯度劃分過程,并以此為基礎對比了作為全國范圍產業轉移重要轉出地的長三角地區與進一步細化的長三角地區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域內重要轉出地的具體轉移情況,結果發現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首先從域內產業高地向域內次高地轉移,再順次向域外低梯度地區轉移,對勞動力和原料成本更為敏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目標相對分散,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重要轉移節點是2008年。
2003~2013年全國范圍和長三角地區的產業互動的重要特征是產業的梯度轉移,且域內地區的產業轉移強于域外地區。因此,長三角等經濟發展先發地區在實施產業轉移戰略時,應基于對域內地區運輸時空成本和產業承接能力等因素的考量,相對優先地引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向域內地區轉移,以盡量減少產業轉移過程中的規模損失,促進長三角等高梯度地區在整體上實現工業化后進一步推進區域經濟的全面工業化。另外,在強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高梯度地區可逐步漸次利用區域經濟聯系,將區域產業轉移的空間范圍拓展至京津冀-華北經濟帶、長江經濟帶和珠江-西江經濟帶等,通過擴大高梯度地區擴散空間范圍的方式減少區域產業轉移粘性。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可立足于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積極構建域內產業高地。依據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戰略及“一帶一路”戰略,成渝和中原等經濟區的中心城市可進一步通過深化市場開放、強化政策安排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筑巢引鳳”,實現區域經濟資源向中心地區集聚,為隨后域內高地的產業梯度轉移積蓄擴散勢能。
[1]Akamatsu K. A Theory of Unbalance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61,(86): 196-217.
[2]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190-207.
[3]劉志彪.全面深化改革:基于縱橫兩條基本路徑的戰略思考[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5):54-60.
[4]陳建軍.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與空間結構的演變[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3):89-98.
[5]楊亞平,周泳宏.成本上升、產業轉移與結構升級——基于全國大中城市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3,(7):147-156.
[6]陳剛,劉珊珊.產業轉移理論研究:現狀與展望[J].當代財經,2006,(10):91-95.
[7]劉紅光,王云平,季璐.中國區域間產業轉移特征、機理與模式研究[J].經濟地理,2014,(1):102-107.
[8]胡安俊,孫久文.中國制造業轉移的機制、次序和空間模式[J].經濟學(季刊),2013,(3):1533-1566.
[9][美]霍利斯·錢納里著,李斯華等譯.發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
[10]劉志彪,張少軍.中國地區差距及其糾偏:全球價值鏈和國內價值鏈的視角[J].學術月刊,2008,(5):49-55.
[11]張公嵬.我國產業集聚的變遷與產業轉移的可行性研究[J].經濟地理,2010,(10):1670-1674.
(責任編輯:化 木)
Cross-regional Gradient Transfer or Regionall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A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the Data in Chin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artition from 2003~2013
ZHANG Mingzhi,XIE Hao
(Marxism Institute,Nanjing Political Institute of PLA,Nanjing 210003,China)
The results of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low gradient areas in 2003~2013 show that industrial gradient is the first variable of influence in industrial transfer,and 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of economic space is the primary trend of th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in terms of space,the marginal industries of regional transfer is stronger than the extraterritorial transfer between the same gradient areas; in terms of timing,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ransfer is earlier than capital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erms of structure,both the high and low gradient areas come into the rising chann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due to the regionally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is regard,the high gradient areas 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transfer in the domain of industrial space by gradually expanding regional economic link,while the low gradient areas should accumulate potential energy to transfer the industries to lower gradient within the region by constructing local industrial highland.
Industrial Transfer;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Industrial Gradient
2016-08-08
長三角合作與發展共同促進基金資助項目(15CSJ04012)
張明之(1970-),男,浙江象山人,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謝浩(1990-),男,安徽合肥人,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F063.1
A
1004-4892(2017)02-0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