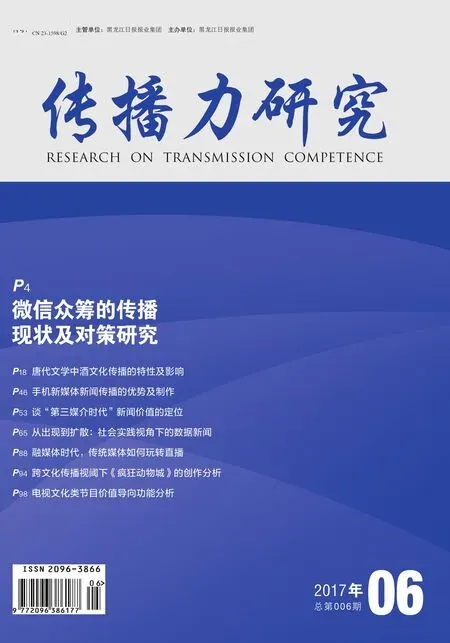理解的藝術
——從解釋學角度探討文本的意義與建構
文/張鈺
解釋學以理解為出發點,然而,關乎理解又必然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即讀者的理解與理解對象——文本的意義的關系問題。具體來說,是理解對文本意義的把握,還是讀者的理解產生了文本的意義;以及讀者的理解如何正確把握文本的意義問題,也就是本源和同一性問題。對于處在制造歷史與成為歷史過程中的我們,即能動主體思考的存在而言,如何看待這一處于解釋交鋒中始終未盡的真相?相較于理解主體的“理解”與文本意義之間的本源問題的爭論到底呈現怎樣的周轉趨勢,是讀者的理解賦予了文本自身意義的顯現,還是主體“理解”的過程即是對文本意義把握與梳理的過程?
施萊爾馬赫明確表明其對于文本意義闡釋重心的理解即在“理解”上。“理解”這一觀念,是經他的手,被置放為整個解釋學理論的基石。[1]整合其觀念縱觀而看,在解釋學歷史維度上的角度探討,此時,理解已經不再是圣經解釋學中作為注腳闡釋的存在。他將理解作為藝術,志在建立一種普遍的解釋學。在以施萊爾馬赫為代表的傳統解釋學派中,理解的藝術即是“消除誤解的藝術”,當他論及我們所面對的文本已經不再是我們熟悉的文本時,便提出了“解釋的重要前提是,我們必須自覺地脫離自己的意識而進入作者的意識”。從作者、文本以及讀者三者間的動態關系來看,施萊爾馬赫在這里將“作者”置于某種“中心論”上,他將文本存在的意義同作者要表達的意圖等同起來,反過來從讀者角度理解,就是讀者企圖對文本作“理解”與解讀時,就必須要轉換為以理解作者的原意為基準。在這里,作者的原意成為三者動態平衡中的核心存在,而“理解”就是一個“讀者作者化”的過程。
與其說將理解主體看作是創作主體,不如說是一個模擬角色的重新構建。然而為了到達此類效果,施萊爾馬赫提出“心理移情”的概念,這便是他認為無限接近于“理解”藝術的真諦。如果這作為條件存在且成立的話,讀者將尷尬地站在此地對“理解”行注目禮。而企圖達到“理解”之目的,也就必須消解讀者的“尷尬”,這即是讀者個體的歷史性所帶來的隔閡,對于這隔閡間距的縫合便是“心理移情”的終極目的。無論是時間距離還是歷史環境都是施萊爾馬赫所認為的理解上的障礙,只有將讀者的個體性與歷史性消解而后重建心理上的屬于作者的個體性和歷史性,替代作者而誕生才能真正把握文本意義。
施萊爾馬赫在理解深度上有一個所謂的客觀標尺,那就是“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的更好”[2],這里闡述了一個在讀者和作者之間的動態關系。當然,這種讀解并非是由著讀者自己的意愿來更改作者的意圖,以此來做到比作者“理解的更好”。他指出了作者并非是權威的解釋者,而讀者對文本的解讀也不是逐步趨近于作者原意的逆向運動,正是有了施萊爾馬赫認為的“尷尬的‘距離’”,才構成了讀者從自己的歷史性出發去讀解文本的可能,這樣同文本自身的溝通過程便成為文本意義形成的創造過程。
若說施萊爾馬赫以其先驅無可比擬的貢獻就解釋學基本問題立論的話,從本體論的立場上建構起了哲學闡釋學的理論體系的巨擘——伽達默爾則堅決反對施萊爾馬赫將讀者理解限制于尋求作者的“原意”,他完全顛覆地反而論之。伽達默爾首先闡明“文本的意義傾向一般也遠遠超出它的原作者曾經具有的意圖”,同時也聲稱“誰想理解,誰就從一開始便不能因為想盡可能徹底地和頑固地不聽文本的見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見解中——直到文本的見解成為可聽見的并且取消了錯誤的理解為止。誰想理解一個文本,誰就準備讓文本告訴他什么。因此,一個受過詮釋學訓練的意識從一開始就必須對文本的另一種存在有敏感。”因而“理解的任務首先是注意文本自身的意義。”可見,伽達默爾不否認文本的意義中含有作者的原意,但文本意義不僅僅如此,還應包括更多。事實上,伽達默爾是將作者創作完成后的作品文本視為是獨立于作者之外的獨立存在,讀者對其的一切理解活動因而也就應以作品這個“屬于被理解東西的存在”[3]為中心,而非作者。
當我們面對一個文本時,尤其是文學作品,試圖去詮釋它的過程便一定會被卷入到兩個不同的歷史背景中,即伽達默爾認為的解釋者的“先見”和待解釋的文本內容。而理解的過程也就是把這兩者融合在一起不斷趨向于一種動態的平衡,傾聽讀者之意更要傾聽文本自身的回答,“視野的融合”便有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伽達默爾說:“文本的意義傾向一般也遠遠超出它的原作者曾經具有的意圖。理解的任務首先是注意文本自身的意義。”[4]他把理解活動的中心從作者轉移到了讀者的身上,并且將施萊爾馬赫認為的理解的“間距”轉變為一種合理的存在,正是由于有了此種“間距”,才為讀者解讀文本及文本創生意義提供了場域,而理解本身的過程就是主體的“先見”同文本現實狀態相連接進而產生非復制性的文本意義。以往被認為危害理解的“時間距離”、讀者的“歷史性”和“先入之見”等要素,堂而皇之地棲身在理解過程之中,并成為決定文本意義的關鍵。[5]
在現代解釋學派中,讀者存在一個視域,文本自身也擁有一個視域。理解的過程便是在一個讀者已有“先見”視域和文本本身帶有作者原意視域的前提下進行的,當“視域融合”發生時才是理解的本質。伽達默爾把“詮釋學的任務描述為與文本進行的一場談話。”[6]即默認解釋者同文本相互對應的主體地位,文本既可以向讀者提問,同時也需要解決讀者的疑惑,反之亦然。這樣理解就變成為一種對話關系存在,對文本意義的把握也就在問與答之間的動態關系中被逐步發掘。
作品有它自己的世界,解釋者也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這兩個世界在解釋者的理解中發生接觸后,融合為一個新的可能的世界——意義。[7]在解釋學中“意義”是一個核心概念,也是現代美學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到底什么是意義,假若將其放置在時間維度上,詮釋意義的對象、主體等不同會賦予詮釋行為的不確定性。從作者、文本、讀者的三者動態關系來看“意義”可分為三層理解角度,即作者與文本,讀者與文本,作者與讀者。

施萊爾馬赫將作者意圖同文本意義等同起來,讓讀者在自我拋棄后,才能發現潛藏在作者背后的意義,即文本自身的意義。假使讀者能夠完全將作者意圖把握,甚至更好的理解了作者無意識,那么也就是對于意義理解的實現。傳統解釋學的觀點流于絕對化,文本意義并不能等于作者意圖。其因可從文本的作者和文本的語言之間的距離來證明,即作者的意圖和他由文字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常常不盡相同,也就是所謂的“詞不達意”“言不盡意”的現象。估且假定作者能夠完全將個人意圖通過語言表達出來,但是由于語言自身的多義,從而演繹出超越作者原意的情況也未嘗不可。如果給“意義”界定理解的話,那作者對文本意圖的灌輸完全不能成為標準。
總體而言,作者、文本、讀者在闡釋重心的動態關系上正在朝著多方位闡釋模式發展,單一的從作者意圖、文本含義、或者是讀者詮釋上對文本意義的把握已經不能成為最佳方案。對文本意義的全面理解過程應從該動態體系中去詮釋,即作者賦意、文本(作為中介)轉意、及讀者釋意的集合中去尋找,而無論是施萊爾馬赫還是伽達默爾在探討文本意義之路上也正是該動態體系最直觀的表現。
[1]段鼎.理解的命運[M]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5):7.
[2]何衛平.解釋學之維——問題與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187.
[3] [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二版序言[A].洪漢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8.
[4] [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上卷.[M]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4):478.
[5]彭啟福.理解之思——詮釋學初論[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68.
[6] [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著.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465.
[7]段鼎.理解的命運[M]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