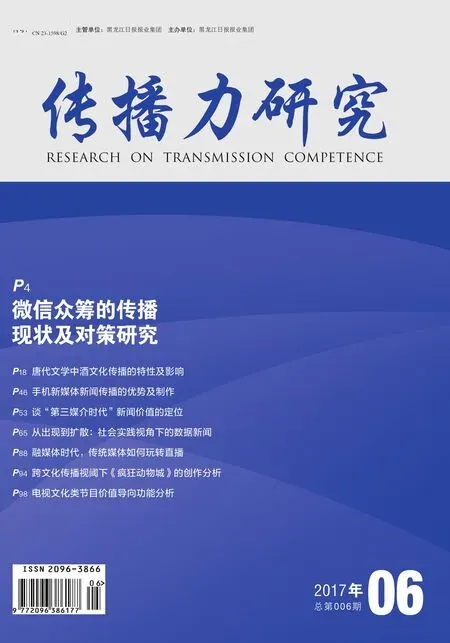為什么我們不再相信媒體?
——試析新聞業的“后真相”危機
文/齊盈盈
公眾和新聞媒體曾有過一段蜜月期。那時的大眾媒體深得公眾的信任,被視為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默契的信任無疑被打破了。新聞業不再成為人們尊敬的對象。究其原因,后真相的語境不可忽視,本文將從后真相的時代特征出發,探尋當前新聞業面臨的受眾信任危機。
一、從真相到后真相:媒體公信力的解構
新聞公信力,即“新聞傳媒能夠獲得受眾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聞傳媒以新聞報道為主體的信息產品被受眾認可、信任乃至贊美的程度”。[1]可以說,新聞媒體的公信力集中反映了公眾對于該媒體的信任感,主要表現在公眾對于新聞媒體發布的信息的信任程度。
傳統媒體時代,作為相對單一的公共信息來源,大眾傳媒壟斷了傳播權和影響力。這種壟斷的合法性、合理性正是建立在大眾傳媒提供給公眾真實、客觀的真相為依憑之上。權力和義務的要求對大眾傳媒業形成了責任約束,大眾傳媒也通過這種約束獲得自身的獨特行業地位。這種潛在的對于真相需求的默契認同構建了公眾和媒體之間契約平衡,也是新聞媒體公信力最重要的來源。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平衡被打破了。在許多突發性事件的傳播過程中,無論新聞媒體提供了怎樣的信息,有依據或沒依據,都會被懷疑是否為真,是否利益勾結,是否客觀公正。在失去了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后產生的真空地帶,謠言理所當然的趁虛而入。而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就在這種后真相的狂歡中被逐步瓦解了。

二、共識困境:新聞業的后真相危機
從根源上講,目前媒體所遇到的公信力危機,是真相危機,是后真相語境下的結果。對于真相重要性認同的錯位和倒塌直接表現就是媒體的新聞產品缺乏真實性,為了利益歪曲事實的現象屢見不鮮。真相危機的直接表現,就是人們不再相信媒體,媒體的公信力下降。
后真相時代,是一個情感讓位于理性的時代,是一個真相被后置的時代,也是一個媒體權威被消解的時代。
(一)真相的證明越來越困難
人類認知水平的提高和技術發展并沒有使證明真相本身更容易。盡管我們已經知道新聞不可能再現全部的事實,加之后現代主義的對人們認識論的瓦解之下,這部分被呈現出來的事實也普遍遭受了懷疑,真相不再不證自明。
從真相的本體上講,我們賴以證明事件真實性的手段在后真相語境中被瓦解了。在以信仰為主的時代,我們的真相認知落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盡管人類無法知曉全部的事實,但上帝知道所有的真相。但是在現代哲學誕生以后,真相的宗教確保被祛魅,那么最終真相的證明落在了人的理性上,“理性推理……只要我們能夠預設一個前提或者假設,運用理性邏輯的力量就可以推理演繹出整個事實體系,從而還原出整個真相,”[2]但是這種演繹存在一個潛在的缺陷:即我們在推理整個事件的真相之前,必須有一個最初的原點(可能是某個新聞事實)作為下一步推理的基礎。但顯然,我們也無法確定這個假設就一定為真。
(二)真相認同越來越困難
“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在新聞傳播過程中也是如此。然而這種視角的分化使我們越來越難以就某一新聞事件達致真相的共識。視角主義的提出者尼采認為:“獨立于視角的所謂的客觀事實,不過是一種錯覺,實際上因為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具有相同視角,得出了一致的闡釋,才造成了客觀性的感知。”[3],這種解釋實際上隱含了一個前提:即,我們不能知曉所有的事實和真相。即使所有人都認同一致的事實真相,那也只是基于相同的視角而造成的“合理幻覺”。
但同時,視角主義帶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發:雖然新聞真實永遠無法徹底還原事件的真相,但真相依賴于“共同視角”。這意味我們仍然可能獲得我們所想要的事實真相,就某一新聞事實達成共識,并以此進行下一步的演繹推理和價值判斷,從而做出行為選擇。
(三)真相辨別越來越困難
人們發現,在辟謠過程中,即使真實的消息已經發布,但是假消息在人們心中造成的影響卻難以消除。有學者認為,確認偏誤的心理有著重要影響。“確認偏誤從能夠確認自己已有信念或假設的角度搜索、解讀、回憶信息,但對其他可能性缺乏考慮的傾向。”[4]這種認知和評價上的路徑依賴,使人們一旦在信息的海洋中誤聽人言,即使最后獲得糾正,也難以消除假消息的深刻影響。新聞的真實性的作用大打折扣。在真相難以自證正當,認同難以達致的情況下,假消息代替真相大行其道,加重了人們對于媒體提供的信息的不信任。
除此之外,社交網絡作為新聞的信息源也加重了確認偏誤的傾向。在社交媒體時代,公眾發言幾乎不需要任何門檻。傳媒機構和專家對事實的壟斷地位岌岌可危,假消息第一時間占據人們視線的可能性增加。
三、為什么人們不再相信新聞真相?
信任是社會重要的潤滑劑,它的存在直接影響社會活動的能否有序運行。“作為一種無形的勢力,信任有利于當事方以開放的心態面向事實,協調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促成和維持平穩順當的合作互動。”[5]同時信任也是媒體和公眾互動,媒介秩序得以運行的重要保證。
事實上,人們對于新聞真實性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人們一方面認為新聞媒介構筑了一個巨大的擬態環境,新聞無法徹底的達致真相,另一個方面又不得不依賴于媒介手段的幫助來認識世界。但后真相時代人們懷疑的不單單是新聞媒體是否提供了正確的事實,而且懷疑新聞媒體是否有能力反映真相。技術手段令人們能夠有更多的手段達致真相,證明真相,媒體的唯一權威悄無聲息的被瓦解。
四、后真相時代如何重塑新聞業公信力?
在后真相時代,難道我們不再需要真相了嗎?顯然不是,個人欲求和社會良好運行總是存在一定的沖突,費孝通先生曾經這樣解釋人類行為的動機:“一是人類對于自己的行為是可以控制的,……也就是所謂意志;一是人類在取舍之間有所根據,這根據就是欲望。”但若我們仍然強調民主、公共利益和社會進步,那顯然不能完全按照市場邏輯去迎合所有的受眾,降低或放棄為受眾提供他們情感上或許沒那么喜歡卻對他們真正有用的新聞真相。
(一)事實查驗,重視新聞的真實性
必須看到的是,對于新聞真實性的要求,不再僅僅是新聞六要素是真實就可以了,更要求事實反映真相。不僅如此,還要求媒體所提供的新聞事實和真相可以禁得住公眾的推敲和檢驗。也就是說,新聞媒體不僅要拿得出事實,更要拿得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新聞是真實的。
在對新聞的真實性要求越來越高的當下,“事實查驗表現了職業力量一如既往地制約和監督權力、維護民主政治體制、關照公共利益。在以新技術為場景的新傳播形態下,事實查驗是新聞從業者繼續維護特定社會系統運轉的試驗。”[6]
(二)價值中立,保證自身的客觀性
價值中立,又稱價值無涉。但這也是新聞學領域中客觀性原則的理論來源之一。通過對事實不偏不倚的客觀報道,新聞媒體由此達致價值中立。刨除它是否可以完全徹底實現先不討論,在容易被情感煽動的“幻影”公眾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為狂熱的冷卻劑,新聞媒體必須保持高度的清醒,而價值中立和客觀性正是這種媒體角色的內在要求。
同時,價值中立還是新聞真相的要求。“正如尼采在《道德譜系學》中寫的那樣:我們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個問題的,那么對此問題我們的概念以及我們的客觀性就越是會完整的多。”[7]媒體只有秉承客觀公正之心,報道更多的視角和觀點,才能實現對真相的盡可能的接近。
(三)功能轉型,從信息的提供者到真相的探求者
當前,新聞傳媒業面臨著轉型的危機。當新聞機構不再是信息獲得的唯一來源,當傳統媒體在速度、權威等各個新聞要素上不及其他機構或者個人,那么新聞媒體的自身定位又在何方?
許多學者提出了媒體功能轉型的見解。美國傳播學者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認為:當前全球新聞倫理應當重新理解探求真相這一媒介倫理。他認為真相需要充分解釋,而“新聞報道者的目的是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因此應致力于充分的說明,用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話說,就是深度地描述。充分的描述形成豐富的認識,進而取代僅僅由技術、外表和精確數據形成的粗淺印象。”[11]童兵教授認為,由于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信息不再是一種稀缺資源,再固守信息發布者的角色,只會令媒體被觀眾淘汰,在后真相時代,情感泛濫,真相成為稀缺者,媒體只有立足于探求真相,解決問題,才能在媒介市場中獲得自己的立足之地。
綜上,在真相后置、被假消息淹沒的后真相時代中,真相恰恰成為人們需要卻又十分稀缺的東西。嚴格說,后真相的說法其實是一種幻象,它并不意味著人們不再看重真相,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人們重視真相,才要不斷通過質疑來盡可能達致真正的真相,而假如當前環境并不能為人們提供真相,那也只會令公眾轉而訴諸感情,最后造成“后真相”假象。而作為新聞媒體要做的,無疑是幫助公眾重塑真相概念,拿出充分的態度和證據來重建人們對媒體的信任,構建良性而健康的媒介環境,而非唱衰真相,自降職業要求。
[1]鄭保衛,唐遠清.試論新聞傳媒的公信力[J].新聞愛好者,2004,3.
[2][3][4][10]藍江.后真相時代意味著客觀性的終結嗎?[J].探索與爭鳴,2017,4.
[5]劉擎.共享視角的瓦解與后真相政治的困境[J].探索與爭鳴,2017,4.
[6][7]王悠然.警惕后真相時代的假消息[J].社會科學報,2017,1.
[8]周睿鳴,劉于思.客觀事實已經無效了嗎?—“后真相”語境下事實查驗的發展、效果與未來[J].新聞記者,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