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吃街邊小吃的大翻譯家蕭乾
安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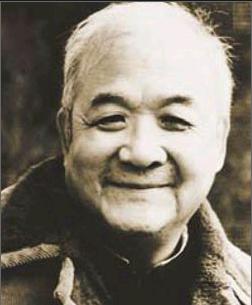
蕭乾正式進入文壇,與兩次飯局有關。
1929年秋,蕭乾在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讀書,次年,經現代文學課老師楊振聲介紹,去采訪當時的文壇領袖沈從文。初次見面,沈從文請他到東安市場的一家小館子吃飯。沈從文用毛筆寫菜單,字跡俊逸,蕭乾看見,惜之為寶,說:“這個菜單您給我吧,我再給您抄一遍。”沈從文笑了,一擺手說:“要菜單干嗎?以后我會給你寫信,寫很長的信。”
1933年,蕭乾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了一篇小說,叫《蠶》。過了幾天,沈從文給他來信,說有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了他的那篇《蠶》,感覺很好,請他去吃茶。蕭乾自然知道這位小姐一定是著名的“星期六聚會”的女主角林徽因。果不其然,當周的周六,在東總布三號,蕭乾第一次見到了林徽因。林見面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然后大家一起吃茶、聊天。梁家客廳的客人都是胡適、沈從文、徐志摩、金岳霖等學界巨匠,蕭乾這才算是正式進了這個圈子。
雖然兩次契機都與飲食有關,但蕭乾并不是一個食不厭精的美食家。這一點在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中可以找到佐證,書中寫道:“蕭乾從來也不是個美食家。作為老北京,他愛吃的炸醬面、炸灌腸、蔥花烙餅,都是大眾化的食品……”蕭乾寫過一本《北京城雜憶》,薄薄的一冊,卻從戰爭風云、時代巨變講到個人情感、吃穿住行,倒也面面俱到。其中有一篇《吆喝》,說的是北京小吃的叫賣聲,讀來興味盎然。
老北京的胡同,從早到晚叫賣聲沒個停,而且分時段有不同內容,大清早是賣早點的:“大米粥呀,油炸鬼。”到了晚上是賣夜宵的:“餛飩喂——開鍋!”餛飩攤子和剃頭攤子一樣,也是一頭熱:一頭兒是一串小抽屜,里面是皮、餡兒和作料,另一頭是一口湯鍋,跟現在城市里只在夜里出沒的“野餛飩”攤,似乎并無太大分別。
叫賣的貨物自然也分季節。春天賣蛤蟆骨朵兒,也就是未成形的幼蛙,一個制錢撈上十幾只,玩夠了還能吞下去——讀到這兒有點震驚,這也能生吃嗎?那時年紀小小的蕭乾自己也奇怪:“它們怎么沒在我肚子里變成青蛙?”夏天賣西瓜和碎冰做成的雪花糕,秋天是“喝了蜜的大柿子”,冬天是北京人最親切的冰糖葫蘆,吆喝的詞兒是“葫蘆兒——剛蘸得”,或者“葫蘆兒——冰塔兒”。隆冬時節當然少不了烤白薯,一路上可以揣到袖筒里取暖,到了學校還可以拿出來大嚼一通。
蕭乾熱愛這種街頭叫賣的小吃,對正式的宴會則避之不及,他認為友朋相聚,主務為敘舊、交流,而赴宴時,滿滿一桌名酒佳肴往往壓倒一切。他曾多次在宴會上遇到想與之深談的人,且彼此也大有可聊之處,無奈席間杯盤交錯、嘈雜喧鬧,即便鄰座,也不大能談得起來,若是再間隔幾人,除了頻頻舉杯、遙遙示好之外,更說不說幾句話。他尤其害怕飲酒無度的聚會,桌上若有一位打通關的勇將擺起擂臺,那宴請就變成灌醉了。
比起宴會,蕭乾更喜歡茶會,不僅因為他喜愛飲茶,更因為赴茶會的人沒有埋頭大吃或舉杯牛飲的,談話才是活動的中心。他在英國一個非常大的收獲,就是通過茶會結識了羅素、李約瑟、羅賓遜夫人等知名學者,在他們身上獲益匪淺。他甚至寫過一篇文章,叫《茶在英國》,里面特意引用了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一句話,也可以看做他自己的表達:“人生最舒暢莫如飲下午茶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