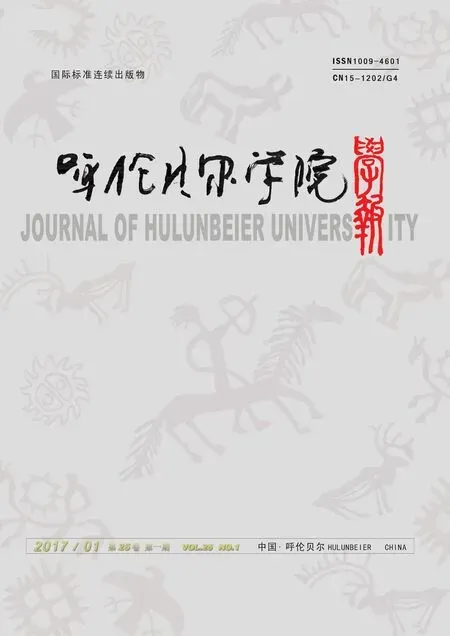論羅馬法中的土地權利
曼德爾娃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 北京 海淀 100081)
土地在人類歷史中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資料,承載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是“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109。土地作為一種有限的自然資源,必然會受到社會強制力的調控與規制。在這之中便產生了為了賦予某種圍繞在土地這一客體之上的利益以法律效力,而要求另一人或所有其他人作為或者不作為的一種被認可的主張,即土地權利。土地權利的形式反映了它所處的歷史時間內特定區域或群體對土地的利用方式以及對“權利”這一抽象概念的認識。現代法中土地權利的理論、概念、內容等既是當下社會的產物,又是土地權利自身在法學歷史上的發展結果。現代法中一個重要理論溯源為羅馬法,其中所包含的土地權利的原始形態是現代土地權利的理論基石。羅馬法泛指羅馬國家的法律,它是羅馬社會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逐步發展完備的奴隸制社會法律[2]65。
一、羅馬法中對土地的認識
在羅馬法中,已經產生了對財產法定的、固定化的類型分類。首先,土地涵括于“物”的概念之中,而在羅馬法中“物”的概念與現代法中的物不同,較之更為廣泛,“羅馬人將所有具有財產價值的客觀存在,進一步說,將客體及客體之上的權利統統視為物”[2]176。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局限下,這種客觀存在也必是可明顯被人感知的,亦不同于現代法上的概念。
依據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的著述,“物的最基本的劃分體現為這樣一種二分法:有些物是神法的,有些物是人法的”[3]80。神法物為與宗教祭祀有關的物品,人法物則是與世俗社會有關的物品。人法物又進一步分為公有物與私有物,“公有物被認為不歸任何人享有,實際上它們被認為是集體的。私有物是歸個人所有的物品”[3]82。在這之中,神法物與人法物中的公有物都被排除在交易之外。私有物又可進一步細分為有形物與無形物,要式物與略式物,不動物與可動物。土地則屬于有形物。有形物在《法學階梯》中的表述為“那些可以觸摸的物品。”[3]82學者進一步解釋為“存在于自然界中可以觸知的實體物”[2]178。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法的發展中,由要式物與略式物這種對土地的二分法向不動物與可動物的劃分方法的轉變。要式物是指轉移需要履行特定的法定形式的物品。對它們的轉讓必須通過要式買賣(mancipatio)或擬棄訴權(in iure cessio)等鄭重的方式進行[4]97。略式物的轉讓則可以采取簡單的讓渡(traditio)方式。而何種土地需要經過復雜的交易方式進行某項權利的轉讓則與其所處的位置相關性很強。公民所有(因而為位于意大利的)土地屬于要式物。而由個人占有而非所有的、位于行省的土地則屬于略式物。這種對權力中心的土地賦予復雜交易模式的背后是對此類土地價值更高的肯定。而后,在羅馬法發展的最后階段,這種因行政地域級別而對土地價值進行高低評判的標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土地自身生產價值的肯定。取代要式物與略式物的分類是不動物與可動物。土地則屬于不動物之中。這種基于物理屬性差異產生的交易模式差異的劃分方法,亦為后世的現代法學所繼承與發展。
二、羅馬法中土地權利的具體內容
羅馬法中雖然產生了物的概念,但沒有針對物這一類財產的物權概念。羅馬法通過區分“對物之訴”(actio in rem)與“對人之訴”(actio in personam)來區分不同的權利。不同于現代法,羅馬法中通過訴訟請求的不同,來展示對不同類型財產所享有權利的不同特質。羅馬法學家認為財產可以包括財物與債。財物和債之間的區別是擁有和應當擁有之間的區別[5]94。“擁有”這一財物性質在“對物之訴”中的體現即是“請求某物屬于原告或者原告有權以一定的方式對某物從事某種活動,或者是被告不享有某項相同或是類似的權利”[6]163。這體現的是一種人對物享有直接且絕對的一類權利。如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的表述,“在這種訴訟中,對方當事人提起的是排除妨害之訴”[3]288,也就是說,在這一訴訟中的基礎是人對物的排他權利,對方當事人的參與是因為在這一排他權利中形成了一種障礙。而債的“應當擁有”則體現為“對人之訴”,強調人與人的關系,“對人之訴的的訴訟請求是請求確認對方一個法定義務,請求對方‘給、做或者履行’”[6]163,這是一種針對特定的人為特定行為的訴訟請求。羅馬法即是通過這種訴訟的區分方式來區分物權與債權。
因此,在羅馬法之中,對土地這一“物”的權利便是在這一框架下闡釋的,它包括對土地的絕對的所有權、役權、永佃權、抵押權與質押權。
(一)所有權
在羅馬法的物法體系下,所有權制度占有核心的地位,而土地所有權又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土地所有權制度的發展促進了所有權制度的發展。羅馬人對物的私有產權是由對土地的自然占有開始的。當土地私人占有被置于法律保護之下,并且和其它財產一樣可以自由買賣和交換,私人所有權就正式形成了[7]98。
而羅馬法對于所有權的規定卻并不是明確的列舉其所享有的權利或明確定義。彼得羅·彭梵得認為羅馬法中的所有權是一種“對物最一般的實際主宰或潛在主宰”[8]148, 因此對于一種潛在的主宰便是一種寬泛的、無所不包的權利,這種權利便無法通過列舉來明晰,而是只能通過對土地所有權的否定的、消極的限制義務來界定其內涵。羅馬法學家也認為這是羅馬法所有權最重要的特征——絕對性。這種特征具有一些明顯的表現,如:第一,土地所有權上為賦稅的免除,因為“在早期人看來這種稅具有為使用和占有支付補償的性質,而應當接受這種補償的人相反應該是所有主”[8]149;第二,在土地的相鄰關系中,各個相鄰土地的責任表現為一種“否定性制度”,“一種在許多不同方面對各個自由的保護,對各個所有主的準主權的保護,而不是表現為一種承認土地間相互影響和役用的‘肯定性制度’”[8]178。如在排放雨水之訴中,相鄰土地發生因自然雨水改道而產生的糾紛時,一方對另一方可提出責任的緣由僅為此種改道是由另一方的是施工或拆除土地所導致,而對于其他類型的侵擾行為只能容忍其自然發生;第三,土地的所有權為一種“最終剩下的物權”[5]146,這種物權在受永佃權或地上權支配的土地上,所有主擁有最終的享有權。當然在羅馬法的后期發展中這種土地所有權的絕對性逐步改變,如相鄰關系中產生了一些嚴格的限制。同時這種絕對性的改變也影響了羅馬法中的物法體系,促進了羅馬法中如永佃權、地上權的等他物權的產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征,即是在前文中所論及的,在羅馬法中物包括客體,也包括客體上的權利。表現在土地這一客體上時,就導致了土地與土地的所有權并沒有顯著的區別開來。
(二)役權
土地存在于開放的環境之中,即使一片特定的土地歸屬于某種類型的所有權者,這片特定區域的土地的利用也與周邊所屬其它所有權者的土地密切相關。同時,只是去保持完整、封閉、靜止的“所有”狀態的土地并不能帶來土地的價值,活躍并開放的“利用”行為才可以賦予土地價值。因此,羅馬法中也產生了關于土地的役權制度。役權是指為特定的土地或者特定的人的便利和利益而利用他人之物的權利[9]68。這其中包括地役權和人役權,二者最顯著的區別是前者針對特定的土地而設立,后者針對特定的人而設立。
地役權的突出特點有:第一,地役權在相鄰關系中調整土地的需求。“兩個土地如果不是相連的,至少也應是臨近的”[8]192;第二,地役權是針對需役地而設立的,首先表現為需役地所有人的變更并不必然導致地役權的滅失。當需役地的所有人變化,后繼的所有主可以當然的享有需役地附屬的地役權。其次,地役權分為城市地役權與鄉村地役權,二者的區別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土地與鄉村土地之間的劃分,而是根據需役地的土地需求為何類而進行的劃分。例如,如果在需役地的需求是建筑物建設,則是城市地役權;如果需役地的需求是農業種植,則為鄉村地役權;第三,地役權的行使是在一定限度內的。首先,需役地的所有人不得要求供役地的所有人實施某種行為,只能要求其不實施某種行為或允許需役地的所有人在供役地上實施某種行為[5]135。其次,地役權的行使目的僅限于需役地的受益。這里的受益要注意是針對需役地的,即是需役地有某方面的需求,如蓋房、通行、灌溉,而對供役地實施某種消極限制或是積極行為,而不能是超出“需求”的濫用或是獲利。
人役權則分為四種:用益權、使用權、居住權以及對奴隸和他人牲畜的勞作權。用益權與使用權與土地直接相關。其中,使用權被認為是“用益權的一部分”[5]136,是一種不獲得孳息的使用。用益權人可以使用他人的土地并獲取孳息,但不得實施損害土地價值的行為或是改變土地的“社會經濟功能”[6]224。因為用益權是針對特定的人設立的,因此只存在供役地而不存在需役地,同時也因為這種密切的人身相關性,用益權也是不可轉讓的。不同于地役權對土地的使用,用益權在對土地的使用時間上是有限制的,“一般為有生之年,或者更短的期限”[5]136,而前者則不受限制,原則上是永久的。
(三)永佃權
永佃權是指對他人的土地長期或永久的使用和收益,并向土地所有者給付一定租金。這項權利來源于一種對穩定經營利用土地行為的肯定性保護。羅馬歷史早期存在未開墾的公共土地(國家的或是城市的土地),在這些土地上產生了長期穩定的租賃關系,在這種土地租賃關系中,租賃一方享有很寬泛的權利,“此項制度遂由債權關系變為物權關系”[9]72。永佃權制度的特殊意義在于賦予佃權人一種充分的權利以維持對土地的高效利用與收益的保護。包括:第一,“不受限制的享用土地,但必須履行不破壞土地義務”[8]203;第二,對土地收益的權利。在孳息與土地分離時,當然的獲取孳息;第三,寬泛的處分行為。永佃權可以被繼承、轉讓,并可以針對該土地設立“役權、用益權、抵押權或者轉租永佃權”[4]126。
(四)抵押權與質押權
在羅馬法中,針對土地的擔保物權主要集中在抵押與權利質押上。抵押權在羅馬法中又稱為協議質押,是指一種基于雙方當事人協議設立但不對客體移轉占有的物的擔保物權。這里雖然用質押的詞語,但不同于現代法中的概念,這其中所要強調的是指這是一種“不導致土地所有權直接移轉的物權性擔保”[6]239。在前文中提及,羅馬法中對“物”的觀念之中包含“權利”,這在擔保物權中也有所體現,用益權人對土地的用益權、地役權中的通行權、永佃權都可以設立擔保物權,這就是關于土地的權利質押[4]131。羅馬法中這種所有權“積極的權能分離”[2]226是對土地價值的提升,它利用了土地的交換價值,刺激了交易。
在羅馬法的他物權制度中另有與土地相關的地上權制度。地上權制度是為了克服因土地的絕對性所造成的土地添附理論,即當利用者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進行營造行為,其所附加和進入土地的物會被判斷為歸土地所有主所有。查士丁尼的《法學階梯》中闡述為“如用自己的材料在他人土地上建筑房屋,建筑物歸屬土地所有人;在這種情況下,材料所有人失去了他的所有權,因為如果知道自己在他人土地上營造即被假定為自愿讓與其材料”[10]54。而這種對土地所有權的無限擴大會極大的降低土地的利用效益,故產生了地上權制度加以彌補。地上權是指“使人充分享有某一建筑物或其中一部分的、可以轉讓并可轉移給繼承人的物權”[8]204。這種權利保障了在土地承租關系的基礎上,對租賃人通過土地利用而獲得的收益,但這種權利的標的是土地之上的建筑物,是針對建筑物所享有的地上權。[11]“它是一種對建筑物的權利,但不涉及建筑物下面的土地”[5]140,故未列為土地權利中的一種。
三、結語
在羅馬法時期,雖存在土地所有權的絕對性這一特點,但是土地的他物權制度亦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土地利用效益的提高是其制度的核心目的。這種他物權制度的設立是對土地利用規律的遵循,使土地的權利狀態與實際利用狀態吻合,也通過此類物權關系使利用者也是權利人對客體的權益趨于穩定與安全,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也是對更多樣利用行為的促進,從而使土地的效益最大化。與所有權相比,他物權表現為一種積極的權能,聯系的是不同主體之間圍繞在權利客體之上的效益博弈與合作。正如學者江平先生的評價“所有權是社會個別成員利益的體現,而他物權則是社會整體利益的體現”[2]277。這種劃分是羅馬法中對社會中個體對物的利用關系的抽象化的深刻總結,同時這也是后世對其繼承與發展的基礎所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