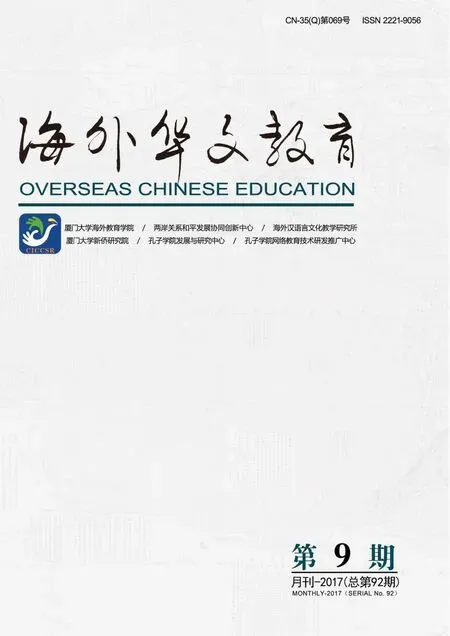《論語》中西英譯本對比研究
——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中心
秦芳芳
(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中國廈門361102)
《論語》中西英譯本對比研究
——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中心
秦芳芳
(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中國廈門361102)
經典的翻譯是中國文化向世界范圍內傳播的有效途徑之一。其中,《論語》在典籍的對外傳播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雖然《論語》的英譯歷史并不長,但因其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它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迅速而廣泛,成為中國經典外傳的典型示例。而最主要的傳播方式還是通過海內外學者對《論語》文本的翻譯和闡釋。本文對《論語》英譯的發展歷程做了簡要回顧,對英譯《論語》的動因做了簡單分析,并集中對比19世紀出版的理雅各和辜鴻銘二人的《論語》英譯本,從文本意義與風格、對《論語》的誤譯兩方面進行了比較。除了從語言層面對兩個版本的英譯進行探討,還深入到《論語》文本的核心觀念層次,探討經典翻譯中的文化闡釋和傳播問題,揭示了造成翻譯不準確或誤讀的深層原因。最后,對今后的《論語》及其他典籍翻譯和傳播工作提出一些建議。
《論語》英譯;文化闡釋;對比研究
《論語》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的作品之一,是中國人的哲學觀念、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行為準則的集中體現,《論語》英譯的研究對今后的傳統典籍翻譯和對外傳播具有主要的學術價值。
16世紀末,耶穌會士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帶著傳播基督教的使命來到中國本土,遭遇了當時作為明王朝正統思想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東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產生了碰撞。一方面,西方宗教信仰和科學知識的到來給傳統的中國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的典籍尤其是儒家經典也被傳教士們翻譯出版,在西方推廣傳播,對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極大影響。
為了順利實現在中國傳教的目的,西方來華傳教士大都花大量的時間學習中文,研究中國當時的主流思想,并努力了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他們通過書信和著述的方式向西方介紹中國,大批儒家經典被陸續翻譯成拉丁語、法語、德語、英語等各種語言在歐洲出版。傳教士們選擇儒家經典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儒家思想是當時中國社會統治階級所秉持的正統意識。傳教士們認為,只有了解儒家思想才有可能獲得中國上層社會人士的支持,他們的傳教事業才能得以進行,才能真正產生影響;二是他們認為孔子思想與基督教教義具有相通性,與其他學派相比,儒家與基督教更能和諧共處(事實上當時的儒學已經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兼采諸子百家,與孔子初創時已大有不同)。
一、《論語》英譯的發展歷程
嚴格意義上說,《論語》英譯開始于17世紀早期,(最早的《論語》英譯本出現在1691年,是從拉丁文轉譯而來的)一直延續至今,且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和歐美漢學研究水平的提高,《論語》的復譯在數量上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19世紀,英譯《論語》的多為英國來華傳教士,在本文所選擇研究的譯者理雅各之前主要有兩人,一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他將《論語》的前十篇翻譯出版,譯名為“The Works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with a Translation”,他完全采用直譯的方式,盡可能使譯文與原文在詞序和句法保持對應,在文本意義的闡釋上,他選擇完全依照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的解釋。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馬士曼沒有參考任何的《論語》英譯本,其他的文獻資料也相當匱乏,再加上受到“禮儀之爭”的影響,他本人一生未能進入中國境內,無法與中國學術界溝通交流,該譯本的質量也自然得不到保證;二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英華書院院長柯大衛(DavidCollie,?-1828),他是歷史上第一個英譯“四書”的人,(馬祖毅、任榮珍,2003:42)其“四書”譯本的英譯名為“The Chinese Classic Work,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與馬士曼相比,柯大衛有了可以參照的《論語》拉丁文譯本和馬士曼的英譯本,而且他還把“四書”的英譯本用作書院里中國學生學習英文的教材,他的譯文得以在教學過程中不斷修改。
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經典英譯被視為是里程碑式的翻譯,這主要是由于他的經典譯作是迄今為止數量最多的、他是目前翻譯中國典籍最多的西方漢學家。除了數量上的優勢以外,理雅各的譯作質量也頗高,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他的《中國經典》譯本每一頁按照原文,譯文,注釋分別排列,其中注釋部分占了極大的篇幅。在第一卷正文之前有很長的“導言”,介紹了孔子的生平、儒家思想以及對他儒家學說的總體評價。
辜鴻銘(1857-1928)比理雅各稍晚,是最早將儒家經典翻譯成英文的中國人,其《論語》英譯本在1898年出版。在翻譯中,辜鴻銘采用歸化策略,在注釋方面,常用西方歷史上的人與物來比喻儒經中的人與物,用基督教和西方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來比擬《論語》中的一些人,譯本行文流暢,富有文采。
傳教士漢學之后,西方漢學進入專業漢學時期。這一階段,譯介經典影響較大的是英國漢學家翟里斯(Lionel Giles,1875-1958),他批駁了長期以來西方對儒家思想的錯誤認知,正文部分別出心裁地將章節按主題進行了分類,打破了原書的布局,使《論語》看起來更有條理,更具系統性。這樣的改動反映出了翟氏本人對《論語》的獨特解讀。林語堂(1895-1976)是繼辜鴻銘之后,把《論語》譯成英文的又一個中國人,他對《論語》的部分章節進行了英譯,并且像翟里斯一樣將孔子的言論根據不同主題分成了數篇。到20世紀,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論語》譯本于1938年在倫敦出版。目前,該譯本已經成為最流行的《論語》譯本之一。
亞瑟·韋利之后,隨著美國漢學的興起,美國逐漸成為漢學研究的重鎮。這一時期,美國漢學家和華人在《論語》英譯中擔任了不可替代的角色,《論語》復譯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且譯本風格也更加多元化,有哲學型翻譯(安樂哲,羅思文譯本),學術性譯本(斯林哲蘭德譯本),有針對普通讀者的大眾型翻譯(亨頓譯本),甚至還有適合青少年讀者閱讀的插圖版譯本。這一時期的國外譯本最具代表性的是龐德的譯本,他的譯本主觀發揮較多,極具創造性,這與其詩人的身份和相對薄弱的漢學功底有關。安樂哲和羅思文的譯本強調中西哲學的差異,美國作家和漢學家亨頓的《論語》譯本面向普通讀者,通俗易懂,可讀性高。英譯《論語》的海外華人代表有劉殿爵、黃治中、李祥甫等。國內從事《論語》翻譯工作的有北外的梅毅仁,還有劉重德、羅志野、楊伯峻、王福林等,此處不再一一贅述。
不同的歷史時期,譯者來自不同背景,他們懷抱著不同的翻譯目的,使得《論語》翻譯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其中,從傳教士漢學到專業漢學的過渡時期是學界爭論最多的階段之一,這一時期涉及文化闡釋者的身份變更,(金學勤,2009)還涉及到譯者的國別問題,筆者選擇對理雅各和辜鴻銘兩位極具代表性的譯者及其譯作進行探討。
二、英譯《論語》的動因
翻譯從來就是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在具體的現實環境下,譯者從事的翻譯活動,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翻譯是不同語碼之間的轉換,更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因此必然受到詩學、意識形態和贊助人的操控。(徐珺,2014)在翻譯交流展開的時候,源語文本的選擇,譯者的動機和翻譯策略,具體的翻譯方法,譯本的流傳和譯文讀者的選擇都受到諸如主流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
17世紀以來,西方各國傳教士們在客觀上為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早期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帶著傳播福音、將儒經“為我所用”的目的翻譯儒經。理雅各繼承了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們在中國開辟的傳教傳統,采取了一系列融入中國本土文化的策略,其中,將儒家經典翻譯成西方語言在他們看來是行之有效的傳教方法之一。
與耶穌會士不同的是,理雅各將儒家經典翻譯成了英文,而不是拉丁文、法文等。理雅各之前,有馬士曼和柯大衛翻譯過儒家經典,但理雅各認為他們的翻譯不成系統且比較粗糙,他歷經重重困難將中國典籍翻譯成英文。理雅各自己在解釋為什么要把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時說:為了讓世界了解中國這偉大的帝國,尤其是為了順利開展我們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并獲得永久的成功,這樣的學術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認為,將孔子所有的著作翻譯并加上注釋出版,會為未來的傳教士們開展傳教工作帶來極大的便利。(理雅各,1960:1)理雅各抱著這樣的目的來解讀和闡釋《論語》,也直接影響了他對文本意義的考證和最終的選擇,以及他對儒家思想體系的整個評價。
辜鴻銘作為第一個把儒家經典翻譯成英文的中國人,他的翻譯動機與作為傳教士的理雅各的翻譯動機截然相反。辜鴻銘出生于一個華僑家庭,從小就學習英文。后留學英國,師從英國著名的浪漫主義思想家卡萊爾。十多年的留學和生活經歷,也為其日后英譯《論語》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在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辜鴻銘看到西方強大的物質世界背后的道德淪喪。回國后,目睹古老的華夏文明慘遭西方列強凌辱的現實,辜鴻銘的保守主義文化觀就此形成,具體以現在他強烈批判西方的物質文化和道德淪喪,而極力宣揚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此外,對歐洲的了解使得辜鴻銘觀照中國社會的文化時有了獨特的視角,文化的迥異和心理上的落差成為辜氏美化東方的內在動因。他認為,理雅各的《中國經典》未能理解儒經的真諦,其翻譯顯得行文呆板且錯漏百出,沒有把中國的文學和哲學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辜氏對西方漢學家尤其是理雅各儒經翻譯的強烈不滿成為他翻譯儒經的直接動因。
翻譯是一個復雜的文化交流過程,但它首先是一個語碼轉換的問題。語言是文本意義和文化信息的載體,同時也是文化最集中的表現方式。譯文在何種程度上傳達原文意旨、再現原文風格,這與譯者使用語言的方式和水平密切相關。文化是不斷變更和發展的,語言也一樣。譯者生活的時代、接受的教育、具備的文學修養,還有意識形態觀念、宗教信仰、翻譯動機、采用的翻譯策略,都與譯者的語言緊密相關。從功能主義的“目的論”來看,譯者的翻譯動機和目的尤其與譯者的翻譯策略和具體方法有著重要的因果聯系。就《論語》英譯本而言,不同譯本如傳教士譯本和專業漢學家譯本,無論在譯文的詞匯選擇和使用上,還是在整體的語言特征上都有差異。這除了與譯者本人的學術修養和性情有關之外,更與他們特別的翻譯動機和目的相關。
三、文本意義與風格的比較
(一)文本釋義上的差異
理雅各的《論語》譯本采用的是典型的學術型翻譯(scholarly translation)。如前文所說,理雅各將《論語》放在《中國經典》的第一卷。《中國經典》中注釋部分占據了幾乎整個正文的三分之一還多,除了對原文文義的注解以外,理氏還對一些關鍵術語作了解釋和評價,并且加入了自己的認識。《論語》20篇,每一篇的篇首都有對該篇要旨的簡單概括以及篇名意義的解釋;正文的每一句都有注釋,按基本結構劃分,每章的注釋可以分為三部分:首先對該章大意進行極簡的概括,全用大寫字母書寫。之后,解釋該章中的文化負載詞和疑難的字詞,其中還經常出現這些詞匯意義與英語中文化詞的對比。最后是理雅各對文本內容的評論,或對其他可供參考的解釋的介紹。采用如此詳盡的注釋,將語言高度精煉的《論語》翻譯成一部冗長的譯作,降低了文本的可讀性,再加上理雅各的諸多注釋準確性存疑,自然遭到了不少批評的聲音。但是客觀來說,理氏的譯本利大于弊。他的譯本內容豐富,詳盡的注釋為讀者提供了大量關于字、詞、句、章、篇的信息以及可能的不同解釋,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他繼承了中國的經書注疏傳統,讓讀者對儒經注疏這一獨具特色的中國學術傳統有所認識,也為后來的譯者在典籍翻譯的方法上提供了借鑒,為中國經典在西方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影響。
當然,理雅各的“學術型翻譯”與其翻譯的動機和目的緊密相關。按照理氏的標準,文本的意義是第一位的。他追求準確傳達經文的意思,并盡量保持譯文與原文的行文結構一致,因此采用直譯的方法,有時甚至是逐字翻譯。這種在行文的詞序和結構上緊貼原文,追求句式對應的翻譯,與理雅各的翻譯原則和意向讀者有關。他最初翻譯儒經就是為了為后來的傳教士提供學習中國語言的教材,這種“忠實”于原文的翻譯方法更能幫助初學者把握《論語》的特點。整體上看,理雅各的努力是成功的,也體現了他高超的翻譯技能,然而,這樣的翻譯方法導致了譯文有時用詞別扭,結構生硬,句子冗長,文本意義晦澀難懂。
辜鴻銘的《論語》譯本跟理雅各的譯本形成鮮明對比。與理氏譯本相比,辜氏的譯本不僅沒有《論語》原文,注釋也很少。在翻譯時,辜鴻銘大多采用目的語讀者熟悉的詞匯,使用現代英語中地道的句子結構,因此,他的譯文流暢易懂,富于文采。在辜鴻銘看來,《論語》不僅是一部哲學和倫理的著作,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他批評理雅各的一個理由就是他認為理氏的譯文句式冗長,行文僵化,在這種認識的前提下,辜氏在翻譯過程中就非常小心避免這些缺陷。他對《論語》中的專有名稱和術語的處理別具一格。比如將原文中除顏回和子路以外的孔門弟子的名字都譯作“a disciple(一個弟子)”,將當時除魯國(the native State of Confucius)以外的諸侯國譯作“a certain State(某國)”或“a foreign State(外國)”;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中的《詩》譯為“The Book of Ballads,Songs and Psalms”,而不是最常用的譯法“The Book of Poetry”。但可以想見的是,辜氏選擇用英文的固有詞匯來翻譯儒經中的特有概念,就不免牽強甚至相去甚遠。例如,他常常將“禮”譯作“art”,通篇都將“君子”譯作“a wiseman”。從注釋上看,如前文提到的,辜鴻銘用西方歷史人與物比喻《論語》中提及的人與物。他常用基督教和西方歷史上的人物來比喻《論語》中的一些人。在《為政》篇第十章譯文的腳注中,他將顏回比喻成“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意思是“孔門福音中的圣約翰”,這實際上是將孔子最寵愛的弟子比作耶穌最寵愛的圣徒。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中的《詩》譯為“The Book of Ballads,Songs and Psalms”,其中“Psalms”是指贊美詩或《舊約》中的詩篇。在整個譯本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此外,辜氏大量采用西方思想家、作家、詩人的言語為《論語》中的章節加注,并不時對中西文化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比較闡釋,辜氏《論語》英譯本的副標題就是“一部引用各地和其他西方作家言語作解釋的新的特別譯本”。在正文中,辜鴻銘善于通過增加適當的字詞實現上下文的連貫,把《論語》的對話體語言很好地再現出來,因此他的譯文讀來生動有趣,地道自然。
(二)譯文風格上的差異
《論語》本身就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作品,全書語言精練但意義豐富,有抒情有說理,運用多種修辭手段,刻畫了許多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
前文談到,理雅各的譯本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盡量和原文句式保持一致。但是漢語和英語存在巨大差異,要將含蓄簡約的古代漢語轉換成要求形式完整句意明晰的現代英語,難度可想而知。在詞匯選擇上,理氏多選用正式用語,書面氣息濃厚,且經常顯得生澀和不恰當。在漢語句子中出現排比和并列時,常有不必要的重復。有時,為了與原文詞序統一,理氏將英文句子的結構做了大幅調整,使得整個句子生硬古怪。這無疑與《論語》原文活潑輕快和高度隱喻的特點分道揚鑣。
辜氏強調《論語》本身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他翻譯《論語》的直接目的就是糾正理雅各譯文存在的問題。他的譯文基本能夠準確地把握原文的風格和氣勢,且注重傳達原文中對話體的語氣,此外還注意增加一些小詞來增強對話的生動性。例如:
1.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論語·子罕》)
理雅各譯文:Yen Yuan,in admiration of the Master’s doctrines,sighed and said,‘I looked up to them,and they seemed to becomemore high;I tried to penetrate them,and they seemed to becomemore firm;I looked at them beforeme,and suddenly they seemed to be behind.
辜鴻銘譯文:A disciple,the favourite Yen Hui,speaking in admiration of Confucius’teaching,remarked,“Themore I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Themore Ihave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When Ihave thought I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lo!It is there.”
兩段譯文高下立見,理雅各的譯本顯然刻意追求與原文句子結構的一致,使譯文看起來生硬別扭,沒有生氣;而辜鴻銘的譯本則非常巧妙地運用了一個比較級的結構,是英文中地道的表達,且譯文中添加的語氣詞“lo!”起了點睛的作用,將整個對話的場景都活化了。
2.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
理雅各譯文:The Master said,“My doctrinesmake no way.Iwill get upon a raft,and float about on the sea.He thatwill accompanymewill be Yu,Idare to say.”Tsze-lu hearing thiswas glad,upon which the Master said,“Yu is fonder of daring than Iam.He does not exercise his judgment upon matters.”
辜鴻銘譯文:Confucius on one occasion remarked,“There is no order and justice now in the government in China.Iwill betakeme to a ship and sail over the sea to seek for it in other countries.If I take anybody with me,Iwill take Yu.”referring a disciple.
The disciple referred to,when he heard ofwhat Confucius said,was glad,and offered to go.
“My friend,”said Confucius then to him,“You have certainlymore courage than Ihave;only you do not exercise judgmentwhen using it.”
在這里,辜鴻銘用了英文作品種最常用的斷句方式,在孔子的言語之后,添加了“referring a disciple”,在最后的回應前,加了一個“My friend”,其實是對他的學生說話,“My friend”這樣顯得孔子平易近人,幽默鮮活。相較于理雅各一味的“themaster said”,辜氏的譯法則靈活得多。
總之,從語言層面來講,兩個譯本在領會文義傳達和譯文風格上存在明顯差異。
四、對《論語》的誤譯對比
《論語》是一部語言高度簡練的作品,這一特點也使得它難解,容易造成歧義。語言本身的變遷,具體語境的缺乏,社會背景的變化更為《論語》文本的理解增加了難度,歷代注疏家對《論語》的解讀就各有不同。中國的學者們對于《論語》尚有解釋不清的地方,外國學者在理解上的偏差就更是在所難免。
理雅各對《論語》文本的誤讀誤譯主要體現在對個別字句的理解不準確以及對某些章節中的整句所傳達的思想和概念理解不當。這主要是因為理氏在從事《論語》的翻譯工作時,漢學功底還不夠扎實,當時還沒有中國學者王韜的細心幫助,何進善、洪仁玕在翻譯上給與他的幫助其實甚少,他在很多疑難地方未能準確把握儒經真義,過分拘泥于文本的字面意思和句子形式,又過度依賴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導致了一些地方受到了朱熹誤讀的影響。舉例為證:
3.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篇第十章)
理雅各譯文:Confucius said,“The superior man has nine things which are subjects with him of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In regard to the use of his eyes,he is anxious to see clearly.In regard to the use of his ears,he is anxious to hear distinctly.In regard to his countenance,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benign.In regard to his demeanour,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respectful.In regard to his speech,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sincere.In regard to his doing of business,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reverently careful.In regard to what he doubts about,he is anxious to question others.When he is angry,he thinks of the difficulties.When he sees gain to be got,he thinks of righteousness.”
可以看出,理雅各的遣詞用句非常地書面化,句式的重復也是為了與原文保持一致,但他并沒有將每個詞的意義都闡釋明確。比如“忿思難”中的“難”,他譯作“difficulties”,并且注釋中也未做解釋。原句意思是“在憤怒的時候要考慮可能造成的后果”,理氏的翻譯讓人不知所以。
辜鴻銘的譯本在字詞理解上的失誤不在少數。在特有概念的名稱上,辜氏過分追求英文表達的地道,常常用詞太過牽強,它對儒家哲學中的特定術語的處理也相當值得商榷。以下舉出具有代表性的兩個例子:
4.子曰:“君子不器。”
理雅各譯文:The Master said,“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
辜鴻銘譯文:Confucius remarked,“A wiseman will notmake himself into ameremachine fitonly to do one kind ofwork.”(《為政》篇第十二章)
原文意思是君子不會拘泥于教條形式。辜鴻銘的譯文回譯過來就是“明智的人不會讓自己成為一個可憐的機器,只適合一種工作”。這種譯法顯然是不合適的,其一,“君子”不是簡單的一個“wise man”可以解釋的;其二,辜氏只翻譯了原文的字面意思,對于外國讀者來說,其深層的含義在譯文中難以知曉。理氏在這里將“器”譯作“utensil”,但他在注釋里做了解釋:不同的器具有其特定的用法,“utensil”在這里只是一個比喻。
5.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篇第十四章)
辜鴻銘譯文:Confucius remarked,“The civilisation of the present Chou dynasty is founded on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two preceding dynasties.How splendidly rich it is in all the art!I prefer the present Chou civilisation.”
此處,周借鑒與夏商兩代的是“禮”,將“禮”譯作“civilisation”,明顯將概念擴大化了,而后面的“art”也很偏頗,筆者認為,理雅各將其譯作“regulation”似乎更為恰當。
五、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和文化闡釋
《論語》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影響深遠的哲學典籍,直到今天仍是中國人重要的精神源泉。單從語言層面對其英譯進行探討是不完整的。作為《論語》的譯者,無法回避地要對原文本所體現的哲學內涵和核心價值作出解釋,而這兩者主要是通過核心概念得以體現的。《論語》涉及的核心概念有數十個,最重要的便是“仁”。此外還有“禮”“義”“德”“君子”等等。這里選取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仁”和“君子”,分別探討理,辜二人的翻譯。
(一)“仁”的翻譯與理解
“仁”是在《論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核心概念,一共出現了109次。西方譯者認為,“仁”在英語里沒有一個統一的對應詞,翻譯時要放在具體的語境當中,根據上下文做出不同的解釋。狹義的“仁”與“智”、“禮”、“勇”一樣是指一種具體的德行,但是在《論語》的絕大部分地方,“仁”是用來指完美的德行,這種廣義層面上,它涵蓋了“智”、“孝”、“忠”、“禮”等多重內容。
兩位譯者第一次遭遇“仁”是在《學而》篇的第二章,舉例說明如下:
6.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學而》篇第二章)
理雅各譯文:The superiorman bends his attention towhat is radical.Thatbeing established,all practical courses naturally grow up.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are they not the root of all benevolent actions?
辜鴻銘譯文:A wiseman devotes his attention to what is essential in the foundation of life.when the foundation is laid,wisdom will come.Now,to be 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 do not these form the foundation of amoral life.
在這里,理雅各援引了朱熹的注解“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the principle of love,the virtue of the heart),將“仁”譯作“benevolent”,并且解釋道“benevolence”與“仁”的意思相近,但無法給出一個統一的譯名。“benevolence”意為“仁慈,善舉”,強調的是利他。“仁”本義專治君王或統治者對下屬和臣民的仁慈之心。根據原文文意,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是治國的根本。理氏在此處將“仁”做此翻譯是很恰當的。辜鴻銘則將“仁”翻譯為“moral”,即“道德”。這體現了他對道德的強調,但無形中擴大了“仁”在這里的涵義。
7.子曰:“巧言令色,鮮仁矣。”(《學而》篇第三章)
理雅各譯文:Themaster said,“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
辜鴻銘譯文:Confucius remarked,“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
理氏在此處將“仁”譯作“true virtue”,說明理雅各明白“仁”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此處做了區分。實際上,在以后的譯文中,理雅各用的最多的譯名就是“virtue”,“virtue”基本意思是“崇高的德行”,但在《論語》中還有一個“德”字。顯然“仁”與“德”是不同層面的概念,“仁”的涵義要比“德”廣泛的多。在《述而》篇中,“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為“上天把德賦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樣呢”。孔子在此處認為自己是有德之人,但他從未以“仁”來贊許自己。筆者認為,“virtue”用來翻譯“德”這個概念更為合適,但辜鴻銘同第一次一樣,將“仁”翻譯為“moral”,且在以后出現“仁”的場合中基本都將其譯作了“moral”,不是辜氏不明白文中“仁”的涵義各有不同,而是刻意追求譯名的統一,為了使西方的讀者閱讀方便,也讓他們對專有的核心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君子”的翻譯與理解
“君子”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僅次于“仁”(108次)。君子在孔子的時代,更多地指稱有仁德的,高尚的人。“君子”的英譯非常多。理雅各在《學而》篇第一章的注釋中解釋道,“君子”的本意為“a princelyman”,對應的與它意義相反的詞是“小人”,“a smallman,mean man”,但要根據不同的場合對其進行恰當的翻譯。例如他在第一章“不亦君子乎”中將“君子”譯作“aman of complete virtue”,而在接下來的第二章中將“君子”譯成了“the superiorman”。在第二章的注釋中,理雅各也就此做了解釋,他認為此處的“君子”沒有前一章的意義強烈(has a less intense signification here than in the last chapter),所以譯成了“the superiorman”(理雅各,1960:139)。
如我們上文討論“仁”時所舉出的例子,理雅各在大部分時候將“君子”譯作“the superiorman”,在他看來,“君子”就是尚德之人(理雅各,1960:157),比普通人要高貴,因此,“the superiorman”是最好的表達,但理雅各也根據上下文在不同的場合對“君子”做出不同的翻譯。比如,在《泰伯》篇第二章“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中,他將“君子”譯作“those who are in high stations”,并在注釋中解釋道這里的“君子”同之前的用法不同,更多地強調地位而不是道德(理雅各,1960:208)。辜鴻銘則如我們上文看到的,他基本上是將“君子”翻譯成“wiseman”,統一的譯名方便了讀者,但事實上這無疑簡化甚至扭曲了“君子”一詞的文化內涵。因為無論從社會地位還是道德品行的角度來看,“wiseman”都沒能傳達出“君子”的涵義。
在對核心概念詞的誤讀的背后,有其深層的原因。在理氏看來,孔子思想學說遠遠遜色于基督教的教義。于是,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將基督教的神學觀念投射到了儒家思想里面,在譯文的導言和注釋中甚至將孔子和基督進行比較,或者對《論語》中近似基督教義之處巧做他解,以得出基督勝于孔子的結論,而辜鴻銘在保守主義文化觀的指引下,批駁了基督教傳教士和漢學家對孔子教義的曲解,用地道的英語表達儒家思想也成為他翻譯《論語》的指導原則。辜氏曾在他的譯本序言中說過,“我們在翻譯中盡可能讓孔子及其弟子的交流顯得地道流利,就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人所要表達中國圣賢們所表達的思想時應當采用的語言一樣”,他想通過這樣的方式改變西方讀者對于中國人和中國思想的誤讀。
六、結 語
綜上所述,理雅各的譯本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為后來的《論語》譯者和翻譯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同時也為西方讀者提供了了解中國文化的敲門磚。他的譯本不僅如實傳達原文本的意義,詳盡的注釋也把經典注疏的傳統帶到了西方漢學的視野里。另外,他的譯文體例也具有開創性意義,影響了后來學者們的諸多譯本。辜鴻銘翻譯論語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對理譯本的諸多不滿,他糾正了理譯本中的不少誤譯處,也使得后來的譯者受益頗多。在孔子形象的構建上,理雅各的譯本給人留下的孔子是守舊循禮的道德家形象,辜鴻銘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認識,在他的筆下,孔子幽默風趣,是個鮮活生動的形象。辜氏的譯本文采斐然,可讀性強,在西方世界產生不小的影響。
經典凝聚的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但經典從來不是靜止的,對于經典的翻譯也會一直進行下去,對于翻譯的研究也是如此。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還是要看到,經典(包括《論語》)的翻譯者們在翻譯的過程中,無一不是將其自身傳統的特定視域同經典傳統的流動視域相結合,以實現自我的價值訴求。(王琰,2012)這給我們的啟發是,在進行經典的翻譯和傳播活動的時候,要盡可能利用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弘揚中國傳統經典中所涵括的優秀的中國文化。
鄧聯健:《委曲求傳: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漢英翻譯史1807-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
段懷清:《理雅各“中國經典”翻譯緣起及體例考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辜鴻銘:《西播<論語>回譯:辜鴻銘英譯<論語>詳釋》,王京濤譯注,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
韓 星、韓秋宇:《儒家“君子”概念英譯淺析——以理雅各、韋利英譯“論語”為例》,《外語學刊》,2016年第1期。
胡適主編:《文化怪杰辜鴻銘》,長沙:岳麓書社,1988年。
金學勤:《<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
理雅各、馬清河譯:《漢學家理雅各傳》,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年。
王 琰:《漢語視城中的〈論語〉英譯研究》,上海:上海外國語出版社,2012年。
徐 珺:《漢文化經典外譯: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岳 峰:《架設東西方的橋梁: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
ArthurWaley.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New York:Random House,1938.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1-2,Shanghai: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1.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nglishment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spectively Written by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
QIN Fangfang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102 China)
The classic translation is an effectiveway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round theworld.The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Although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not long,it spread quickly and widely in the English world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Society.And the main way of transmission is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mak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ha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motivation to English translate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Then compare the meaning of text,style of translation and themistranslation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from Legge and Ku Hung-ming).In addition to study the two versions from the language,also deep into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during the classical translation.Then reveals the deep cause of the inaccurate translation and misreading.Finally,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and other classics in the futu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us Analects;cultural interpretation;contrastive study
H159
A
2221-9056(2017)09-1267-09
10.14095/j.cnki.oce.2017.09.011
2017-02-17
秦芳芳,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漢語國際教育。Email:331299386@qq.com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世紀稀見英文期刊與漢語域外傳播研究”(15BYY05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7-19世紀歐洲漢學視野中的漢語類型特征研究”(13YJAZH021)、廈門大學社科繁榮計劃科研啟動項目“歐洲的漢語傳播與華文跨境教育研究”(HGF04)的階段性成果,方環海為本文通訊作者。同時,本文在寫作的過程中,參考了學界有關論著的論點,在此一并致謝。感謝《海外華文教育》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文中不妥之處概由本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