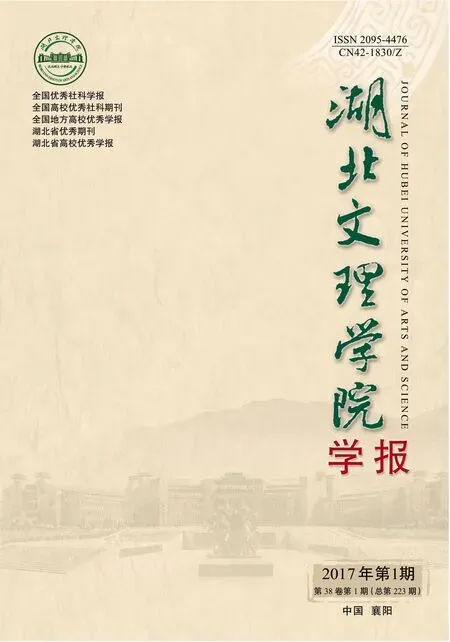向死而生的游歷式敘事
——論方方小說《軟埋》
李 嵐
(湖北第二師范學(xué)院 文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205)
向死而生的游歷式敘事
——論方方小說《軟埋》
李 嵐
(湖北第二師范學(xué)院 文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205)
方方的《軟埋》是作家對于歷史觀的一次文學(xué)表達,小說采取了游歷式敘事,通過“陰間”“陽世”兩段旅行將“歷史”與“現(xiàn)實”并列起來進行對比和觀照,在極端敘事下凸顯主人公對于記憶和歷史的矛盾態(tài)度,而其中對于過往的反思,成為了映照現(xiàn)實人生態(tài)度的鏡像。
《軟埋》;游歷式敘事;歷史觀;極端敘事;女性視角
2016年,湖北作家方方在《人民文學(xué)》第2期發(fā)表了新作《軟埋》。這個古怪的名字直接切入小說主題,方方對此解釋說,在一些地區(qū)的民俗文化里,“軟埋”意味著沒有棺槨,直接用泥土埋葬,并且導(dǎo)致將沒有來世,“而一個活著的人,忘卻過去,忘卻自己,無論是有意識地封存往事,還是下意識地拒絕記憶,也是軟埋。只是軟埋他們的不是泥土,而是時間。時間的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1]初步看來,這部小說沒有像當(dāng)年的《風(fēng)景》那樣用新寫實的手法去探究環(huán)境與人性的關(guān)系,也不同于《出門尋死》《萬箭穿心》《惟妙惟肖的愛情》去寫女性在愛情和婚姻里的掙扎或妥協(xié),也沒有構(gòu)筑一個尷尬的情境,讓人物如《琴斷口》《中北路空無一人》里的那樣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濘。它像一部歷史小說,講述了地主士紳家族在土改中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可是又和方方著名的歷史題材小說《民的1911》《武昌城》不同,它沒有敘述某一段歷史的全貌,也沒有刻畫真實和虛構(gòu)相結(jié)合的歷史人物,而是將歷史的一點碎片,藏進一個普通女人丁子桃的夢境,并且最終也沒有昭示于后人。可以說,《軟埋》是一部運用了一定的敘事技巧來直接討論“態(tài)度”的小說,這種“態(tài)度”是一種如何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更是如何面對“活著”的態(tài)度。
一、游歷式結(jié)構(gòu)與探尋真相之旅
丁子桃是一個失憶的女人,她忘記了過去,半輩子給人做保姆,嫁給同樣身世模糊的救命恩人吳家名醫(yī)生,丈夫死后她拉扯大兒子青林。在苦盡甘來,住進兒子買的別墅后,卻失去了意識終日昏睡不醒,讓青林擔(dān)心愧疚不已。同時,青林從母親之前的言行、父親的遺物、以及老板的父親劉晉源的往事里,逐漸發(fā)現(xiàn)了母親身世的蛛絲馬跡。
由此,小說就將“歷史”和“現(xiàn)實”通過“陰間”“陽世”兩段旅行擱置到了一起。
從第五章開始,丁子桃在昏迷中走進地獄,第七、九、十一、十三章,她的記憶在對十八層地獄的探索里一步步重現(xiàn):她的娘家和夫家均是土改中被批斗的地主鄉(xiāng)紳,見親家家破人亡之后,公公陸子樵擔(dān)心死前受辱,決定帶著全家十余口人自盡,以軟埋的方式直接入土,安排媳婦胡黛云掩埋親人,帶孫子汀子逃走。逃亡途中,汀子淹死,胡黛云被人救了,巨大的刺激讓她忘記了一切,變成了丁子桃。丁子桃始終沒有醒來,這些真相伴隨她走向死亡,永不重見天日。
在第六、八、十、十二、十四章里,兒子青林卻在到處尋找真相。他發(fā)現(xiàn)目不識丁的母親丁子桃能吟詠詩文,工于刺繡,似乎受過很好的教育,“且忍廬”“三知堂”等僅有只言片語的線索也終于在陪伴老板的父親劉晉源旅行懷舊的途中,慢慢浮出山林,他知道了父親與劉晉源有深厚的友誼;劉晉源是個老革命家,戎馬一生戰(zhàn)功赫赫,他尋覓著老戰(zhàn)友老鄉(xiāng)親,講起過去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感人至深;母親身世凄慘,“且忍廬”“三知堂”正是她過去生活的地方……他接近了歷史真相,卻又決定就此結(jié)束探尋。
兩段旅行是并行展開的,在敘述這一部分的時候,小說使用了旅程化的結(jié)構(gòu)和線性的敘事方式,分別以丁子桃和青林為視角中心,以她和他的行蹤為線索,完成了一段記游的過程。陳平原認(rèn)為,“記游者注定應(yīng)該是一個觀察者。倘若他觀察的不是山水而是人世,記錄的不是真實的游歷而是擬想中的游歷,那就可寫成一篇游記體的小說了。”[2]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篇小說的基本結(jié)構(gòu)是有游記體小說的特征的。游歷者游觀和游感的真實性被帶到了小說里,尤其是丁子桃的地獄之旅。
但是,單純的游記體小說難以謀篇布局,被游歷者的單線視角局限,以游蹤為線索不利于情節(jié)的鋪設(shè)。所以,小說采取了兩種辦法來解決,首先是將“陽世”與“陰間”兩段旅行并列展開,互為補充,線索單一卻清晰,彌補了單純游記體敘事的單調(diào)。其次,在必要時候,離開丁子桃和青林的視角中心,轉(zhuǎn)為全知敘事。例如,每當(dāng)丁子桃進入一層地獄,就很快隱退,代之以胡黛云,她作為親身經(jīng)歷者敘述更直接,丁子桃只在感嘆或評說時出現(xiàn)。現(xiàn)實中,重要的線索人物劉晉源也會脫離陪伴人青林,以獨自外出的方式接觸到其他線索人物如老起,引發(fā)新的懸念。
二、莊園的隱喻與鉤沉歷史之旅
在虛構(gòu)的《軟埋》里,有一段關(guān)于真實歷史和真實人物的敘述。青林途經(jīng)湖北山區(qū),參觀了李氏莊園“大水井”,聽山民講述了土改期間李氏族人的悲慘命運,令他唏噓感慨了一番。這處李氏莊園“大水井”的歷史是確有其事的,它坐落在湖北省利川市的柏楊壩鎮(zhèn)深山之中,是從晚清延綿至民國的李氏地主家族所修建的莊園群落,因院內(nèi)有一口大水井而以此命名,建筑風(fēng)格中西合璧,兼有土家族的風(fēng)貌,房屋布局繁復(fù),蔚為壯觀。
方方設(shè)計了這樣一個情節(jié)并非僅僅為了描山畫水、豐富青林游玩的蹤跡。昔盛今衰的“大水井”正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三知堂”“且忍廬”的真相。丁子桃的娘家“且忍廬”和夫家“三知堂”均是傳承幾代的地主富戶,族長是典型的封建家長,家規(guī)森嚴(yán),父親胡如勻和公公陸子樵一同東渡日本求學(xué),胡如勻回國經(jīng)商,愛吟詩作賦、書畫傳家,養(yǎng)出了能讀《紅樓夢》、能誦謝朓詩的女兒胡黛云(丁子桃);陸子樵參加了辛亥革命,從政后才告老還鄉(xiāng)。兩個家族都是農(nóng)、商、政結(jié)合的典型,同時也好文學(xué)藝術(shù)。這和“大水井”的背景非常相似,“大水井”的正門門楣上也高懸著“青蓮美蔭”四字,自稱李白后人,實為攀附風(fēng)雅。所以,虛構(gòu)的“三知堂”“且忍廬”是“大水井”的鏡像,特殊時代背景下真實的“大水井”李家的家破人亡的悲劇,就是胡家、陸家的真實寫照。
因此,青林的父親吳家名的家庭變故就不必完整交代了,同樣的地主家庭,同樣年代里家破人亡后逃出的傷心人,有了之前的真實參照與鏡像,小說就將他的經(jīng)歷隱去了。但是這種隱去是“被動”的,作者采用了“不巧”的“巧合”手法。小說里充滿了“巧合”,諸如劉小川是青林的老板,誰也不知道其父劉晉源與青林父親吳家名有多年的友誼,青林母親丁子桃還在劉晉源家做保姆養(yǎng)大了劉小安、劉小川,這些盤根錯節(jié)的關(guān)系直到劉晉源去世才水落石出。但是最關(guān)鍵的“巧合”卻是一場“不巧”,劉晉源新認(rèn)識的老友老起,認(rèn)出了照片上的表兄吳家名,他應(yīng)該姓董,老起成為了唯一知道吳家名身世的人,然而未及告訴青林,劉晉源突然去世了,再也無人知道老起這個人了。唯一線索的中斷,徹底隱去了吳家名的秘密。之后的敘事也同樣如此,想知道真相的人和知道真相的人不斷地擦肩而過,相遇的機會全部錯失,彼此永不知情。
有著過多的巧合的設(shè)計方式,其實是有些妨礙小說情節(jié)上的審美的。但是作者更注重的其實是歷史態(tài)度的選擇而不是故事本身。方方在很多作品中都流露出這樣一種歷史觀念:“歷史是由偶然的許多不期而至的巧合組成的,這些巧合常常改變?nèi)说纳畹缆罚虼巳说拿\恍惚不定,充滿非理性的外來的異己力量”[3],早在《何處是我家園》中,她就說自己之所以喜歡敘述往事,正是因為它能帶來參不透的生命無常感和無法自控感。《軟埋》所描寫的這些歷史已然被如今的人們遺忘,作者借青林提出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必要去追溯歷史,面對人生或歷史的真相時,究竟是要背負因襲的重擔(dān)舉步維艱還是就此放下輕松過日子。胡家、陸家和董家不過是一段邊緣歷史漩渦里的一群小人物,早已是過往云煙。在小說里,丁子桃被動忘記了歷史,將過去“軟埋”了,才好輕松前行。然而即便過好“小人生”“小日子”,歷史依然在那里,而且它所呈現(xiàn)的某種真實,正成為了映照現(xiàn)實人生的逼真的鏡像。昏迷的丁子桃的最后一句話是“我不要軟埋”,正是不要忘記的意思,在小說的結(jié)尾,龍忠勇對鉤沉歷史的堅持讓青林無法輕松。
故事不一定要有結(jié)局,丁子桃和青林不必知道當(dāng)年和陸家一同自盡的陪嫁丫鬟小茶未死,作者也不安排丁子桃恢復(fù)記憶清醒過來與可能還在世的前夫陸仲文以及小茶團聚,這些都是必須拒絕的“巧合”,因為現(xiàn)實人生就是這樣飄忽不定、不可捉摸。但是對于歷史和記憶不能“軟埋”,不管是這些家族的悲慘記憶,還是劉晉源所代表的激動人心、感人肺腑的革命記憶,只有將它們進行修復(fù)與重構(gòu),并且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才能真正面對現(xiàn)實,這是青林在思考的,也正是作者想要告知讀者的道理。
三、“她”的退場與極端命運之旅
方方的小說常常使用女性視角,也擅于刻畫在生活里掙扎的有著強大生命力的湖北女性形象,這些生命力往往來自湖北女人們骨子里的韌勁和蠻力,她們的生存空間逼仄艱難,她們的生活瑣碎尷尬,但是這些“女將”(武漢方言,意為女人)總能抬頭挺胸、抖擻精神走在“男將”(男人)的前面,刀子嘴豆腐心,活得剛烈又麻利,例如《萬箭穿心》中的李寶莉、《水在時間之下》中的水上燈。為了呈現(xiàn)這類激烈的富有沖擊力的個性,方方常常會設(shè)計一些苦難的情境,讓女主人公去掙扎、去迸發(fā)個性中的“潛力”,李寶莉的一念之差,逼死了丈夫,做女“扁擔(dān)”(挑夫)養(yǎng)家糊口半輩子后被滿腹仇恨的兒子掃地出門,水上燈自小被母親為了富貴生活而拋棄,而她一生堅持的不寬恕、不原諒卻讓自己親人離散、形單影只。於可訓(xùn)稱這些情境為“極端敘事”或“刀鋒敘事”:“常見她把筆下的蕓蕓眾生至于‘刀鋒’之上,讓他們一步一步地艱難爬行,看他們?nèi)绾纬惺苓@份‘刺’激和‘鋒’險:是頹然仆倒,被‘刀鋒’割成碎片?還是履險如夷、順利到達終點?抑或歪歪扭扭、磕磕碰碰,任爾遍體鱗傷,也不懼身處‘刀鋒’之上?”[4]在極端敘事的效應(yīng)下,方方的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中都會有一個大寫的“她”,有鮮明的湖北地域色彩和性格特征,棱角分明而立體,讓其他角色黯然失色。
但是,《軟埋》是另一種風(fēng)格,作者已然將這個“她”置身于更為凌厲的刀鋒之上,不但娘家家破人亡,而且夫家為了保存最后的體面十幾人一同自殺,只留她來掩埋,去求生,然后再經(jīng)歷一次喪子之痛,可以說超越了作者之前設(shè)計的所有“‘刺’激和‘鋒’險”。然而,“她”始終沒有迸發(fā)。
小說中,姓名隱藏著記憶的真相,例如吳家名,就是無家無名之人。丁子桃這個名字,是因為胡黛云失憶后一直念著“汀子”,吳家名以為是“釘子”,見窗外有桃花,就給她起名丁子桃。這個名字其實就是“釘住”和“逃走”的對立統(tǒng)一,殘忍的往事讓丁子桃一生處在分裂和掙扎中。小說開始,是以丁子桃的女性口吻來寫,她惶恐、膽怯、整日被陰影籠罩,她和丈夫吳家名有恩有愛,卻覺得有個“魔鬼”在身邊,或許是還未出世的兒子,或許是吳家名。吳家名車禍身亡,她悲痛欲絕又無比輕松安寧,“那只潛伏并且老去的魔鬼,也被這個成天安慰她的男人帶走了,他同時還拔掉了生活背后那支毒刺。仿佛吳醫(yī)生的死有如風(fēng)暴卷走了所有令她害怕的東西,海面安靜如鏡。”[5]這魔鬼就是她對過去的記憶的恐懼,一切與之有關(guān)的人和事她都害怕,哪怕是收容并保護了她的丈夫。直到她記憶有恢復(fù)的跡象以至于病倒陷入昏迷,小說的視角發(fā)生了改變,女性視角導(dǎo)入了丁子桃的地獄游蹤,代以“她”出現(xiàn),通過“她”的眼睛,呈現(xiàn)了過去的記憶的景象;而一致被丁子桃“看”的青林成為了現(xiàn)實部分的視角人物。但是不管是在哪一條線索,不管是丁子桃還是胡黛云,“她”始終是一個怯懦的逃避的人,經(jīng)過慘絕人寰的遭遇,她害怕面對現(xiàn)實,與其說是落水失憶,不如說是她主動放棄了這段不堪的記憶。在歷史洪流之下,“她”無法像方方之前塑造的那些女性一樣抬頭挺胸了,只能縮到小小的軀殼里,一旦記憶的魔鬼來臨,就是“她”的死期將近。所以“她”再也沒有醒來,唯一的抗?fàn)幘褪悄且痪洹拔也灰浡瘢 笨墒牵龑τ洃浀木芙^,也是一種軟埋。但是女性意識的退場,也正好突出了小說所要突出的歷史觀,使得小說得以在“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執(zhí)著回憶與“歷史眼光地對待”之間做一番斟酌,而不是一部常見的女性小說。
總體來說,《軟埋》是方方的一次嘗試和創(chuàng)新。她采取了一個整體的游歷式敘事,將“探尋真相”“鉤沉歷史”“極端命運”的三段旅程融合在一起,用來呈現(xiàn)她對于歷史的態(tài)度。在這部小說中她不去刻意剖析人性之善惡,也沒有直接評述歷史,她對每個人物、每一種回憶都是善意的,即便是對作為陸家悲劇的始作俑者的王金點,她也同情地追溯了陸家與王家的世仇、轉(zhuǎn)述了王金點事后的悔意,因為每個人都是站在個人立場上的歷史中的人。用歷史的眼光去審視歷史,去看不同立場的歷史中的人,而不是忘記或拒絕記憶,這才是真正的“不要軟埋”。
[1] 方 方.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結(jié)局——與《文學(xué)報》記者的對話[J].當(dāng)代,2016(3):108-109.
[2]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8:196.
[3] 童慶炳.中國當(dāng)代歷史文學(xué)的創(chuàng)造與重構(gòu)[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92.
[4] 於可訓(xùn).方方的文學(xué)新世紀(jì)——方方新世紀(jì)小說閱讀印象[J].文學(xué)評論,2014(4):194-202.
[5] 方 方.軟埋[J].人民文學(xué),2016(2):4-107.
(責(zé)任編輯:倪向陽)
A Travel Narration about Death and Life:OnSoftBuryingby Fang Fang
LI L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China)
Fang Fang’sSoftBuryingis a literary expression about the view of history. This novel adopts the travel narration, through the two journeys from “l(fā)ife” to “hell”, to embody the charity of humanism in pondering over our history an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In the extreme narration, the protagonist’s ambivalence about memory and history becomes a mirror, which reflects the real attitude of life.
SoftBurying; travel narration; view of history; extreme narrative; female perspective
2016-11-24;
2016-12-23
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15Q254);湖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xué)重點研究基地湖北方言文化中心項目(2015FYZ002)
李 嵐(1979— )女,湖北武漢人,湖北第二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I247.5
A
2095-4476(2017)01-00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