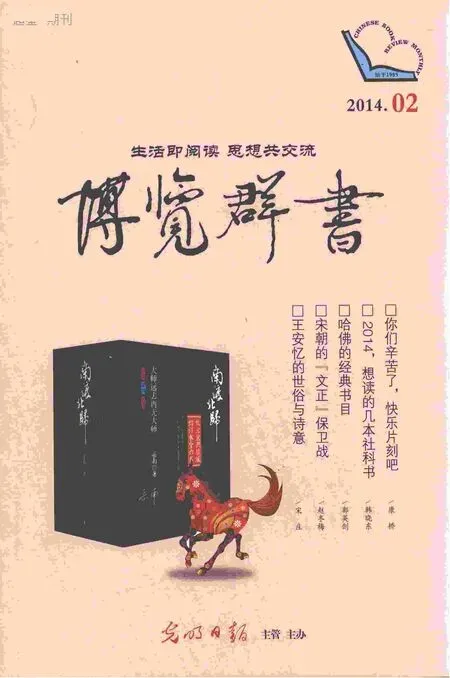他突然寫出《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
趙勇
一
熟悉李建軍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國當代文學方面頗有成就的思想者、研究者和批評者。近兩年來,他又開始了“重估俄蘇文學”的研究,文章聯翩而至,讓人應接不暇。然而,就在這種排山倒海般的寫作中,他卻突然拿出了這本《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集團2016年版),這讓我既感到驚奇,又心生羨慕。按照專業分工,他的這一研究已進入比較文學領域。從其后記中可以看出,他的這次寫作似是偶然,原本不在他的寫作計劃之內。而在半年左右的時間內,他從通讀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開始,到搜集資料形成寫作框架,再到最終寫成這39萬字的厚重之作,其比較的力度、思考的深度和寫作的速度都令人稱道,也值得我好好學習。作為一個學術中人,我深知即便有前期準備,但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這樣一部學術著作也殊為不易。這樣的寫作自然需要養氣運氣的功夫,但更需要一種極強的爆發力。這個事情若是擱到我的頭上,我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的。
仔細閱讀這本書,又會發現它是一部寫作嚴謹、分析深入、洞見迭出的著作,體現了李建軍一貫的治學理念和批評風格。一方面,它建立在嚴格的文本細讀的功夫之上,言必有據,決不信口開河。作者不僅是對兩位作家的文本讀得細,而且漢語學界莎學、湯學方面的前期研究成果和譯介成果也幾乎被他一網打盡。這就保證了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它又并非學院派那種為學問而學問式的高頭講章,而是更多體現了批評家的鋒芒、銳氣、關懷和進入問題的角度,以及與此相隨的出色的鑒賞力和判斷力。這本書既入乎其內,能帶領讀者走進兩位作家豐富無比的文本世界,又出乎其外,能對附著于作家作品的評論文本甄別鑒定,辨事理,明是非,從而進一步確認了兩位作家的人格價值和作品的文學價值。因此,若要讓我來為這本書定位,我覺得它是思想性與學術性相互支撐、鑒賞力與判斷力相互映照、才膽識力體現得充分完備的一部力作。我更愿意借用古人和今人的說法,用“氣盛言宜”和“紙背心情”來概括我的閱讀感受。但在進入這兩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從比較的方法說起。
從比較文學的角度看,把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看作“并世雙星”并對他們進行比較分析,是屬于所謂的“平行研究”。根據我對平行研究的粗淺理解,此種研究的重點在于揭示研究對象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而這種異同之所以能夠呈現出來,就是因為一旦進入比較的狀態,我們便可以左顧右盼。我把這種方法稱作“互看”。就是說如果僅僅研究湯顯祖或莎士比亞,這只是形成了一個維度,我們只能就人說人,就事論事。如果對這兩個人進行平行研究,那么就有了兩個維度,視野一下子也變得開闊起來。這時候,我們便可以從湯顯祖的視角看莎士比亞,或從莎士比亞的視角看湯顯祖。建立起這樣一個“互看”的模式之后,同和異就變得分明,原來沒發現的長處也昭然若揭,不是問題的問題也纖毫畢見。
當李建軍用“互看”的視角打量湯顯祖和莎士比亞時,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作家與時代的關系,也看到了作家的人格力量和人生哲學。前者可以說是同中之異,后者則是異中之同。李建軍指出,莎士比亞生活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這是一個有教養的君主所管理的社會,這樣,作家才能夠享有生活和寫作的基本自由,安全地寫作。而與之相比,湯顯祖則遠不像莎士比亞那么幸運,他生活在萬歷皇帝朱翊鈞統治的天下。朱翊鈞平庸而低能,懶惰而任性,他管理的社會,嚴刑峻法,駭人聽聞。在這種野蠻的時代,“即便那些勇敢的寫作者,也不得不選擇一種隱蔽的寫作方式,例如隱喻和象征的寫作方式,就此而言,湯顯祖象征化的‘夢境敘事,就是一種不自由環境下的美學選擇;而莎士比亞的全部創作所體現出來的極大的自由感和明朗感,則彰顯著寫作者與寫作環境之間積極而健康的關系。”(P17)
二
研究作家作品,我們總要面對作家與時代的關系,但通過比較而看到的莎士比亞所處時代之好和湯顯祖所處時代之惡,至少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提醒。而因為有了比較的視野,一個時代對作家的正負影響也就異常醒目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人不得不有悚然一驚之感。而當李建軍從時代回到人,“互看”兩位作家時,他則提煉出二人差不多相同的人生哲學:湯顯祖是“節制人欲及必要的虛無感”,莎士比亞則是“理性而低調的自然主義”。因為這種人生哲學,他們都擁有了一種健全而偉大的人格,這樣他們才創作出了偉大的作品。而由于湯顯祖所處的時代環境非常糟糕,他要堅守那種人生哲學并使人格不受扭曲,或許要比莎士比亞困難百倍。這樣,從同中之異始(第一章),在異中之同終(第七章),全書就形成了一個知人論世的完整比較框架。通過這一框架,兩位作家的人格與操守,作品中的人性光輝與美學價值,作家與時代的復雜關系就有了一個穩妥的著落。
但以上所言還不是我想談論的重點,我更想表達的一個意思是,除了“互看”之外,李建軍在這部著作中還形成了一個反觀自身的“回看”視角。這種“回看”又可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明著說,直指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存在的問題,痛快淋漓;其二是暗中講,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令人玩味。例如在談及哈茲里特對權力所采取的批判態度時,作者馬上轉到我們這里文學和影視中的“權力敘事”,對《英雄》《大秦帝國》和《雍正王朝》展開了批評。(P278)當他述及雨果筆下的一位經濟學家不喜歡莎士比亞是因為他沒寫出當代題材的作品時,李建軍援引的又是當代中國的例子,替雨果予以反駁:“中國當代文學中這種熱鬧一時的垃圾作品,汗牛充棟,亦云夥矣。《創業史》和《鐵木前傳》已經失去了它二分之一的價值,《金光大道》和《上海的早晨》已經失去了它五分之四的價值,而《高玉寶》和《虹南作戰史》則失去了幾乎全部價值。”(P311)
第二種情況的例子更多,茲引幾例:“因為朱翊鈞不懂得‘納稅人這個概念,所以,他也就不明白,每個勞動者吃的都是自己的飯,而不是官家和‘寡人的飯,更不可能毫無來由地砸他朱家的鍋,壞他朱家的事。”(P108)“個人崇拜不僅是一種病態的心理現象,反映著獨裁者嚴重的自卑心理和傲慢傾向,更是一種極其骯臟的政治現象,是對所有公民肆無忌憚的人格羞辱和厚顏無恥的精神掠奪。”(P229)“大權在握而又暴虐無度的最高統治者,幾乎沒有幾個不被嚴重的失眠癥所折磨,甚至難免患有消化不良和便秘等‘權力病。”(P440)這些隨機引發的議論遍布于這本書的字里行間,微言大義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很能引發人的一些聯想的。它們表面上看似乎是旁逸斜出,節外生枝,并不構成書中論述的主要內容,但我以為它們也恰恰是書中最為閃光的部分之一。
正是因為這種明里暗里的“回看”,才讓這本書具有了更豐富的維度。如前所述,當李建軍形成一種“互看”的視角時,書中只是有了兩個維度,這是中西對話;而一旦加入了不時的“回看”,便形成了一種三維結構,中西對話之外又有了古今互動。正是在這種中西古今的碰撞和思考中,李建軍讓他的這部論著出現了多種聲音:有學術層面的,有思想層面的;有面向文學的,有面向政治的;有褒揚文學之真善美的,有批判時代之假惡丑的。它們或此伏彼起,或多音齊鳴,形成了特殊的言說策略,撐大了言說的表意空間。
這種言說方式是頗有點陳平原所謂的“壓在紙背的心情”的(參見陳平原:《學院的“內”與“外”》,見《大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頁)。按照我的理解,所謂“紙背的心情”,其中之一應該是現實關懷。但問題是,這種現實關懷有的可以講,有的則無法談。因為道理很簡單,我們在許多方面似已進入到李建軍的描述之中,寫作失去了安全感。但既然還無法做到默不作聲,既然還必須寫作,我們便只好使用曲筆,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微言大義,隔山打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甚至以后我們是不是也得像錢鍾書那樣,使用夏中義所解釋的“暗思想”“隱理據”和“側闡釋”來進行言說(參見夏中義、葉祝弟:《思想默存于學術:作為思想家的錢鍾書——答〈探索與爭鳴〉記者問》,《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0期),也未可知。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我們才會在這本書里看到,攤在紙面上的是對四百年前的一對歷史人物的評說,而壓在紙背后的卻是作者的現實關懷。也許是歷史人物的境遇引發了作者的現實關懷,也許是現實關懷的沖動照亮了他筆下的歷史人物,總之,在這部書中,我讀出來的是一種特別的意味。而因為這種“紙背的心情”,這本書也就有了特別的分量。
三
除了這種紙背心情外,我還想用氣盛言宜談談我對這本書的另一感受。眾所周知,氣盛言宜這一說法來自韓愈的《答李翊書》:“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氣盛,一般解釋為作者道德修養達到了很高的境界。而汪曾祺則解釋為“作者情緒飽滿,思想充實”(汪曾祺:《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見《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我認為這兩種解釋都有道理。所謂言宜,是指語言要合適、準確。由此來看李建軍的這本著作,氣盛言宜的特點可以說體現得尤其充分。而這種特點之所以能夠體現出來,又來自他長期的文學批評實踐,以及在這種實踐中業已形成的那種穩健的文學觀和批評觀。例如,早在十多年前他就說過:“真正的文學是精神領域的羅賓漢,拒絕服從任何形式的奴役。它天生是個人道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總是站在被欺凌的弱小者和失去家園的流浪者一邊,堅持用理想的尺度衡量、評價殘缺的現實。它始終是尖銳的提問者,‘誰之罪‘怎么辦甚至‘明月幾時有‘江月待何人等等,都可能成為讓它困惑和焦慮的大問題。正是通過充滿激情的提問,它把文學變成偉大的啟示錄。”(李建軍:《我的文學觀》,見李建編:《十博士直擊中國文壇》,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頁)這大概是其文學觀的首次亮相。后來他又通過批評實踐,進一步完善了他的文學觀和批評觀。比如他說過:“在我的批評話語中,倫理尺度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李建軍:《文學因何而偉大》,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他還說過:“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具有態度性、選擇性和評價性的精神現象;不存在無態度的文學,只存在態度內斂或外顯、正常或病態的文學。”(李建軍:《文學的態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從他的這些表述中以及我對他著作文章的長期關注中,我覺得對現實主義(尤其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鐘情,對倫理道德尺度的看重,對作家人格力量的敬仰以及強調人與文的統一(文如其人),對所謂的純文學的鄙視,對作家病態心理和消極寫作的批判,等等,構成了李建軍文學觀和批評觀中的主要義項,而現實主義精神、理想主義情懷、為人生而藝術、對抗性寫作、俄蘇文學中的大氣與悲憫、批評家的責任倫理等,則構成了理解其文學觀和批評觀的關鍵詞。當這樣一種文學觀和批評觀變得成熟和穩定之后,他的著作文章中就充滿了一種正氣和浩然之氣,也有了一種斬釘截鐵的道德力量。《并世雙星》無疑是他這種堅守多年的文學觀和批評觀燭照之下的產物,自然也就有了一種清正剛健和雄辯滔滔之氣。
我以一個例子略加說明。此書中的第六章是“崇仰與焦慮:闡釋莎士比亞的態度”,內容涉及英、法、德、俄、美等國的作家與學者和中國的梁實秋對莎士比亞的接受,以及接受過程中敬仰、激賞、賓服、貶低、否定、誤讀和闡釋的焦慮。這一章的寫作難度不僅在于要梳理大量的史料,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李建軍所面對的評論對象大都是大作家或大批評家。如何對他們那些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評論文字予以辨析并進行恰如其分的評說,難度很大。如果某位作者缺少強大而堅定的價值立場,或許就很容易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中不知所措。但李建軍卻并非如此,在其文學觀和批評觀的支撐下,他肯定那些值得肯定的,批評那些滿嘴跑火車的,仿佛是四兩撥千斤,輕而易舉就把那些論述歸置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布魯姆、托爾斯泰和梁實秋的莎士比亞評析。
布魯姆的《西方正典》一書確立了26位作家的經典地位,而在這些經典作家中,莎士比亞則成為核心人物,是所有作家的試金石,“考察前人或后輩是否屬于經典作家都須以他為準”([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這種評價不可謂不高。但李建軍卻發現了這位唯美主義者的致命缺陷:他只注重莎士比亞作品的審美力量,卻把它們的社會意義和教育功能拒之門外。因此,李建軍認為布魯姆的“認知是混亂的,語言是橫恣的,判斷是任性的”(P386),他所發明的“憎恨學派”(School of Resenment)“是一個接近學術上的‘階級敵人的概念,也是一個極其粗暴的修辭行為和極其簡單化的命名行為”。(P387)這種批判讓我感到震驚,因為我在課堂上介紹《西方正典》多年,卻從未從這個角度對布魯姆做出過評析。李建軍的論述豐富了我的思考。
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批評眾所周知,通過仔細分析,李建軍認為托爾斯泰的批莎長文固然尖銳,“但那批評的態度,卻是極其嚴肅和認真的”。(P363)而托爾斯泰之所以對莎士比亞有嚴重的誤讀,關鍵在于其美學思想、文學理念和宗教觀念。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有著俄羅斯式的虔誠的宗教意識和嚴苛的道德要求”,是“封閉的規則的現實主義”,而莎士比亞奉行的卻是一種“開放的不規則的現實主義”,“有著大自然的氣質”(P366~367)。以這種單一的尺度衡量莎士比亞,自然就會造成嚴重的錯位和誤讀。這樣一種評析我覺得是清晰和準確的,也解決了我本人的一個困惑。
關于“梁實秋莎學研究”的一節內容,不僅是要釋放梁實秋研究莎士比亞的意義,而且更是對梁實秋文學觀的一個考察,對困擾我們多年的人性與階級性問題的全面清理。李建軍認為:“梁實秋自己的文學觀念和文學路向,就屬于莎士比亞的文學譜系,屬于遵循中庸之道的理性主義。這種基源于莎士比亞的文學精神和文學傳統,長期被誤解,被遮蔽,因而造成了很多人對它的誤解,留下極為消極的‘刻板印象。”(P394)于是他既正本清源,追溯梁實秋與莎士比亞文學精神的內在關聯,又去除陳見,直接面對當年的人性與階級性之爭,還原了魯迅所批判過的所謂的“乏走狗”的本來面貌。通過他的梳理、分析和辯護,一場歷史的糾紛便呈現出一種老吏斷獄似的清晰與明朗。
這就是我所謂的氣盛言宜。而通過這次對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文本細讀,通過這一番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解讀,我覺得李建軍不僅僅是完成了一次研究,而且也讓他“養”了一回“浩然之氣”。他的文學觀和批評觀將因此變得更加堅不可摧。與他讀的書和研究對象相比,我是既慚愧又羨慕。因為我研究大眾文化,面對的往往是二、三流的有問題的文本,而他面對的則是一流的經典作品。當他讀著營養豐富的莎士比亞和湯顯祖時,我看的卻可能是劉震云與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清湯寡水。所以我時常念叨:研究大眾文化,研究得我越來越沒文化了。這就是我慚愧和羨慕的原因。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