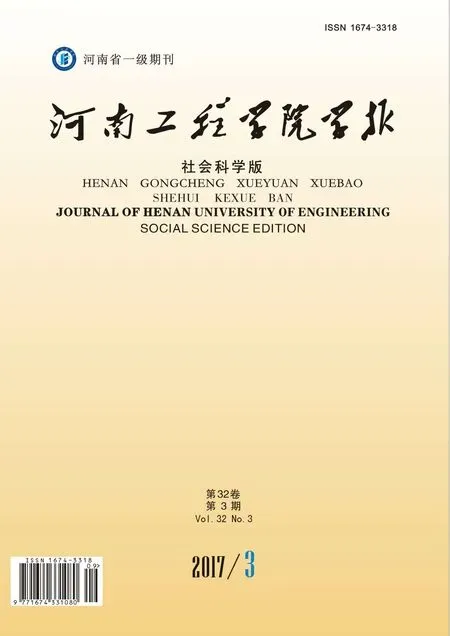姜夔對林逋梅花詞意義的繼承和引申
瞿 慧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姜夔對林逋梅花詞意義的繼承和引申
瞿 慧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南宋著名詞人姜夔尤愛描寫梅花,其梅花詞藝術成就很高且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評價。從姜夔的詞中不難看出,他深受北宋著名詩人林逋的影響,二人無論是在性格志趣、身世遭遇上,還是對梅花的愛好上都很相似。姜夔在詞中有頗多對林逋詩句的化用,并對其梅花意象進行了意義引申,將林逋寄托高潔志趣的“隱士梅”引申為寄托自己情感苦悶的“愛情梅”。
姜夔;“隱士梅”;“愛情梅”;意義引申
宋代愛梅者甚多,對梅花的贊賞和描摹可謂空前絕后,留下了許多流傳千古的名作。正如唐代人對牡丹的偏愛,宋代人則獨愛梅花,這與時代精神是分不開的。唐代文化恢宏奔放,仿佛只有“天上有香能蓋世,國中無色可為鄰”[1]201的牡丹才配得上這盛世風情;宋代文化風格沉靜內斂,“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2]134,清雅脫俗的梅花似乎更能代表宋代的文化品格。在描寫梅花的眾多宋代文人中,林逋和姜夔最為出眾。林逋的生活和生命都與梅花渾然一體、不可分割,其《山園小梅》為千古描梅之絕,林逋也因此成為梅花的代名詞;姜夔深受林逋影響,化用林逋詩句而作的《暗香》《疏影》使其成為與林逋并壽千古的詞人。故陳廷焯評論:“梅花題,無論詩詞,古今佳者絕少。蓋梅花高絕,最難落筆……老杜山意沖寒,坡公竹外一枝,逋仙雪后園林,放翁孤城小驛及白石《暗香》《疏影》二詞并壽千古”[3]195。
一、姜夔與林逋的孤山情結——“因覓孤山林處士”
孤山為林逋隱居之地。林逋一生酷愛梅花,隱居西湖孤山,“以梅為妻,以鶴為子”[4]1,以種梅養鶴為生活志趣,閑來作詩吟詠,仿佛世外仙人一般,在孤山一待就是一生,無論他的生活習性還是詩詞作品,都與孤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孤山于林逋并非只是醫治仕途失意的心靈棲居地,它還與林逋的生命和靈魂融為一體。在隱世文化興盛的中國古代,林逋可以說是一個另類。中國古代以儒家文化為主導,文人注重才學無非為了“學而優則仕”[5]171,謀求政治仕途從而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而文化才學是進入仕途的敲門磚,所以許多士人為求功名刻苦好學。只有在考試中屢次碰壁無緣政治抑或是入仕后官場失意的文人才選擇歸隱,以文學作為自己的心靈寄托。前者如姜夔,才學無所不通,然而命途多舛,屢試不中,除了歸隱并無他選;后者如魯迅贊為“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6]5的陶淵明,當文人的耿直性情同官場的趨炎附勢格格不入時,他選擇了歸隱,以《歸去來兮辭》明志,以菊花作為自己的人格象征。即便是自由灑脫的莊子,仍舊是在做了漆園吏后,對政治和現實的黑暗無能為力才拒絕仕途轉向自由無為的精神追求。而林逋則不同,雖通曉百家,才學超人,卻不趨榮利,他歸隱林壑,絕意仕途,既不是灰心,也不是失望,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愛,他自知自己的性格和志向,“然吾志之所適,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貴也,只覺青山綠水與我情相宜”[4]185。他作詩隨作隨毀,不求留名于后世,他喜愛“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漫隨天外云卷云舒”的詩意生活,在孤山上以梅鶴為伴,賞梅吟詩,如不是真正的愛梅成癡,又怎會有藝術水平高超的“孤山八梅”?
對于姜夔,一生中最重要的無非三個地方:揚州、合肥與孤山。“少小知名翰墨場”[7]175的揚州成名之作《揚州慢》,使年紀輕輕的姜夔一出手便不同凡響,受到當時名流贊賞,蕭德藻贊其有“黍離之悲”[8]1,同時奠定了他在詞壇的地位,揚州成為姜夔成名且風光無限的地方;“當初不合種相思”[8]153最后卻又不得不“兩處沉吟各自知”[8]153的合肥,是姜夔一生的眷戀和回憶;“因覓孤山林處士,來踏梅根殘雪”[8]180的杭州孤山,是姜夔的精神慰藉之地,這里有與自己志趣相投、經歷相似的知音林處士。讓姜夔名聲大震的梅花詞《暗香》《疏影》,其詞名正是化用林逋《山園小梅》中的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4]87,借用詞中最經典的意象做詞名,足見姜夔對林逋的贊賞和傾慕。同時姜夔詞中多次出現林逋和孤山,林逋有詠梅詩“孤山八首”,姜夔有《卜算子》梅花八詠,詩中隨處可見林逋對姜夔的影響及姜夔的孤山情結。在姜夔的《念奴嬌》(毀舍后作)中,作者表明來杭州踏雪尋梅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要尋覓孤山上的高士林逋的足跡。在《卜算子》中作者感嘆:“億別庾郎時,又過林逋處。萬古西湖寂寞春,惆悵誰能賦?”[8]193冬去春來,又經過林逋隱居之處,梅花將謝,面對西湖寂寞的春天,惆悵心情該如何宣泄呢?在《鬲梅溪令》中“漫向孤山山下覓盈盈,翠禽蹄一春”[7]77,梅花女神的傳說給孤山梅花更添幾分神秘色彩。在《法曲獻仙音》中作者寫道,“喚起淡妝人,問逋仙今在何許。象筆鸞箋,甚而今、不道秀句。怕平生幽恨,化作沙邊煙雨”[8]212。想起孤山上淡妝的梅花,卻不知善詠梅花的逋仙身在何處;春風詞筆,卻寫不出秀麗的詞句,真怕平生的幽恨酸楚都成了沙邊的煙雨。作者借與自己命格相似的林逋抒發自己羈旅漂泊的落寞心情,可見姜夔對孤山梅花的情結不僅是對林逋詠梅作品藝術的贊賞,更是對寥落身世和志趣愛好相似的知己的同病相憐。
二、高潔隱逸人格的比附——“眾芳搖落獨暄妍”
中國文人的花草之愛多有所寄托。陶淵明愛菊花,“身寄東籬心傲霜,不與群紫競春芳”[9]51的菊花最能體現陶淵明歸隱田園的隱逸情懷;李清照愛桂花,“暗淡輕黃性體柔,情香跡遠只香留”[10]38的桂花最符合李清照清疏恬淡的性格;林逋則是梅花的癡情守候人,“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4]87,傲雪凌霜的梅花最符合林逋的高士氣質。梅花是孤獨的,也是落寞的,在百花凋零、萬物沉寂的寒冷冬天迎風開放,梅與雪相伴,一塵不染的雪花更能襯托梅花的明艷動人,“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11]315,梅花冰清玉潔、高冷出塵,引得無數文人疼惜與愛憐。崔道融對“香中有別致,清極不知寒”的梅花亦是疼惜而又無可奈何,只能呼求“逆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12]3725。晁補之對梅花贊賞道:“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徹。”[13]268對于傲岸倔強的梅花,林逋選擇癡情守候,隱居孤山,終生不仕不娶,以梅為伴。梅花也正是林逋真實的人格寫照,林逋雖滿腹才學,卻不愿如其他文人一般對仕途趨之若鶩,以功名富貴為追求,他對塵世繁華并不貪戀,而獨獨向往清冷孤寂的西湖孤山。這正如梅花不愿如百花般在春天爭芳斗艷,而是恬淡清雅地開在寒冬,也不愿開在人人可踏足觀賞的繁華地帶,而是開在人跡罕至的江岸山壑。梅花高潔出塵的品質也正是林逋高雅逸趣和隱士人格的比附,在《梅花》詩中林逋就表達了喜愛梅花的原因:“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后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4]89世俗多愛紅艷之物,林逋獨愛清香淡雅的梅花,這是林逋陶寫隱逸寂寞的心情獨白。
姜夔一生中最愛的當屬荷花與梅花,在姜夔八十多首詞中,梅花詞接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對于姜夔酷愛此兩種花的原因,葉嘉瑩曾探析道:“姜白石所以獨借梅與荷以發抒而不借旁的花,則是由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其品最清;梅花凌冰雪而獨開,其格最動,與自己的性情最符。”[14]458姜夔一生羈旅漂泊,貧寒凄苦,少年喪父,寄居姐姐家中,青年才名遠揚,無奈科舉考試屢次落第,不得不結交權貴豪門及當世名流以求生計,而姜夔對梅花的愛、對林逋的贊賞則是無功利、無目的,非常純粹的。一個是畢生高臥山林的隱士,一個是漂泊終生的布衣,雖歸隱的初衷有主動與被動之分,但二人人格有許多相近之處。姜夔雖輾轉幕府淪為幕僚,但性格孤高狷介,不屑朋友為其買官入仕途,更不貪戀富貴,以梅花明志。姜夔在詞中多處提到林逋,以梅花書寫落寞情懷,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以跨代知音林逋的高潔情志來抒發自己羈旅落寞的身世感喟。劉熙載評論姜夔詞“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窮。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15]513。后人概括姜夔詞的風格為“清空騷雅”“幽韻冷香”[16]146,姜夔的詩歌風格也是同梅花清雅幽香而出塵的品格一致的。王國維評論“蘇辛,詞中之狂也;白石,猶不失為狷也”[17]29。縱然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猶不及梅花的桀驁不馴,姜夔就是這樣一位清高自負的文人。科舉與仕途是世俗對文人價值的衡量尺度,姜夔縱使歸隱漂泊也不屑于買官和別人施舍的財富,又有什么比梅花更能象征姜夔的心性品質呢?姜夔就是南宋詞壇中一枝清冷傲岸的雪中紅梅。
三、姜夔對林逋“隱士梅”意義的引申——“見梅枝,忽相思”
筆者認為,姜夔喜愛梅花和推崇林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梅花的清新雅潔、高潔脫俗的品質與自身對文人品質的追求相一致;其次,對林逋閑散逍遙、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對清冷高潔的梅花的志趣愛好,以及孤高狷介、不慕名利的人格和個性的認同與接受;再次,梅花于姜夔的特殊意義,即對愛情相思的寄托。姜夔的一生可謂心酸悲戚,少小家庭變故,而后政治仕途失意,年輕時的摯愛也成為一生的遺憾,姜夔的情感寄托同梅花意象融為一體構成了他悲涼酸楚、令人惆悵百結的情詞。夏承燾先生考證,姜夔年輕時在合肥遇到人生的摯愛——赤闌橋邊才華橫溢、容貌動人的歌女,而由于種種原因,二人最終只能勞燕分飛,留給姜夔一生的懷念。夏先生認為:“姜夔用情之專之深,在兩宋文人中只有陸游可與之相比,這也使得姜夔的詞具有極為感人的品質。”[18]3從姜夔詞的回憶和描述可知,這段感情與梅花是分不開的,如《暗香》中“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8]96,《江梅引》中“人間離別易多時,見梅枝,忽相思”[8]137,《踏莎行》中“春初早被相思染”[7]21等。人生最痛苦的莫過于在痛苦的時候回憶幸福的時刻:想當年年紀輕輕便寫出《揚州慢》這樣的杰作而名動詞壇;早春梅花開放的時節,意氣風發,才情縱橫的年紀游于江淮之地,一位紅裙粉黛的美貌女子正淺吟低唱著“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7]1“燕燕輕盈,鶯鶯嬌軟”[7]21的女子粉黛紅裙如同雪中盛開的紅梅一樣,讓姜夔為之心動,而除卻才情一無所有的姜夔又如何許女子一個未來呢?古代文人唯有以科舉入仕來改變階級地位,自恃才高的姜夔卻與功名無緣,屢次落第,最終不得不結交富貴名流而謀生。女子是癡情的,在分別時“擬將裙帶系郎船”[7]36,即便“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19]104,在漫長的離別中癡情等待姜夔十多年,姜夔終究是“系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20]198,辜負了女子。姜夔受到當時著名詩人蕭德藻的賞識,蕭德藻念其凄苦無人照料,將自己侄女許配給姜夔,而姜夔對于對自己有知遇之恩而又依傍的人的盛情又如何推卻呢?只能辜負意中人,把一生的痛苦和回憶留給自己。當初給自己無限美好和期待的梅花,此后再見只能勾起傷心的回憶,如張炎認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8]98的《暗香》《疏影》,正是借梅花懷念伊人的佳作。在《暗香》中作者寫道:昔日皎潔的月色曾經映照著我,想起與美麗的佳人一起梅邊吹笛、不顧清寒攀摘梅花的美好時刻,而今我漸漸老去,竹外梅花開得正好,可嘆路程遙遠,無法折枝梅花寄托我的相思之情,面對著雪中綻放的紅梅,往日美好的回憶涌上心頭,忍不住潸然淚下。曾經攜手的地方,盛開的紅梅壓滿了枝頭,西湖一片澄碧,而梅花被風無情吹落,這樣的情景何時能夠再見呢?何時能夠與佳人再重逢呢?詞中作者正是借梅花抒發對佳人的思念。《疏影》中作者同樣運用幾則典故,借眼前梅花抒發對女性悲戚命運的感嘆,同時也抒發了作者對遠方佳人的思念及愛而不得的苦悶。在《江梅引》中作者更直接表達了這種相思悲傷的情懷,“見梅枝,忽相思”[8]137,羈旅漂泊,與戀人分隔兩地,辛酸悲戚只能訴于曾經見證自己愛情的梅花。從“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7]21的離別哀愁,到“春為綠,鬢先絲,人間別久不成悲。誰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沉吟各自知”[8]153的絕望,即便到老這段情事也是姜夔揮之不去的憂傷,“花滿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來悲”[7]81。這段悲劇的愛情留給姜夔的是一生的留戀和遺憾,對這份愛情從期待到無奈再到絕望,這種愛情的失意、人生的失意仿佛也只有梅花可與訴說,在姜夔的詞中梅花是人,是佳人的象征,它寄托了作者的離愁別恨,對于姜夔來說梅花是寄托愛情的,是他獨一無二的“愛情梅”。
四、結語
梅花將林逋與姜夔這兩個本來毫無關系且跨時代的人密切聯結了起來,兩人都摯愛梅花,在生平遭際和心性品位方面兩人是相似的。姜夔對林逋的推崇和贊賞飽含著同病相憐、相知相惜的知音情調,以及對林逋追求自由、不慕名利的高潔隱逸人格的贊賞。兩人在作品中除卻對梅花品貌的傳神刻畫描寫之外,都有以梅花寄托自己冷僻孤傲、清雅高潔人格的意義,即將梅花作為自身高雅出塵人格比附的“隱士梅”。與林逋不同的是,除卻寄托隱逸情志外,梅花還象征著姜夔高潔而純美的戀情。在姜夔為仕途謀生而在外羈旅漂泊的時候,借梅花以懷念佳人,傳達了自己思情纏綿、眷戀哀傷的情思。而后與佳人失散不得見時,詞中多清冷孤寂的寒梅意象,從而寄托對戀人的懷念,傳達人去樓空的悲痛之情,所以姜夔對林逋梅花詞意義的引申主要在于愛情方面,將林逋寄托隱逸情志的“隱士梅”引申為寄托自己相思情愁的“愛情梅”。
[1]張景星,姚培謙,王永祺.元詩別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
[2]王兆鵬,黃崇浩.王安石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10.[3]陳廷焯.白雨齋詞話[M].濟南:齊魯出版社,1983.
[4]林逋.林和靖集[M].沈幼征,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5]臧力農.論語新注[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
[6]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7]姜夔.姜夔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劉乃昌.姜夔詞新釋輯評[M].北京:中國書店,2001.
[9]方勝.滿城盡帶黃金甲——談黃巢的兩首詠菊詩[J].名作欣賞,2007(21):50-52.
[10]李清照.李清照詩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1]胡國強.毛澤東詩詞疏證[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12]王啟興.校編全唐詩[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13]廖承良,陳書良.蘇門四學士[M].長沙:岳麓書社,1998.
[14]繆鋮,葉嘉瑩.靈溪詞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劉熙載.藝概注稿:下[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16]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7]王國維.人間詞話[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8]孟斜陽.詞解姜夔[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2.
[19]晏幾道.晏幾道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0]過常寶.柳永詞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Jiang Kui′s Inheriting and Extending the Meaning of Lin Bu′s Plum Blossom Ci
QU Hu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Jiang Kui, the famous poet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loved describing plum blossom especially, whose plum flower ci has achieved a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 and was appraised highly by later generations. From his works, it can be found easily that he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ous poet of Lin Bu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y had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personality and hobby and life experience. Jiang Kui paraphrased many poets of Lin Bu in his works and extended the meaning and the image of Lin Bu′ plum flower. Jiang Kui extended "the hermit plum blossom"(expressing the elegant interest of Lin Bu) to "the affection plum blossom"(expressing the anguish of Jiang Kui).
Jiang Kui;Lin Bu;"hermit plum blossom";"affection plum blossom";the extension of meaning
2016-12-09
瞿 慧(1993- ),女,陜西安康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2015級文藝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論。
I207.3
A
1674-3318(2017)03-006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