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藝術(shù)設(shè)計(jì)作品的民族風(fēng)格及其形成原因
彭茹娜
(湖北大學(xué) 藝術(shù)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62)
張仃藝術(shù)設(shè)計(jì)作品的民族風(fēng)格及其形成原因
彭茹娜
(湖北大學(xué) 藝術(shù)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62)
張仃是一位民族風(fēng)格設(shè)計(jì)大師。他設(shè)計(jì)的作品不僅實(shí)現(xiàn)了功能與審美,更賦予設(shè)計(jì)受眾濃郁的民族藝術(shù)體驗(yàn)。張仃藝術(shù)設(shè)計(jì)作品的民族風(fēng)格特色主要從主題與形式中呈現(xiàn)的民族歷史印記、民族書畫藝術(shù)手法的跨界運(yùn)用以及中國(guó)民間美術(shù)在設(shè)計(jì)中的善用與創(chuàng)新三個(gè)方面體現(xiàn)出來(lái);對(duì)民族和國(guó)家觀念的自覺(jué)觀照、深厚的文藝修養(yǎng)和廣泛的藝術(shù)興趣、扎實(shí)的筆墨功底和志趣相投的良師益友、與生俱來(lái)的藝術(shù)天賦和對(duì)生活的深入觀察則是其民族風(fēng)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張仃;藝術(shù)設(shè)計(jì);民族風(fēng)格
張仃先生是中國(guó)藝術(shù)設(shè)計(jì)事業(yè)的重要奠基人,也是一位民族風(fēng)格設(shè)計(jì)大師。張仃的設(shè)計(jì)作品不僅實(shí)現(xiàn)了功能與審美,更賦予設(shè)計(jì)受眾濃郁的民族藝術(shù)體驗(yàn),探究其作品民族風(fēng)格特色和特色形成的原因,對(duì)于當(dāng)前藝術(shù)設(shè)計(jì)的民族風(fēng)格研究不無(wú)裨益。
一、張仃藝術(shù)設(shè)計(jì)作品的民族風(fēng)格特色
張仃先生藝術(shù)設(shè)計(jì)作品的民族風(fēng)格特色從主題與形式中呈現(xiàn)的民族歷史印記,民族書畫藝術(shù)手法的跨界運(yùn)用,以及中國(guó)民間美術(shù)在設(shè)計(jì)中的善用與創(chuàng)新三個(gè)方面體現(xiàn)出來(lái)。
(一)主題與形式中呈現(xiàn)的民族歷史印記 張仃將自己的藝術(shù)追求融入到歷史的宏大進(jìn)程和民族的廣闊圖景中,他不封閉于專業(yè)技術(shù)的探索,而是時(shí)刻響應(yīng)時(shí)代的呼聲,將藝術(shù)設(shè)計(jì)與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密切聯(lián)系起來(lái)。因此,其設(shè)計(jì)作品的主題與形式均是對(duì)國(guó)家意志和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呼應(yīng),呈現(xiàn)出鮮明的民族歷史印記,這是其民族風(fēng)格設(shè)計(jì)的突出標(biāo)志。
張仃設(shè)計(jì)作品的主題凸顯了對(duì)歷史任務(wù)、時(shí)代精神、人民呼聲和主流價(jià)值觀的真切關(guān)懷和深度融入。以20世紀(jì)30年代張仃創(chuàng)作的宣傳漫畫為例,從現(xiàn)有資料來(lái)看,1936年到1938年是張仃發(fā)表漫畫的巔峰時(shí)期,他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漫畫作品均發(fā)表在這段時(shí)期。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前,他的漫畫作品以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為題材,主要是用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諷刺手法針砭社會(huì)的痼疾,揭露勞動(dòng)人民的苦難和剝削階級(jí)的冷酷,如《買賣完成了》尖銳地表現(xiàn)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對(duì)立關(guān)系。他在這幅作品中,用有著漆黑煙囪的冰冷的廠房、巨大的磚制煙囪、鋼鐵起重機(jī)、橫跨天空的電線和交錯(cuò)的貨運(yùn)鐵軌來(lái)表明“買賣”發(fā)生的場(chǎng)所,用荷槍實(shí)彈的警察正在帶走一群被綁縛的工人,留下一具尸體躺在地面上來(lái)控訴買賣完成后工人的遭遇——生產(chǎn)完成、貨物賣出后,工人的任何反抗都會(huì)遭到資本家和警察的無(wú)情鎮(zhèn)壓。該漫畫作為“全國(guó)漫畫名作選”中的一幅刊登于《上海漫畫》1936年第3期,反映他積極響應(yīng)魯迅先生在《新青年》上撰文提出的用諷刺畫“針砭社會(huì)的痼疾”,“指出確當(dāng)?shù)姆较颍龑?dǎo)社會(huì)”[1]的號(hào)召,立志要做一位關(guān)心人類命運(yùn)的新青年,試圖用藝術(shù)的方式來(lái)教育大眾、影響大眾,使中國(guó)擺脫封建主義和帝國(guó)主義壓迫的強(qiáng)烈愿望。盧溝橋事變后,中日戰(zhàn)爭(zhēng)全面爆發(fā),漫畫以通俗易懂的形式,簡(jiǎn)便的工具媒介和鼓動(dòng)性的內(nèi)容成為艱苦戰(zhàn)爭(zhēng)環(huán)境中最有效的宣傳工具,張仃也因漫畫而成為抗日救亡藝術(shù)家的中堅(jiān)力量,并達(dá)到自己的漫畫創(chuàng)作巔峰期。張仃此時(shí)期的漫畫作品并不是逗笑與幽默,而是激昂的吶喊與有力的抨擊,發(fā)揮著匕首與投槍的作用,歷史地見(jiàn)證了當(dāng)時(shí)震人心魄的民族危機(jī)。《日寇空襲平民區(qū)域的賜予》是張仃發(fā)表于《救亡漫畫》1937年10月第4期的一幅作品。作品比喻、象征、對(duì)比等手法,用諷刺的形式切實(shí)地記錄、揭露了日本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歷史事實(shí):前景是一位悲痛的農(nóng)民雙手抱著自己死去的孩子,黝黑的皮膚,粗厚樸實(shí)的著裝和臥在地上的耕牛表明了人物的農(nóng)民身份;遠(yuǎn)景是煙囪廠房的殘?jiān)珨啾冢瑹焽琛⑵鹬貦C(jī)、堡壘式的建筑象征資本家的廠房;一架從空中掠過(guò)的日本飛機(jī)揭示了日寇空襲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作品的用意非常明顯,即在日寇面前,資本家和平民面對(duì)著同樣的空襲與炮火,在戰(zhàn)爭(zhēng)面前,二者之間的階級(jí)矛盾不再是主要的對(duì)立矛盾。他以這種方式來(lái)喚起民眾同仇敵愾的抗日救亡行動(dòng),這正是當(dāng)時(shí)每一位愛(ài)國(guó)藝術(shù)家的歷史使命,而這種歷史使命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則賦予作品民族歷史的風(fēng)貌。
張仃設(shè)計(jì)作品的視覺(jué)形態(tài)與審美趣味均及時(shí)地呼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的主流形式。如他在1947年設(shè)計(jì)的一批宣傳畫就呈現(xiàn)出鮮明的延安時(shí)期藝術(shù)特征。首先,從表現(xiàn)手法上看,這些作品多采用讓人一目了然的寫實(shí)風(fēng)格,用勾線平涂的手法,和老百姓喜聞樂(lè)見(jiàn)的通俗化的、帶有喜慶色彩的視覺(jué)符號(hào)來(lái)歌頌解放區(qū)的新生活、新景觀。如《人民翻身興家立業(yè)》以象征豐收喜慶的金黃色調(diào)為主,用肩扛滿滿一大袋糧食的農(nóng)民、裝滿金黃稻谷的谷倉(cāng)、掛滿屋檐的玉米棒、墻頭一大串火紅的辣椒、屋頂上一群歡樂(lè)的小鳥(niǎo)、院子里一群憨態(tài)可掬的花豬、一大群圍著主人滿地跑的家禽等元素,來(lái)營(yíng)造人民翻身興家立業(yè)的喜悅。又如張仃1950年發(fā)表在《美術(shù)研究》第1期上的一幅宣傳畫《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jìn)》,盡管與他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宣傳漫畫具有同樣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沖擊力,但風(fēng)格卻全然不同。他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作品多采用夸張諷刺的手法,人物形象粗獷簡(jiǎn)潔,不求色彩而講究黑白對(duì)比,畫面中文字的字體與版式通常比較自由隨意。而這幅作品采用的卻是寫實(shí)的表現(xiàn)手表,人物形象結(jié)實(shí)有力,畫面色彩鮮明強(qiáng)烈,粗而有力的仿宋體美術(shù)字“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jìn)”工工整整地排列在畫幅的下端。在共和國(guó)成立初期,著名文學(xué)家郭沫若先生1949年11月在《人民日?qǐng)?bào)》上發(fā)表了著名詩(shī)歌《新華頌》:“人民中國(guó),屹立亞?wèn)|。光芒萬(wàn)道,輻射寰空。艱難締造慶成功,五星紅旗遍地紅。”[2]以史詩(shī)般的詩(shī)詞歌頌了共和國(guó)的誕生,工農(nóng)群眾翻身的喜悅,和在巨大勝利鼓舞下的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顯然,張仃在這幅宣傳畫里描繪的毛主席巨像、高高飄揚(yáng)的黨旗、熱情激昂的解放軍都讓人不由自主地聯(lián)想到郭先生詩(shī)歌里的壯麗圖景,感受到共和國(guó)成立之際舉國(guó)歡騰的氣氛,說(shuō)明他能夠敏感地察覺(jué)主流的意識(shí)形態(tài)與藝術(shù)形式,并在自己的設(shè)計(jì)創(chuàng)作中及時(shí)地呼應(yīng)這種形態(tài)與形式。此外,張仃同一時(shí)期設(shè)計(jì)完成的政協(xié)會(huì)議會(huì)徽和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第一屆全體會(huì)議紀(jì)念郵票在表現(xiàn)形式和風(fēng)格特色上也都呈現(xiàn)出非常類似的、與主流藝術(shù)形式相吻合的審美取向。對(duì)國(guó)家意志和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呼應(yīng)讓張仃的設(shè)計(jì)作品在每個(gè)歷史時(shí)期都產(chǎn)生較為廣泛的歷史影響,甚至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并由此賦予作品民族的風(fēng)格與歷史的內(nèi)涵。
(二)民族書畫藝術(shù)手法的跨界運(yùn)用 張仃曾被吳冠中先生譽(yù)為“中國(guó)山水畫發(fā)展史中的里程碑”。[3]他精于繪畫,尤其擅長(zhǎng)中國(guó)民族書畫,晚年在焦墨山水和書法藝術(shù)上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shuō),張仃在繪畫領(lǐng)域的成就絲毫不遜色于設(shè)計(jì)領(lǐng)域的成就。
作為一位精通民族書畫藝術(shù)的設(shè)計(jì)大師,張仃的設(shè)計(jì)風(fēng)格明顯有別于術(shù)業(yè)有專攻的設(shè)計(jì)師。其設(shè)計(jì)作品最獨(dú)特的地方在于民族書畫藝術(shù)精神在設(shè)計(jì)中的自然流露,這種自然流露首先從書畫用筆在設(shè)計(jì)中的“跨界”運(yùn)用——作品中“線”的形態(tài)充分體現(xiàn)出來(lái)。中國(guó)民族書畫以線條美為上,用線條來(lái)傳達(dá)民族藝術(shù)的精神,將線條視為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對(duì)象化和民族特有的生命形式。與設(shè)計(jì)作品中常見(jiàn)的扁平工整無(wú)變化的、等粗細(xì)的輪廓線截然不同,張仃的設(shè)計(jì)非常注重具有民族書畫藝術(shù)筆力、骨氣與神韻的“線條”的運(yùn)用,其作品中的線條不是用扁平的排筆或生硬的繪圖筆勾勒出的工整勻稱、一般粗細(xì),無(wú)輕重變化的靜態(tài)輪廓線,而是講究骨法用筆、輕重緩急、虛實(shí)變化的,有意趣、筆力的書法線、國(guó)畫線。他作品中的線盡管形式質(zhì)樸單純,其精神內(nèi)蘊(yùn)卻無(wú)限豐富,力求與民族藝術(shù)的精神和民族審美心理的律動(dòng)取得和諧一致。如在他為《漫畫》創(chuàng)刊號(hào)設(shè)計(jì)的封面中,主體人物形象的描繪就是一幅地道的中國(guó)工筆畫,面部五官的勾勒,衣紋的結(jié)構(gòu),均講究圓潤(rùn)渾厚、結(jié)實(shí)而有力感的中鋒運(yùn)筆。此外,他善于用不同的線條來(lái)表現(xiàn)對(duì)象的質(zhì)感,如用類似于顧愷之的高古游絲描來(lái)表現(xiàn)隨風(fēng)飄揚(yáng)的五星紅旗,用堅(jiān)挺有力的直線來(lái)表現(xiàn)直指敵人的纓槍。他為《裝飾》創(chuàng)刊號(hào)設(shè)計(jì)的封面,運(yùn)用具有民族書畫視覺(jué)邏輯的線條,引起觀眾深沉雋永的審美體驗(yàn),以線條的長(zhǎng)短、粗細(xì)、曲直、方圓、濃淡、枯濕、肥瘦、剛?cè)帷⑦M(jìn)退變化,激發(fā)“運(yùn)動(dòng)”的聯(lián)想,暗示高舉“衣食住行”四面彩旗之龍舟的氣勢(shì)與動(dòng)向,由此活躍生命的意識(shí),深入細(xì)微地表現(xiàn)自己的意趣與精神,可見(jiàn),張仃設(shè)計(jì)作品中的線富有民族書畫的韻味,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作為單一設(shè)計(jì)構(gòu)成單位的運(yùn)用。
從中國(guó)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獲得的位置經(jīng)營(yíng)審美體驗(yàn)也對(duì)張仃的設(shè)計(jì)美學(xué)思想和民族風(fēng)格的形成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1952年6月,在北京中山公園參觀了“波蘭招貼畫展覽會(huì)”后,張仃撰寫了一篇名為《談波蘭宣傳畫》的觀后感,文中寫道:“若干優(yōu)秀的波蘭宣傳畫,畫面上雖然很簡(jiǎn)單,卻都是經(jīng)過(guò)辛苦的構(gòu)思的,創(chuàng)造性很強(qiáng)。我國(guó)古代畫家所謂:‘以少少許勝多多許’,‘惜金如墨’等,就是要達(dá)到以最精煉的形式表現(xiàn)最豐富最深刻的內(nèi)容。看波蘭宣傳畫使人想起古人這些話語(yǔ)。”[4]正是由于同時(shí)兼修傳統(tǒng)書畫,張仃才能夠?qū)⒃O(shè)計(jì)的構(gòu)圖與中國(guó)古代繪畫美學(xué)精神建立起關(guān)聯(lián),形成不同與其他設(shè)計(jì)師的民族風(fēng)格特色。張仃為《裝飾》雜志創(chuàng)刊號(hào)設(shè)計(jì)的封面也充分反映了傳統(tǒng)中國(guó)畫美學(xué)理念對(duì)設(shè)計(jì)風(fēng)格的影響。首先,用寥寥幾筆抽取了畫面主體龍舟與高高屹立、隨風(fēng)飄揚(yáng)的4面彩旗的主要精神特征,彩旗上的衣食住行4個(gè)符號(hào)簡(jiǎn)潔明了地承載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其次,畫面虛實(shí)相生,上端寬扁排筆蘸上朱紅拖過(guò)的印跡,恰似一抹瑰麗的云霞,下端的普蘭似波濤,中間大面積的留白讓人仿佛見(jiàn)到一片廣天闊水、煙云浩渺的汪洋,托載著龍舟乘風(fēng)破浪地平穩(wěn)前行。畫面中的虛無(wú)與空白,以虛帶實(shí)、虛中有實(shí)地營(yíng)造出悠遠(yuǎn)的意境,這正是張仃體悟到的“以少少許勝多多許”,“惜金如墨”在設(shè)計(jì)中的巧妙運(yùn)用。張仃在設(shè)計(jì)中流露出的民族書畫藝術(shù)精神,是他對(duì)民族藝術(shù)自尊與自信的突出表現(xiàn),也讓其作品從內(nèi)在的韻味到外在的視覺(jué)不由自主地向民族文化的“視覺(jué)語(yǔ)言系統(tǒng)”靠攏。作為中國(guó)民族藝術(shù)精粹的書法與繪畫藝術(shù),積淀著明顯的民族、社會(huì)內(nèi)容,并在視覺(jué)語(yǔ)言與美學(xué)趣味上體現(xiàn)了民族的審美心理與情感,帶有民族精神的印記,呈現(xiàn)出鮮明的地緣文化特征,民族書畫藝術(shù)手法在設(shè)計(jì)中的跨界運(yùn)用,賦予其作品敏銳的情思、蓬勃的生氣與獨(dú)樹(shù)一幟的民族風(fēng)格。
(三)中國(guó)民間美術(shù)在設(shè)計(jì)中的善用與創(chuàng)新 張仃出生于民間美術(shù)資源豐富的陜北地區(qū),早在幼年時(shí)期,家鄉(xiāng)的民間美術(shù)就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種子,培植了深厚的情感,不僅促使他成為中國(guó)民間美術(shù)的“守望者”,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設(shè)計(jì)風(fēng)格。
首先,張仃站在現(xiàn)代設(shè)計(jì)的立場(chǎng)上,從中國(guó)民間美術(shù)中發(fā)掘原始的力量與稚拙之美。對(duì)中國(guó)民間美術(shù)的善用讓他的作品自然真誠(chéng)、質(zhì)樸清新,體現(xiàn)了民族的喜聞樂(lè)見(jiàn)和廣大人民的審美情趣,絕緣與浮華的視覺(jué)語(yǔ)言,形成簡(jiǎn)約、樸素、含蓄、靈氣的民族風(fēng)格特色。中國(guó)民間美術(shù)源于勞動(dòng)人民的生產(chǎn)生活與民風(fēng)民俗,無(wú)過(guò)多的雕琢修飾,保持稚拙、簡(jiǎn)括、純真的原始性魅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具有濃厚的鄉(xiāng)土氣息和鮮明的中國(guó)特色,這種魅力與特色在張仃的設(shè)計(jì)中常常不經(jīng)意地流露出來(lái)。如他為全國(guó)漫畫展覽會(huì)設(shè)計(jì)的宣傳畫,其立意源自“公雞戰(zhàn)五毒”的民俗故事,以“公雞”、“五毒”、“鋼筆”、“投槍”這些象征性的視覺(jué)符號(hào),寓意漫畫針砭時(shí)政的戰(zhàn)斗力量與社會(huì)功用。除去黑色的底色和留出的空白,整個(gè)畫面只用到了紅與綠這對(duì)互補(bǔ)色。畫面主體部分是一只昂首挺胸、闊步向前的大公雞,其造型采用民間剪紙的夸張變形手法,輔以粗獷、稚拙的鋸齒紋、月牙紋、柳葉紋來(lái)表現(xiàn)結(jié)構(gòu)、裝飾畫面。公雞背上,一只有力的臂膊高高舉起一桿猶如投槍匕首般鋒利的繪圖鋼筆,讓前方的“五毒”,毒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驚慌失措、倉(cāng)皇逃竄。這件作品運(yùn)用了民間美術(shù)自由無(wú)羈地表達(dá)內(nèi)心審美理想,得意忘象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用夸張、概括、抽象與組合(如手臂與公雞組合而成的復(fù)合造型)等造型手法,賦予作品喜聞樂(lè)見(jiàn)的民間視覺(jué)形態(tài)和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張力,讓作品散發(fā)出醇厚的鄉(xiāng)土氣息與具有濃郁地域色彩的原始性魅力。
其次,從張仃的設(shè)計(jì)作品可以看出,他并非簡(jiǎn)單地求助于民間美術(shù)元素來(lái)為設(shè)計(jì)貼民族化的標(biāo)簽,而是尊重并挖掘自己對(duì)民間美術(shù)的感受,再將這些元素創(chuàng)造性地重構(gòu),其作品強(qiáng)烈的民族辨識(shí)度不是浮于形式的刻意而為之,而是由內(nèi)及外的、本質(zhì)的自然溢出,體現(xiàn)出他作為一位現(xiàn)代人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觀照。張仃在20世紀(jì)50年代主持的一系列世界大型博覽會(huì)中國(guó)館設(shè)計(jì),以強(qiáng)烈的中國(guó)風(fēng)深深吸引了來(lái)自世界各地的觀眾。以1954年的萊比錫國(guó)際博覽會(huì)為例,他為展館外廊設(shè)計(jì)的一排燈籠,充分展現(xiàn)了他對(duì)民間美術(shù)的善用與創(chuàng)新。在建筑空間外廊的每一對(duì)柱廊之間懸掛燈籠是中國(guó)民間慶祝活動(dòng)中的常見(jiàn)形式,張仃將這種形式借鑒到國(guó)際博覽會(huì)的中國(guó)館設(shè)計(jì)中,營(yíng)造共和國(guó)誕生的喜悅之情,以及以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之蓬勃朝氣,正是基于對(duì)中國(guó)民間生活美學(xué)的理解。他取民間大紅燈籠的造型,使之成為有意味的民族形式,卻創(chuàng)造性地用白色的燈籠壁紙取代原本的紅色,只保留燈籠下粗壯的大紅色流蘇穗,再用民間剪紙、繪畫等藝術(shù)手法來(lái)裝飾白色的燈籠,這樣一方面讓燈籠的視覺(jué)效果更加豐富,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出他從文化上和美學(xué)上對(duì)整個(gè)空間設(shè)計(jì)的周密考量。張仃1959年設(shè)計(jì)的民間剪紙紀(jì)念郵票是與此類似的另一件代表性作品。他從自己收藏的陜北剪紙作品中直接選取公雞、壽桃、駱駝、教子4幅作品作為設(shè)計(jì)原型,(顯然,這是他認(rèn)為最能夠代表民間剪紙藝術(shù)成就的4件作品),但卻創(chuàng)造性地用富有現(xiàn)代感的黑色取代了剪紙作品原本的紅色,又用含蓄、樸素的民間美術(shù)色彩——朱砂、翠綠、青蓮、鈷藍(lán)作為烘托剪紙的背景,設(shè)計(jì)出來(lái)的作品既有對(duì)民族文化的追溯,又有對(duì)當(dāng)代現(xiàn)實(shí)的思考。剪紙等以人民為創(chuàng)作根基的民間美術(shù),其視覺(jué)形態(tài)類似于“俗語(yǔ)”與“土語(yǔ)”,有深厚的歷史積淀、頑強(qiáng)的生命力、生動(dòng)強(qiáng)烈的地域文化特質(zhì)和特定的視覺(jué)確認(rèn)族群范疇。張仃在設(shè)計(jì)中對(duì)剪紙等民間美術(shù)的善用與創(chuàng)造,藝術(shù)地搭建了設(shè)計(jì)與百姓之間溝通的橋梁,有效地引起觀眾的聯(lián)想與共鳴,并賦予作品濃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文化生活氣息。
二、張仃藝術(shù)設(shè)計(jì)作品民族風(fēng)格形成的原因
張仃先生是中國(guó)藝術(shù)設(shè)計(jì)民族風(fēng)格探索的先行者。他在藝術(shù)設(shè)計(jì)領(lǐng)域取得的成就有力地表明——唯有具備民族特色的設(shè)計(jì),才是最為國(guó)際化的設(shè)計(jì)。在探討其設(shè)計(jì)作品的民族風(fēng)格特色之后,筆者認(rèn)為,以下四方面因素是張仃先生藝術(shù)設(shè)計(jì)作品民族風(fēng)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對(duì)民族和國(guó)家觀念的自覺(jué)觀照 對(duì)民族和國(guó)家觀念的自覺(jué)觀照讓張仃的作品呈現(xiàn)出歷史的風(fēng)貌和濃郁的民族風(fēng)格特征。作為一位設(shè)計(jì)師,張仃并不將自己孤立地作為一位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而存在,而是將個(gè)人的專業(yè)特長(zhǎng)自覺(jué)地向民族和國(guó)家觀念靠攏。20世紀(jì)30年代“九一八”事變后,在北平美術(shù)專科學(xué)校國(guó)畫系主修中國(guó)畫的張仃,時(shí)常被魯迅“不要作空頭美術(shù)家”的遺囑所震動(dòng),“總想找個(gè)旁的出路”。[5]“走出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是當(dāng)時(shí)文藝在國(guó)家民族危難關(guān)頭必然的抉擇,同時(shí),漫畫作為簡(jiǎn)便的大眾化讀物,以及與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密切聯(lián)系而成為抗敵救亡運(yùn)動(dòng)的最有力武器。于是,在高漲的民族救亡旗幟的感召下,他放下中國(guó)畫的研習(xí),轉(zhuǎn)而開(kāi)始創(chuàng)作漫畫,擔(dān)負(fù)起偉大的宣傳使命,全身心地匯入抗擊民族侵略主題的洪流中。他時(shí)刻關(guān)注抗戰(zhàn)局勢(shì)的發(fā)展,通過(guò)觀察與思考,及時(shí)地用通俗易懂、極具說(shuō)服力的諷刺漫畫,不斷地回應(yīng)自己從報(bào)刊上獲得的信息,揭露事物的本質(zhì),表達(dá)對(duì)侵略者的控訴,對(duì)不作為政府的抗議和對(duì)勞苦百姓的同情。對(duì)國(guó)家和民族觀念的自覺(jué)觀照讓張仃的設(shè)計(jì)有了明確的情感歸屬和強(qiáng)大的精神支撐,他的設(shè)計(jì)作品,在民族危難關(guān)頭發(fā)揮著投槍匕首的戰(zhàn)斗作用,代表著中華民族擺脫帝國(guó)主義壓迫、抗擊侵略暴行的強(qiáng)烈愿望,記錄了特定時(shí)代中華民族的進(jìn)步呼聲,也由此呈現(xiàn)出鮮明的歷史民族印記。
(二)深厚的文藝修養(yǎng)和廣泛的藝術(shù)興趣 在大多數(shù)人眼中,搞藝術(shù)的人是不大愛(ài)讀書的,但張仃卻是一個(gè)例外。從他發(fā)表的近百篇文章來(lái)看,其閱讀面不僅涵蓋了藝術(shù)史和藝術(shù)技法等專業(yè)知識(shí),還包括了古今中外文史哲等諸多學(xué)科領(lǐng)域的積累。這種廣泛全面的知識(shí)積累讓他能夠?qū)⒏鞣矫嫘畔⑷跁?huì)貫通,站在一個(gè)較高的角度去進(jìn)行設(shè)計(jì)構(gòu)思,批判地吸收民族優(yōu)秀藝術(shù)遺產(chǎn),從而賦予作品文化的內(nèi)涵。此外,廣泛的藝術(shù)興趣也對(duì)張仃設(shè)計(jì)民族風(fēng)格的形成發(fā)揮著重要影響。藝術(shù)接受之廣,讓他能夠通過(guò)對(duì)各門類藝術(shù)的縱橫比較,探究不同歷史時(shí)期和不同地域藝術(shù)風(fēng)貌之異同,進(jìn)而對(duì)形式美的規(guī)律形成更加客觀與深刻的認(rèn)識(shí),也有助于他突破僵化的固定模式,打通各種約束與界限,以開(kāi)廣的藝術(shù)視野博采眾長(zhǎng),讓作品呈現(xiàn)出煥然一新的民族風(fēng)格形態(tài)。
(三)扎實(shí)的筆墨功底和志趣相投的良師益友 從張仃先生在繪畫和書法藝術(shù)上取得的成就來(lái)看,其筆墨功底非同一般。他的焦墨作品腴潤(rùn)、厚重,既繼承了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的筆墨,又比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多了些時(shí)代氣息和蓬勃朝氣,猶如交響樂(lè)中敲擊樂(lè)器的鏗鏘之音,雄強(qiáng)高昂。他的小篆用筆靈動(dòng)、遒?gòu)?qiáng),具有石鼓文結(jié)體寬博舒展、氣韻樸茂自然的風(fēng)格特征。扎實(shí)的筆墨功底豐富了張仃設(shè)計(jì)作品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為他在設(shè)計(jì)上獲得藝術(shù)升華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更促使他由技進(jìn)道地對(duì)民族藝術(shù)風(fēng)格形成更加深刻的領(lǐng)悟,從而對(duì)其設(shè)計(jì)思維、審美和表達(dá)的方式均產(chǎn)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此外,張仃身邊有許多出類拔萃的優(yōu)秀藝術(shù)家朋友,如葉淺予、張光宇、黃苗子、郁風(fēng)等人,這些人大多是民族風(fēng)格的倡導(dǎo)者和踐行者,在與這些優(yōu)秀藝術(shù)家朋友的交流、溝通、合作、共事的過(guò)程中,他們的民族風(fēng)格觀必然會(huì)從各個(gè)方面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張仃設(shè)計(jì)創(chuàng)作的民族風(fēng)格審美趣味。
(四)與生俱來(lái)的藝術(shù)天賦和對(duì)生活的深入觀察 張仃先生擁有與生俱來(lái)的藝術(shù)天賦,這種天賦讓他能夠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方面具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天才性的先知先覺(jué)。他能夠從人們不以為然的日常生活中——如雪白饅頭上鮮紅的圓點(diǎn),農(nóng)村女孩眉心上的胭脂點(diǎn),平民瓜皮帽尖上殷紅的圓頂,發(fā)現(xiàn)美的趣味,提煉美的規(guī)律。可見(jiàn),他對(duì)形式之美具有天性般的感悟能力,而他的設(shè)計(jì)作品,更是讓人無(wú)時(shí)不刻地感受到這種原生態(tài)的、與生俱來(lái)的藝術(shù)天賦的存在。如他能夠用農(nóng)村最為尋常的農(nóng)具——篩面的籮圈和籮網(wǎng)設(shè)計(jì)制作成浪漫質(zhì)樸的壁燈,驗(yàn)證了其得天獨(dú)厚的藝術(shù)天賦。在藝術(shù)領(lǐng)域得天獨(dú)厚的先知先覺(jué),讓張仃先生褒有持久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熱情,而這股熱情又讓他比一般人更加熱愛(ài)生活。他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走遍大江南北觀察摹寫民族生活,這讓他的設(shè)計(jì)隨處可見(jiàn)生活的痕跡,同時(shí)也讓他的設(shè)計(jì)思維不受制于習(xí)慣與常態(tài)化的模式,讓他能夠不去重復(fù)別人的創(chuàng)作成果,甚至也不必重復(fù)自己已經(jīng)取得的創(chuàng)作成果,讓其作品具有多元飽滿的形態(tài)、持久的生命活力和深沉厚重的民族風(fēng)格特色。
鮮明的民族風(fēng)格是當(dāng)今設(shè)計(jì)吸引世界目光的重要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gè)尷尬現(xiàn)實(shí)是,設(shè)計(jì)民族化的呼聲遠(yuǎn)遠(yuǎn)高于優(yōu)秀民族風(fēng)格設(shè)計(jì)作品的產(chǎn)出數(shù)量,有許多設(shè)計(jì)師仍然在創(chuàng)作中將民族風(fēng)格簡(jiǎn)單地理解為民族符號(hào)的添加。張仃先生的設(shè)計(jì)作品造型樸素、形式簡(jiǎn)潔、色彩濃郁、構(gòu)思奇巧,是學(xué)界公認(rèn)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民族風(fēng)格設(shè)計(jì)的光輝典范。認(rèn)真研究其作品的風(fēng)格特色,分析其作品民族風(fēng)格形成的原因,無(wú)疑有助于對(duì)設(shè)計(jì)民族風(fēng)格形成更深刻的認(rèn)識(shí)。
[1]華君武.中國(guó)現(xiàn)代美術(shù)全集[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8:193.
[2]郭沫若.新華頌[N].人民日?qǐng)?bào),1949-11-27.
[3]吳冠中.向探索者致敬——張仃畫展讀后記[M]//李兆忠.大家談張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70.
[4]張仃.談波蘭宣傳畫[J].文藝報(bào),1955(23)51.
[5]張仃.我與中國(guó)畫[M]//雷人子編.張仃文集.濟(jì)南:山東美術(shù)出版社,2011:141.
責(zé)任編輯 張吉兵
G623
A
1003-8078(2017)05-0055-05
2017-09-02
10.3969/j.issn.1003-8078.2017.05.14
彭茹娜(1976-),女,湖北武漢人,湖北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項(xiàng)目編號(hào):13YJC760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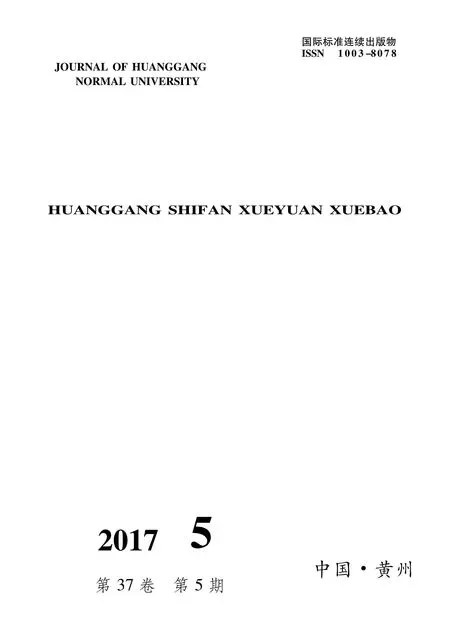 黃岡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年5期
黃岡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年5期
- 黃岡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基于有序Logistic模型農(nóng)戶精準(zhǔn)扶貧滿意度的影響因素研究
——以湖北大別山片區(qū)為例 - 鄂湘地區(qū)“編導(dǎo)”、“播主”藝考培訓(xùn)現(xiàn)狀調(diào)查
- 愉快教學(xué)法在《旅游地理學(xué)》課程中的實(shí)踐探索
- 基于崗位需求的《市場(chǎng)營(yíng)銷》課程CDIO教學(xué)模式構(gòu)建與實(shí)施
- 應(yīng)用型專業(yè)與就業(yè)的匹配性研究
——以高職商務(wù)英語(yǔ)專業(yè)為例 - 基于微信公眾平臺(tái)的高校圖書館閱讀推廣調(diào)查分析
——以南京地區(qū)高校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