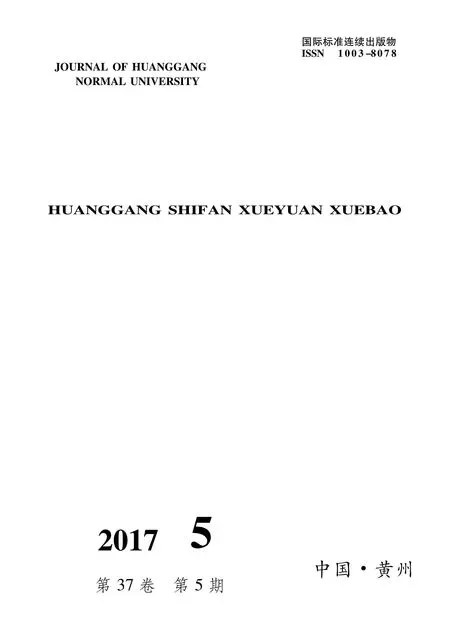日本電影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
——以《情書》和《東京日和》為例
孫英莉
(黃岡師范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北 黃岡 438000)
日本電影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
——以《情書》和《東京日和》為例
孫英莉
(黃岡師范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北 黃岡 438000)
日本電影因其濃厚的民族特色,受到了東西方觀眾的普遍贊賞,在世界電影史上取得矚目的成就。日本電影在情感表達方面完全不同于西方電影中的熱情奔放、直抒袒露,顯得含蓄內斂、深邃幽遠。這實際上體現了日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審美追求——幽玄。本文以電影《情書》、《東京日和》為例,分析日本幽玄電影的情感表達方式及其文化審美心理。
日本電影;幽玄;審美心理
一
電影除了可以借助電影音樂來表達情感外,它還可以直接通過人物的言行舉止,輔以各種畫面造型手段來表達劇中角色或電影創作者的情感。不同的國家因民族個性和傳統文化的差異,在情感表達上呈現出迥異的品格特質。西方國家崇尚自由、平等、博愛,情感表達濃郁奔放、直抒袒露;東方國家崇尚自然法則、倫理秩序,情感表達平和沖淡、溫雅節制。這種民族性情的差異性直接影響到民族電影風格的差異性。日本民族性格推崇隱忍、靜謐,相應地在他們的電影中,情感表達呈現出含蓄內斂、深邃幽遠的風格特征。
含蓄內斂、隱忍節制的情感表達是日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審美追求——“幽玄”的重要體現。具體說,它指的是作者把要表達的思想情感、意象等間接、委婉地表現出來,給讀者或觀眾留下無窮韻味和思索空間的一種含蓄美,一種難以言表的微妙的、深遠的境界。作為日本審美意識中的核心范疇,充分顯現了日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追求。幽玄類似于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蘊藉”這一概念,都強調含蓄深遠,意味無窮的審美意蘊。余秋雨直而言之:“柔和,纖弱,雅麗,蘊藉,這就是‘幽玄’美的主要傾向。”[1]幽玄美幾乎滲透在日本文藝的一切樣式中,“無論是和歌、俳句、能樂、散文以及物語文學乃至園林建筑、插花、茶道,無不閃爍著一種深奧玄寂、綺麗纖細、疏散自如、微妙虛幻的幽玄之美。”[2]
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日本電影特別是家庭倫理片與青春愛情片,在情感表達方面都極其推崇含蓄、委婉、節制的幽玄美,表現了日本民族所特有的美學風格,甚至在日本的暴力影片中也無不體現這一美學追求。如北野武的《花火》雖然描寫暴力,但不像吳宇森那樣把血腥暴力赤裸裸地暴露在觀眾面前,而是把暴力、死亡和溫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用一種瞬間的暴力與靜態的彩色漫畫相互穿插、映襯,表現出凄艷的美。
談到日本電影的民族性,不能不提到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它們被認為是最具日本民族風格的電影作品。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大多以現代日本家庭生活為題材,表現現代社會生活的風俗習慣和人情味,沒有激烈的戲劇沖突,沒有波瀾壯觀的場面。這對于習慣于欣賞美國好萊塢類型電影中戲劇性情節、動作化場面的觀眾而言,也許會難以接受。因為小津的影片極其生活化,就像生活的自然流露,平平淡淡。但正是通過平淡的生活場面,通過人物行動與對話,蘊藏著豐富的情感內涵。如電影《東京物語》中,表現的是尋常人的尋常事,這些人就存在我們的周圍,這類故事我們或許耳聞目睹。但小津并沒有讓他的電影流于庸俗平乏,他描寫傳統的日本家庭是如何分崩離析,傳達了傳統家庭因工業社會而導致的親情疏離這一主題。影片中,平山周吉夫婦從農村來到東京時,并沒有因為兒女們的冷漠疏離而抱怨,而是表現出一種寬容、體涼的心態。平山周吉在喪妻后,也沒有表現得極度悲傷,反而非常平靜,把對妻子死亡的痛苦藏于內心。小津電影中的鏡頭語言也不像好萊塢電影那樣,頻繁切換,大量使用兩極鏡頭,而是采用低角度中景鏡頭,并喜歡用長鏡頭。這些無不體現導演小津在電影中的含蓄、空寂的審美態度。這一美學思想,在同時代的導演如溝口健二、成瀨巳喜男等人的電影中都有所體現。
二
日本年輕一代的導演如巖井俊二、竹中直人等,繼承了老一代導演的這一美學思想,為觀眾創作了一些經典的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電影作品。巖井俊二導演的電影《情書》以奇特的構思,通過博子與女藤井樹之間的通信,逐漸揭開了一段塵封已久的愛情故事。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劇情建構離不開編劇奇妙的構思,而這一構思的奇妙之處在于人物設置的巧和情節虛構的巧。首先是人物設置上運用了多重巧合手法,不僅男女主人公有著同樣的名字,而且渡邊博子與女藤井樹有著同樣的模樣,影片中還用同一個演員扮演兩個角色。其次,在情節虛構方面,編劇有意讓博子抄錯地址,把女藤井樹的地址當作男藤井樹的地址,以便讓博子與女藤井樹之間通信,展開女藤井樹的那一段美好的回憶。為了突出回憶中的美好,導演有意在光影處理方面讓現實部分陰暗,而回憶部分則顯得格外明亮。盡管影片中女藤井樹與男藤井樹的那一段美好的回憶在整個影片中所占時間不長,但卻是最有份量的一部分,不僅是因為影片中的少男少女的愛情,更為因為影片中含蓄節制的情感表達,撥動了有著類似經歷的觀眾心中那根青澀暗戀的琴弦。正處于少年中的或經歷過少年的人,都有過青春期的萌動,對異性純情的渴望與追求,它們正是我們成長的印記。導演把這份既具有私密性,同時又具有普泛性的人類情感,通過唯美的畫面和動人的背景音樂呈現給觀眾,讓觀眾緬懷這段美好的時光,觀眾無不為之動容。而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正是影片《情書》的魅力所在。
竹中直人導演的《東京日和》是另一部值得稱贊的具有日本民族審美追求——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風格的經典電影。《東京日和》取材于日本著名攝影家荒木真惟與他的亡妻的真實故事,以倒敘的方式講述了攝影家島津和他的妻子生前的點點滴滴與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影片自始至終這對夫妻既沒有接吻等親密恩愛的舉動,也沒有甜言蜜語的對話,但從他們多次平常的吃飯場面中,從被有意延伸了的彼此對視中,觀眾能捕捉到其中綿綿纏繞著的情愫,并且為之深深感動。影片在追憶一份逝去的溫情,既表達了島津對他亡妻無限的思念,也給那些忙于工作而忽略了身邊的親人和朋友的人送來一縷既溫暖又刺骨的春風,促使他們去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默默地去愛身邊的每一個親人和朋友。島津與他妻子之間默默的溫情以及島津對他妻子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呵護與關懷,都是深藏于夫妻共同相處的日常生活細節之中——“這樣的定位沒有展示驚心動魄的大場面的契機,面且在處理夫妻的誤會與沖突上竹中直人也以盡其可能地含蓄委婉,所以整部影片的鏡語風格呈現出一種情緒化濃郁日常性濃重的特征,竹中直人的鏡頭影像構成是對生活中最細膩常態的捕捉,是心理特點完全日本化的影像再現。”[3]
三
日本電影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集中表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而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又是通過一些細節來刻畫的。在影片《情書》中,導演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動作細節,塑造了一位性格內向但又很可愛的男主人形象,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堂課教師點名,因出現同名現象,男女主角彼此對視,盡管男主角表面上顯示出一副不屑一顧的表情,但內心深處卻喜歡上了這個有著同樣名字的女孩子。為了博得女孩子的關注,但又羞于對她的表白,男主角做出反常態的表現。他在班委選舉時大打出手,表現出英雄救美的姿態;作為圖書委員,他不幫女主角整理圖書,卻站在窗戶旁假裝看書,還在書上留下對方的名字,把對她的愛慕隱藏在圖中;他還有意拿錯試卷,在停車場通過糾纏于試卷的內容來拖延與她相處的時間;當女主角要幫他介紹女朋友時,他卻表現出憤怒之情,并且在放學的路上把袋子惡作劇地套在她頭上。盡管他左腿骨折,但仍堅持上賽場,只希望搏得她的關注;當他要轉學了,他有意請女主角幫他還書,因為他在書上藏著畫有女主角畫像的卡片。影片細膩地傳達了青春懵懂期少男的暗戀心理,以一種含蓄的情感表達和隱忍美打動了無數男女觀眾的心,成為日本電影追求幽玄的審美意識的典型文本,“正象人們從日本的‘能樂’所看到的那樣,盡可能地控制外部的表現,將感情凝聚于內部,表現這種內部的情結,這是日本藝術傳統的心理要素之一”。[4]
在影片《東京日和》中,主人公島津和妻子陽子之間真摯的感情,表現為島津在日常生活中對他妻子默默地關心、呵護與體貼,于無聲處見真情。影片一開始,島津和妻子因一點小事鬧矛盾,島津的妻子出走三天沒回來,事后島津深感自責,于是跑到妻子的公司找她。島津對妻子的關心與呵護自然地流露出來。最感人的是他們在野外巨石上彈奏《土耳其進行曲》這場戲。在一次晨跑中,突然下起了雨,島津和妻子往家趕,妻子突然停了下對島津說:“看,鋼琴!”原來她指的是路邊一塊大石頭,于是他們興沖沖地走過去,在石頭上“彈奏”起了莫扎特的《土耳其進行曲》。他們就像小孩子似的陶醉于眼前的那快巨石,一邊彈一邊唱,其樂無窮,全然不顧正下著的雨。與其說他們陶醉于眼前的那快巨石,毋寧說是他們陶醉于此刻幸福的感覺。這種感人的場面和細節還有很多,如島津和妻子在回家的路上你一下我一下來回地踢著易拉罐,有說有笑;再比如有一次在理發店中島津睡著了,妻子走丟了,他苦苦尋找他的妻子,最后在一條船上發現熟睡的妻子,他從焦急的表情轉為欣慰,并激動地流下了眼淚……影片在東京溫煦細小的陽光下,時而優雅時而感傷地描繪出夫婦間真摯的感情。
四
日本電影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還體現在一些貫穿影片始終的具有象征性的道具運用上。影片《情書》中先后四次出現了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整個故事正如書名那樣,在不停地追憶過去美好的時光。這本書第一次出現在圖書館里,女藤井樹正在為這本書做書卡,而男藤井樹站在風中飄動的白窗簾后面若隱若現。女藤井樹沒有料到的是,多年后,她真的再次打開塵封的記憶,開始追憶曾逝去的時光。當她再次走進圖書館,看到風中飄動的白窗簾后面空無一人時,此情此景,讓她觸景生情,耐人尋味。這本書第二次出現在女藤井樹的家門口,當時男藤井樹因為要轉校,于是在書中的卡片背面畫有她的肖像,并讓她去幫他還這本書,想借此表達他的愛慕之情。但讓女藤井樹沒有想到的是這卻是她們最后的見面,他與男藤井樹的一切只能在她的塵封的記憶中追尋。這本書第三次出現還是在圖書館,當女藤井樹要幫他把書放入書架時,又情不自禁地翻開看了一眼書卡,因為書卡上有男藤井樹寫下的名字。這本書第四次出現是在女藤井樹家的大門口,學妹們羨慕地把十多年前男藤井樹寫給她的“情書”——一張畫有她肖像的卡片送過來時,她突然明白了許多年前不曾知道的秘密,于是眼睛里噙著眼淚。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在影片中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它成為男女主角之間傳遞情意的媒介;另一方面,它被創作者賦予了特殊的內涵,成為揭示影片主題的一個象征性道具。影片正是通過對已逝年華的追憶,對愛情和死亡的描繪,以東方特有的含蓄優美,略帶感傷地表達了影片的主題:珍惜有限的生命和美好的愛情。
影片《東京日和》中也多次運用了“向日葵”這一道具,無論是家里的向日葵,福崗車站的向日葵,朋友送來的向日葵,還是影片結尾時出現的兩枝向日葵,在影片中都成為一個具有能指功能的“符號”,象征著島津與妻子之間的愛情。
日本電影含蓄內斂的情感表達方式除了表現在劇作上外,還表現在景別、構圖、場面調度等影像語言中。由于篇幅的原因,在此不做詳細闡述。總之,日本民族的個性心理對日本電影的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而日本電影中特有的含蓄內斂的風格,又集中體現了日本民族的個性心理和文化審美追求,成為日本民族電影的一個重要特征。作為亞洲電影中最早崛起的日本電影,有許多方面值得中國電影借鑒和學習,而日本電影與日本民族之間所構建的互文現象以及日本電影在民族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探索,尤其值得中國電影人深思。
[1]余秋雨.戲劇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58.
[2]梅曉云.日本文化的“幽玄美”[J].人文雜志,1990(1)124.
[3]虞吉,葉宇,段運冬. 日本電影經典[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179.
[4][日]南博.日本人的心理[M].劉延州譯. 上海:文匯出版社,1991:67.
責任編輯 張吉兵
J90
A
1003-8078(2017)05-0073-03
2017-08-02
10.3969/j.issn.1003-8078.2017.05.18
孫英莉(1981-),男,江西吉安人,黃岡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