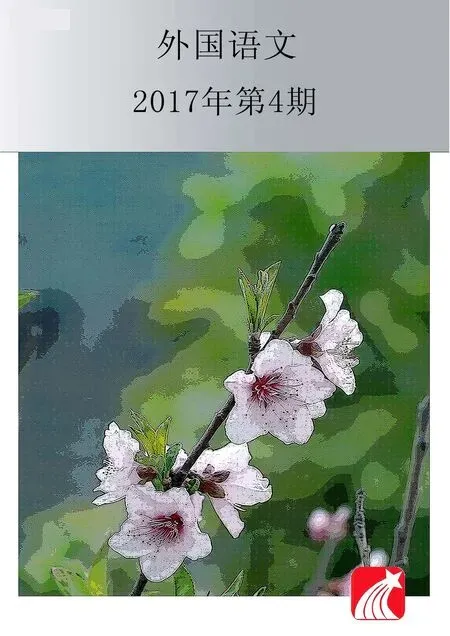“后記憶”之后
——“后記憶”概念之探微
程 梅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后記憶”之后
——“后記憶”概念之探微
程 梅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隨著以“后現代”為代表的多個“后”概念不斷遭到質疑甚至顛覆,瑪麗安·赫希提出的“后記憶”概念岌岌可危。“后記憶”描述了大屠殺幸存者后代的隔代記憶,強調創傷影響跨越代際距離的持續存在。本文以大屠殺親歷者后代的紀實敘事以及小說《噩夢父親》為例分析記憶與后記憶的關系,展現幸存者無論沉默還是健談都會導致與子女之間話語交流不暢、情感交流失敗的問題,從而質疑后記憶中創傷影響的跨代延續,進而推翻后記憶的存在。
記憶;后記憶;創傷傳遞;大屠殺
0 引言
21世紀的文學理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后”時代。各種以“后”修飾的概念,如后殖民、后女權、后結構、后工業化、后二戰、后9-11等術語,充斥著各個流派的文學理論、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及評論。那么,除了時間滯后,“后”與“原”概念之間存在什么關系?是變革、創新,還是更弦改轍、另辟蹊徑?一篇題為《子虛烏有的“后現代”》的文章否定了“后現代”與“現代”之間的上述關系,質疑學術界將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區別開來的傳統做法,指出后現代是對現代的繼承和發展(阮煒,2004:67),二者之間“沒有什么本質區別,而是一脈相承,兩位一體的”(阮煒,2004:68),從而大膽得出結論:后現代不是全新的概念,最多只是現代主義的附庸(阮煒,2004:68)。如果作為20—21世紀文學、藝術典型特點的后現代都是子虛烏有,那么其他眾多“后”概念的狀況又是怎樣的呢?本文關注的正是其中之一——“后記憶”及其與“記憶”的關系。
1 記憶、后記憶中的創傷延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發起了慘絕人寰的種族清洗,歐洲多國人民生活在法西斯暴行的鐵蹄下,超過600萬無辜猶太人慘遭屠殺。那段殘酷的歷史成為揮之不去的記憶,縈繞在幸存者心頭。隨著大屠殺的漸行漸遠,事件親歷者慢慢淡出歷史舞臺,他們的后代成為紀念、繼承大屠殺遺產的主力軍;記憶產生的源素材也由親眼見證的畫面、親身經歷的事件逐漸轉變為檔案館保存的文字、聲音與影像的證詞、證言,這些證據材料承擔著向后代的文化記憶輸出大屠殺歷史的責任。大屠殺受害者后代繼續訴說著戰爭的殘酷,形成所謂的“大屠殺后敘事”(林斌,2007:3),他們的聲音在公共生活和學術界都表現了強有力的存在。
大屠殺影響深遠,不僅親歷者甚至他們的后代都深受其害。孩子們的生活重新經歷了納粹集中營的創傷,非人的經歷通過父母與子女關系的互動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學者們用各種術語描述那些出生在大屠殺之后的幸存者后代的隔代記憶:“缺失記憶”“傳承記憶”“遲后記憶”“移植記憶”“空洞記憶”“灰燼記憶”等(Hirsch,2008:105),這些術語反映了后代深切感受到上輩人遭遇的不幸,創傷記憶甚至傳遞到從未經歷過事件本身的那些人。雖然這種間接記憶不同于當事人的直接回憶,但是,上述種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共同修飾一個核心成分——“記憶”,說明盡管對后代記憶的真正含義有各種不同的認識,但創傷影響的持續存在是眾多學者的共識。
在表述幸存者后代對大屠殺創傷記憶的眾多術語中,影響最為廣泛、深遠的是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的“后記憶”(postmemory)概念。孩子們沒有經歷過大屠殺,對事件本身沒有任何記憶,卻生活在父母遭受創傷的陰影下,形成所謂的后記憶。赫希說:“他們伴隨著出生前的事件長大,既無法理解也不能完全想象出上一代的創傷經歷,但自己后來的生活卻被這些事件填滿了。”(Hirsch,1997:22)赫希關注“后記憶”的前綴“后”,而“記憶”在她看來似乎不言自明。她認為,后記憶不僅意味著“在記憶之后”,而且,因其代際距離而區別于記憶,因緊密的個人聯系而區別于歷史(Hirsch,1997:22),“后”更表達了一種“令人煩惱的延續”和“密切相關”(Hirsch,2008:106);赫希進一步解釋說,在“記憶”前面“強調‘后’說明了創傷后遺癥在兩代之間的傳遞與共鳴”(Hirsch,2008:106)。也就是說,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代際距離沒有阻隔創傷的延續,相反卻帶給后代直接的創傷影響。赫希認可后記憶在時間上的滯后性,但她更強調傷痛的連續性:事件雖然“發生在過去,但影響持續至今”(Hirsch,2008:107)。雖然時間上孩子們遠離父母的創傷事件,但卻生活在創傷的直接影響之下;雖然沒有親歷過,但痛苦的回憶卻通過父母的言行和媒體的宣傳深深地烙在孩子們心里,構成他們自己記憶的一部分。所以,在赫希看來,盡管后記憶是上一代人植入孩子們頭腦中的記憶,但它包含對過去事件強烈的創傷情感。
后記憶概念一被提出,學者們紛紛用它描述幸存者后代對大屠殺的記憶,在共同的后記憶傷痛中表達著猶太性的延續。其中我國學者關注的有美國猶太作家福厄的小說《一切皆被照亮》中的美國猶太青年作家前往烏克蘭尋根,用父母的視覺記憶填補自己的缺失記憶(曾桂娥,2015:39);美國女作家歐茨的短篇小說《表姐妹》表現了相似的猶太人尋根和認親主題,大屠殺后記憶起到認同猶太民族意識和個體身份的作用(林斌,2007:3)。除了用于敘述對大屠殺的間接記憶,后記憶還“可以有效描述其他文化或集體創傷事件和經歷的二代記憶”(Hirsch,1997:22)。例如,蘇雷曼將后記憶概念用于后殖民流散人群對上一代人流亡經歷的傷痛記憶(Suleiman,1999:v),利維用后記憶論述經歷獨裁統治后烏拉圭人民的跨代創傷記憶(Levey,2014:5)。華裔文學研究中,以“后記憶”為題的文章——《離散族裔的創傷與后記憶》(呂燕,2012)和《移民“后記憶”陰影下的自我重建》(程梅,2015)——將后記憶表現為因移民引發的創傷經歷從第一代移民傳遞到第二代的間接記憶。此外,在《德國、波蘭與后記憶關系》(Germany,Poland,andPostmemorialRelations)一書中,作者科普和尼金西卡(Kopp & Nizynska,2012)注意到后記憶的承載者逐漸從個人擴展到集體,因為后記憶的形成和改變受到國家政治、文化和經濟壓力的影響。從20世紀90年代初赫希提出后記憶概念至今短短20幾年的光景,已經有了“后后記憶”概念,用于描寫第三代幸存者的間隔兩代的創傷記憶(Bayer,2010:116)。赫希等人還創立了宣傳后記憶的專業網站——postmemory. net,以幸存者后代的身份紀念、記錄大屠殺歷史遺跡及其產生的個人、集體和文化記憶。后記憶似乎不僅可以廣泛用于描述創傷影響的跨代延續、傳遞,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本身也同樣具有驚人的傳播效果:從紀念大屠殺到記述其他創傷事件、從描述個人記憶到敘說集體記憶、從第二代的“后記憶”到第三代的“后后記憶”、從書本文字的紙質載體到虛擬網絡的電子媒體,等等。
2 質疑創傷延續、顛覆后記憶
上述關于后記憶的眾多論述、應用和研究都在運用這樣一個概念:幸存者與后代之間的關系被描述為創傷影響的延續和傳遞。在第二三代大屠殺見證文學和證詞中,記憶、后記憶的跨代延續性似乎也在證明大屠殺幸存者經歷的創傷延續。但是,稍加留意不難發現,“第一代”“第二代”這種說法本質上存在問題:第一代是幸存者,或者說是戰爭受害者,第二代是第一代的延續,“第二代幸存者”或“第二代受害者”的表達方式似乎在說他們與父輩一樣也是戰爭受害者、幸存者,不同的是父輩是第一代受害者、幸存者,他們是第二代受害者、幸存者,當然,這不是事實。第一代與第二代的順序關系一方面客觀反映了上下輩分的傳承,另一方面錯誤地傳遞出創傷受害者身份的傳承而忽略了第二代是全新的一代,與父母那一代經歷根本不同的事實。兩代之間血緣關系的自然延續模糊、混淆了彼此記憶、經歷內容本質上的不同。
完成第三稿之前教師的反饋應更具條理性,從詞匯和句式的準確性、內容的邏輯性和語篇的連貫性等方面逐一列出學生的共性問題,結合學生作文中的實例給出修改建議并共享給學生,供學生逐條核對修正自己第二稿中的問題。
記憶與后記憶之間也存在同樣問題。赫希在“記憶”前面加上“后”修飾,表示后記憶本質上是記憶,一種非常特殊的記憶(Hirsch,1997:22),在情感作用上接近記憶(Hirsch,2008:109),但在產生方式上又不同于記憶,因為它與記憶內容的聯系不是通過回憶而是通過想象和創造。然而,后記憶的想象、創造性本質不能使它從根本上區別于記憶,因為根據赫希的觀點,記憶也是間接的、經過思考形成的;二者之間只有一個細微差別:記憶“與過去的聯系更為緊密”(Hirsch,2008:109)。但是,聯系緊密程度大小只是量的差別,無法表明兩個概念存在本質區別,這種不明確地使用后記憶概念的做法源于一個無法規避的矛盾事實:赫希想用后記憶表達子女與父母緊密的個人關系,同時與創傷事件缺乏聯系。但是,一個詞怎么能同時準確表達既(與父母聯系)緊密、又(與事件聯系)松散的矛盾關系呢?
此外,從記憶構成上看,記憶與過去的聯系完全是依附的:一個人記憶的存在是因為他曾經經歷過,記憶是大腦對經歷過事物的識記、保持、再現或重復,也就是說,記憶的內容是記憶主體經歷過的事物。上文提到,通過命名后記憶,赫希似乎希望建立與過去事件的聯系,但是,她所稱的孩子們的“緊密的個人聯系”首先應該是與父母而不是與創傷事件的聯系,因為只有通過與父母的聯系才有可能建立起與創傷事件的聯系,與后者聯系的建立是孩子們對父母-子女關系的認可而不是對過去事件的重視或者受到過去事件的傷害。所以,將子女對大屠殺事件的認知稱為“后記憶”合適嗎?如果說子女后記憶的對象或內容是父母談及、影射的大屠殺經歷,這似乎混淆了兩代人的不同經歷,因為子女沒有經歷過大屠殺,所以大屠殺也就無法成為記憶的內容,對事件的了解也無法構成后記憶。
大屠殺幸存者后裔霍夫曼關注大屠殺與記憶的復雜聯系,她用“記憶、歷史和大屠殺遺產”(Memory,HistoryandtheLegacyoftheHolocaust)作為自己紀實文學著作的副標題,從創傷第二代的切身感受描述子女與大屠殺事件的關系。霍夫曼明確指出,雖然人們已經習慣說大屠殺“記憶”,但是“記憶”一詞不適用描述孩子們與大屠殺之間的關系,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大屠殺(Hoffman,2004:6)。但霍夫曼無法準確定義這種關系,因為那是一種“更強有力的、更不清晰的事物……有時近乎精神狀態的體現”,而無論原始素材是什么,都是孩子們“無法消化、無法融入意識流或記憶,也無法明白易懂的情感”(Hoffman, 2004:7),那是一種“沒有具體性狀的失落感”(Hoffman, 2004:73)。孩子們與這種看不見、摸不著、趕不走、說不清的幽靈生活在一起,感到“相比與現實困難做斗爭,與陰影摔跤更可怕、更令人無所適從”(Hoffman, 2004:66)。父母通常沉默,小心翼翼地回避著與大屠殺相關的一切事物;即便無意間談及,剛一出口便馬上敏感地意識到觸碰了雷區,話語立刻變得唐突、破碎與結巴,無法按正常邏輯繼續進行,只能語無倫次地說出零星的只言片語、重復贅言或者干脆欲言又止,這樣的交流無法融入連貫的敘事和話語秩序,而只能成為父母-子女情感發展的障礙。
霍夫曼的與陰影摔跤比喻反映了家庭記憶傳輸的失敗,產生了范恩所說的“無法傾訴事件的緊密真空”(Fine,1988:44)。與霍夫曼一樣,范恩也是大屠殺幸存者后代,她解釋說,孩子們“不斷地遭遇父母和親戚的沉默,家人傳遞給他們的……不是記憶”(Fine, 1988:43)。同樣,作為與大屠殺親歷者最親密的接觸者,霍夫曼這樣描寫她所承載的“記憶”:“那些記憶,不是戰爭經歷的記憶而是放射物,不停地像飛逝的圖像、破碎的殘片一樣噴發。”(Hoffman,2004:9)赫希引用霍夫曼對那段記憶的感受,矛盾地總結說:“正是這些肢體語言表達的‘飛逝的圖像’和‘破碎的殘片’所傳遞的‘非記憶’構成了后記憶的全部內容。”(Hirsch,2008:109)如果像赫希所言,后記憶的全部內容都是“非記憶”,即“不是記憶”“沒有記憶”,那么,后記憶也就是個虛無存在的概念了。幸存者后代承載的是一種認知,是通過視聽、感覺、思維和想象等多種方式對外界事物進行信息加工的結果。這種認知無論是否作為創傷后代都可能通過公共文化中廣泛流通的大屠殺文學、電影、回憶錄、日記和證人證言等各種信息渠道獲得。創傷后代的痛苦感源于(受創傷的)父母而不是源于創傷事件本身。后記憶概念的創立混淆了這兩個不同概念。
3 《噩夢父親》中創傷延續的失敗
霍夫曼和范恩作為幸存者后代的切身感受表明,后記憶中創傷延續的說法本質上存在問題,這一點可以從另一位大屠殺幸存者后裔、荷蘭作家卡爾·弗里德曼(Carl Friedman)的小說《噩夢父親》*這部小說目前沒有中譯本,小說中文題目和引文的中文譯文均出自筆者。(Nightfather,2004)中父親與子女之間話語、情感交流失敗的故事更加具體、形象地反映出來。小說以自傳體形式,從年僅7歲的女兒角度用最簡單的語言描述了父親作為大屠殺幸存者的納粹集中營經歷對自己以及家人無法抹去的創傷影響。作為大屠殺見證文學,作品講述了幸存者口中的駭人經歷,雖然噩夢已經過去,但夢中人卻還沒有完全醒來,噩夢仍在現實生活中重復出現。小說中父親創傷后遺癥的表現形式不同于霍夫曼或范恩父母那樣的戰爭受害者通常沉默、無法傾訴、刻意回避自己過去經歷的做法。他對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喋喋不休、反復提起,不顧家人的感受以及子女是否理解,強迫癥似的講述如何歷經苦難,與死亡擦肩而過的種種細節,無法自持。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一種情況——吃飯、踢足球、郊游、參加宗教祭拜——都會激起父親回到過去的沖動,都會令他想起集中營的恐怖過往。如果在霍夫曼和范恩的親身經歷中因為創傷幸存者的沉默寡言、話語障礙導致交流失敗,進而導致創傷傳遞失敗,那么《噩夢父親》中父親這種喋喋不休的聒噪、發聲能否建立起與家人特別是與子女的有效交流?他確實講了很多,但是聽眾能理解多少?
年幼的女兒作為敘事者講述生活在大屠殺陰影下的痛苦和迷茫,令人揪心和深感不安。孩子們一出生,他們的世界就籠罩著烏云,父親的集中營經歷永久地影響了他們,在尚未成年的年紀聽到父親談論大屠殺經歷首先產生了話語理解障礙。敘事者描述的畫面戲劇性地展現了父親對集中營的記憶并以此作為家庭話語標準,而這種標準在家庭以外的學校、朋友圈卻無法適用:她發現朋友的父親沒有集中營,有的是自行車、飯盒;朋友家人談話中沒有“營房、廁所或火葬場”這些詞(Friedman,2004:21)。她和兩個哥哥尷尬地介于父親的集中營世界和朋友、學校的真實環境之間。他們說著與周圍人不同的納粹集中營的語言,而此時的集中營語言發生的情境卻是現實生活。語言與語境的脫節造成了孩子們的認知混亂。不是那段歷史多么令人費解,而是他們無法分清父親曾經的集中營經歷與此時、此地現實生活的界限:“孩子們怎么能理解饑餓、羞恥和謀殺的故事?故事在哪兒結束、現實從哪兒開始?我們不知道。”(Friedman, 2004:135)
這種話語混淆標志性地反映在父親使用camp(集中營)一詞上。小說中,父親自創了一個現在時短語has camp表達自己曾經的集中營經歷,集中營不像是個地方而更像一種狀況,孩子們聽起來像在說有什么病。父親“有集中營”,而孩子們“得過水痘、風疹”,西蒙從樹上摔下來得過腦震蕩,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過集中營(Friedman, 2004:1-2)。時態混亂似乎真的將父親過去的集中營經歷變成現在的一種生活常態,反映在父親的臉上,更深入他的眼里。當敘事者在動物園里看到與父親有著同樣眼神的一匹狼在籠子里焦躁地踱來踱去時,她嚇哭了,脫口說出了描述父親狀態的語言:“它有集中營!”(Friedman, 2004:2)父親不僅嘴里說著集中營事情,臉上寫著集中營狀態,他還經常唱著集中營歌曲,用孩子們聽不懂的歌聲傾訴著內心的痛苦和難以名狀的失落。集中營似乎成了父親的專屬,代表著過去、苦難和病態,所以當朋友奈麗用這個詞指稱每周三下午的女童子軍活動,并說如果你不去“會錯過許多活動,電影啊、跟蹤攝影啊這些事情。還有野營(camp)!”時,敘事者吃驚地睜大了眼睛,重復道:“Camp!”(Friedman, 2004:40)理解失敗了。這里,敘事者認知范圍中只有父親的集中營(camp),沒有朋友口中的野營(camp)。
兩代人對集中營的不同理解表現了他們之間話語結構存在無法彌合的分歧,無法建立起有效交流。日積月累,彼此的隔閡和情感沖突日益強烈,特別是父親與大兒子麥克斯。當麥克斯問“集中營里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時,父親回答:“這樣的問題很愚蠢……是饑餓還是凌辱,是冬天挨凍還是夏天受熱,哪個更糟糕?被毒氣毒死比被繩索絞死更糟糕?誰能說清楚?”(Friedman, 2004:96)父親非但沒能回答麥克斯的問題,而且認為回想這些事情都是對逝者的侮辱。為了避免爆發沖突,父親試圖緩解劍拔弩張的氣氛,他安慰麥克斯說自己愛他,麥克斯反駁道:“你只愛你的黨衛軍!我們吃飯時,你繼續說你的挨餓!我們感冒時,你繼續說你的傷寒。別人的爸爸陪孩子在街上踢足球,而我唯一一次帶朋友回家,你卻只談你的集中營。你怎么不好好待在那該死的地方!”(Friedman, 2004:97)積累多年對集中營、對父親的集中營經歷的困惑、憤怒和埋怨在這一刻爆發了。當他向父親吼著,讓他還是待在集中營里為好時,顯然已經超越了話語底線,給父親造成二次傷害。從麥克斯的過激言辭可以得出與上一小節結尾相同的結論:孩子們更是受到父親而不是父親的創傷經歷的影響。小說題目Nightfather的構詞仿擬nightmare(噩夢),字面上雙重表現了父親的噩夢和噩夢般的父親,父親需要面對的是前者,即噩夢;孩子們需要應對的是后者,即父親,兩代人需要克服的問題存在本質不同,所以,創傷延續這種說法毫無意義。孩子們可能受到創傷,但是他們的創傷并非來自大屠殺事件本身,而是源自父親,曾經受到大屠殺傷害的父親。
孩子們生活在大屠殺陰影下,備受傷害。大屠殺文學研究學者阿爾芬認為,創傷的形成是因為當事人認知所依賴的理論參考框架沒有提供適合的詞匯或表達方式描述該事件的本質(Alphen,2006:482)。這一觀點準確解釋了《噩夢父親》中孩子們問題產生的原因。困擾父親的事件背景遠離孩子們的生活環境,他們所掌握的知識體系所構想出的畫面與事件發生的實際情況之間存在分歧,或者說,當描述大屠殺事件的詞匯置于孩子們的話語范疇時,無法表達出原始意義,只能形成一些晦澀的、偏頗的、缺乏邏輯的語義片段。他們所處的外界環境與父親營造的家庭環境以及父親講述的集中營往事存在不同的話語秩序,同一語匯表達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思。父親與子女之間的互動是斷續的、阻塞的,包含許多不解和誤解(如對camp的理解)。
大屠殺已經成為過去,父親的創傷依舊,痛得真切、劇烈,但是即便與父親朝夕相處的子女、家人對大屠殺、集中營經歷都無法感同身受,更別說作為非親歷者的旁人及其后代會理解多少了。幸存者的傷痛并非如赫希等眾多學者所言在傳遞給后代的過程中加劇了(Hirsch,2008:106;Goldenberg,1994:63;Berg & Coller,2012:145),因為幸存者的情感傷痛和精神傷疤是他人無法想象、無法感受的見證。喋喋不休的聒噪與緘口不言的沉默一樣無法傳遞內心的傷痛和苦悶。雖然父親的表現不同于那些話語障礙的幸存者,但是他的話語同樣無法將創傷經歷呈現、傳達給家人。此時,無論多語還是寡言都不能傳遞原始信息和當事人的內心創傷。
4 結語
綜上所述,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代際距離客觀存在,阻隔了創傷影響的有效傳遞,所以用父母記憶與事件之間的固有聯系描述子女經歷與事件之間缺乏聯系的實際情況注定是模糊的、混亂的與無效的。如果子虛烏有的后現代根本不存在是因為現代主義的強大和持續,“所產生而反過來又被它加強的精神氛圍同樣依然如故”,使現代主義不會存在短短幾十年后便走下歷史舞臺(阮煒,2004:65),那么后記憶虛無存在的原因則恰恰相反,那是因為創傷記憶無法跨越兩代人之間的時空距離而繼續存在。雖然后現代與后記憶概念的產生遭到質疑和顛覆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體現了文學概念發展路徑的復雜、迂回,以及概念本身引人探幽發微的魅力。
Alphen, Ernst. 2006. Second-Generation Testimony,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nd Postmemory [J].PoeticsToday(2): 473-488.
Bayer, Gerd. 2010. After Postmemory: Holocaust Cinema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J].Shofar(4): 116-132.
Berg, JPC van den and HP van Coller. 2012. Contextuality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Nightfatherby Carl Friedman [J].TydskrifvirLetterkunde(2): 136-149.
Fine, Ellen. 1988. The Absent Memory: The Act of Writing in Post-Holocaust French Literature [G] ∥ Berel Lang.WritingandtheHolocaust. New York: Holmes & Meier.
另一方面,若A∈csX且A?M,下證A∈clcsX{M}。事實上,對任意csO∈τ,若A∈csO,則A∩O≠?。由A?M,M∩O≠?,于是M∈csO,{M}∩csO≠?,從而A∈clcsX{M}。
Friedman, Carl. 2004.Nightfather[M]. New York: Persea Books.
Goldenberg, Myrna. 1994. Nightfather [J].BellesLettres(1): 63.
Hirsch, Marianne. 1997.FamilyFrames:PhotographyNarrativeandPostmemo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Marianne. 2008.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J].PoeticsToday(1): 103-128.
Hoffman, Eva. 2004.AfterSuchKnowledge:Memory,History,andtheLegacyoftheHolocaust[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Kopp, Kristin & Joanna Nizynska. 2012.Germany,Poland,andPostmemorialRelations:InSearchofaLivablePast[M]. London: Palgrave McMillan.
Levey, Cara. 2014. Of HIJOS and Ninos: Revisiting Postmemory in Post-dictatorship Uruguay [J].History&Memory(2): 5-39.
Suleiman, Susan Rubin. 1999. Reflections on Memory at the Millennium: 1999 President Address [J].ComparativeLiterature(3): v-xiii.
程梅. 2015. 移民“后記憶”陰影下的自我重建 [J]. 外國語文(5):20-25.
林斌. 2007. 大屠殺敘事與猶太身份認同 [J]. 外國文學(5):3-10.
呂燕. 2012. 離散族裔的創傷與后記憶 [J]. 華文文學(1):55-62.
阮煒. 2004. 子虛烏有的“后現代” [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5):65-68.
曾桂娥. 2015. 《一切皆被照亮》中的“后記憶”與猶太性 [J].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9-46.
責任編校:路小明
After “Postmemory”
CHENGMei
Many “post-” terms, especially “postmodernism”, are being questioned and subverted, which threatens the existence of “postmemory” proposed by Marianne Hirsch. “Postmemory” describes the “memory” of Holocaust survivors’ children, emphasiz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raumatic effect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By taking as examples the documentary narratives and the novelNightfatherby Holocaust survivors’ childr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postmemory, shows the failure of discursive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rvivors, whether silent or talkative, and their children, and question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thus denies the validity of postmemory.
memory; postmemory; trauma transmission; the Holocaust
I563.074
A
1674-6414(2017)04-0019-05
2016-12-05
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西方文學中的‘野蠻’敘事”(教外司留[2013] 693)的階段性成果
程梅,女,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大屠殺文學和流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