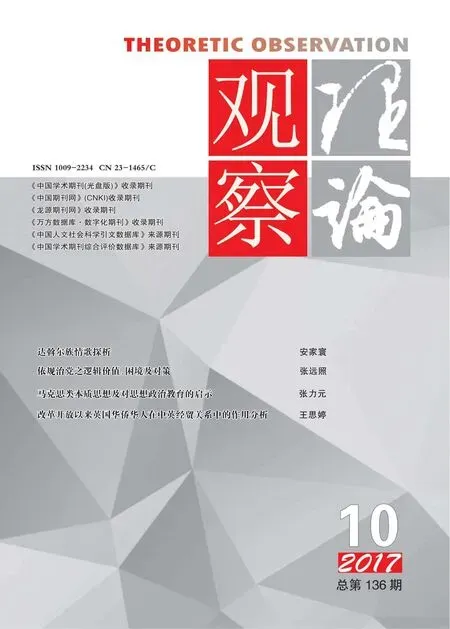簡論南京國民政府蒙地開墾政策的得失問題
張亞濤
(內蒙古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
簡論南京國民政府蒙地開墾政策的得失問題
張亞濤
(內蒙古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
南京國民政府力圖恢復中央權威,實現國家統一,強化對蒙古地區的統治力度,因此延續并發展清末和北洋軍閥政府對蒙地實行的土地開墾政策。國民黨土地開墾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對內蒙古地區社會進步具有積極促進作用,但也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消極影響。因此,我們應以史為鑒,制定并實行符合當代內蒙古地區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政策與制度。
南京國民政府;蒙地開墾;得失
一、蒙地開墾的政策制定與實施
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意識到西北地區對國家邊防安全的重要戰略地位,1932年4月,國民政府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難會議,通過《移民墾殖案》,規定“(一)移民地點為東北、西北,包含綏遠、河套、青海、西康、西藏在內;(二)移民種類為災民、冗兵、被裁政府官員”〔1〕,旨在通過開墾蒙地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來吸引移民耕種。
蒙墾方針確定后,內蒙古地區成為各路軍閥、地方當局等爭相開墾的場所。此前,張學良的東北軍僅1928至1930年兩年間就在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中旗境內丈放“東夾荒”、“西夾荒”、“遼北荒”土地共計230440坰。1929年在熱河省政府設立經界委員會,開始清理蒙地經界。1931年晉綏當局以“開發西北、充實邊防”和“寓兵于民”的名義開始在綏遠西部地區推行屯墾。
二、蒙地土地開墾政策的得與失
蒙地開墾政策是南京國民政府采取的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也必然會隨著社會進步發展而淘汰。
(一)經濟視角下的得與失
1.社會經濟局面繁榮
南京國民政府為了便于掠奪墾區糧食和牧區畜產以及進一步加大對蒙古地區的統治力度,不但獎勵開墾,甚至還與試圖侵略中國、控制遠東的沙俄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勾結,修建鐵路。從客觀角度來講,隨著鐵路在全國范圍內的修筑,蒙古地區與國內外各地的經濟交流也逐漸頻繁。
開墾帶動漢族移民的遷入,帶來了內地相對先進的農耕技術,哲里木盟等被開墾地區開始種植小麥、土豆等農作物,種類增多、改良農具、建設水利工程等均有利于種植范圍的擴大和農作物產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蒙古牧民的糧食需求,也緩解了出塞饑民的生存壓力。俄國學者波茲德涅夫游歷內蒙古時,所見巴林人已全部從事農業,而且,蒙古人還從漢人那里學會了養蠶繅絲。〔2〕(P428、255)“在游牧經濟生活之蒙民,本無商業可言”〔3〕(P267),農業的發展也不斷帶動商業、手工業、金融業以及傳統畜牧業等的發展,因此出現“蒙旗地開放愈早,其旗愈富”〔4〕(P80)的局面,即被開墾地區相對于未被開墾地區要富裕得多,蒙古族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對外交流活動增多。
同時,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在各旗縣內設立蒙租征租局,從開放地內征收每坰地每年三角的蒙租,其中六成稱為報公銀,納入國庫〔5〕(P121)。在被開墾土地上收納的租稅等大大增加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南京國民政府準備抗日提供了大量的物資支持,間接上促進了民族解放與獨立。
2.蒙地經濟可持續發展
南京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地區標榜 “欲提攜蒙民開發生產”,但卻采取大規模的四處游耕和不注重對蒙地施肥等墾種方式,再加上內蒙古地區先天惡劣的內陸地理環境與大陸性氣候的影響,導致“墾地日廣,牧場益狹,蒙官之利漸失,蒙民之生計日蹙”〔6〕(P13)的局面。 草原傳統畜牧業遭受打擊,蒙民生活艱難,畜牧業勞動力減少,這均不利于當今具有蒙古少數民族特色的畜牧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視角下的得失問題
1.社會局面穩定進步
“綏西屯墾”以前,后套土匪遍地,竊盜叢生,棒子隊到處橫行,離城五里就不太平。數年來屢經土匪蹂瞞,遂致疲憊不堪,貨棄于地,民不聊生”〔7〕(P303)。蒙地開墾政策的制定考慮到緩解內蒙古地區人地分布不均和自然災害帶來的社會問題,因而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內蒙古地區的社會安定與進步。
蒙地開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被開墾地區的社會基礎事業的進步與發展,促進思想文化的解放。張學良在東蒙古實行大規模的軍墾,加快興安區警察設立的步伐,有利于治安穩定;修筑洮索鐵路、鋪設公路,完善基礎設施;1929年在王爺廟設立東蒙學院,招收蒙旗子弟,實行分級教育,培養地方人才。
九一八后,日本分別在蒙古地區建立蒙疆政權和東三省地區建立偽滿洲國政權。國民政府在蒙古被開墾地區從事種植業的人民扮演亦農亦兵的角色,閑時耕作,戰時作戰,一定程度上為鞏固北部邊防提供大量的兵力,有利于緩解北部邊防力量空虛的嚴峻局勢。
2.內蒙地區社會矛盾尖銳
由于蒙地開墾政策深深觸及到蒙古廣大基層勞動人民最根本的土地權益,于是爆發了廣大勞動人民參與的抗墾運動,其中規模和影響范圍最大的是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嘎達梅林領導的武裝抗墾起義。同時那些在商業城鎮里破產的蒙古人更是“以干粗活、賣淫、乞討和劫掠為生”,社會階級矛盾激化。科爾沁地區敘事民歌《趕走屯墾軍》表現出蒙民對傳統草場的深深熱愛和對屯墾軍的強烈不滿。
傳統蒙古上層貴族一方面因為自身土地收益被國民政府分割含有不滿情緒;另一方面由于蒙地開墾損害了蒙古民族的土地利益,具有民族壓迫性;再加上廣大基層人民的抗墾運動帶來的壓力,1929年3月,錫林郭勒盟王公等也召開會議,向國民政府提交“維持蒙古民族游牧生計,凡內蒙未開墾之地不得藉何等名義再行開墾,其已開墾者,土地所有權仍有蒙人自主”〔8〕的強硬呈文較為充分的反映了蒙古各階層反對墾殖的普遍愿望與要求。
(三)民族關系視角下的得失問題
1.蒙漢民族文化大融合局面
伴隨著國民政府蒙地開墾政策的貫徹實施,山西、陜西、河北等蒙古鄰近地區的人民大量遷入蒙古地區,形成新的人口遷移熱潮。蒙地開墾后蒙漢兩族各種文化生活習慣不斷融合、進步與發展。正如徐世昌在《東三省政略》中所說,“蒙漢雜處,觀感日深,由酬酢而漸通婚婭,因語言而兼習文字”〔9〕(P13—15)。 同時,蒙古地區也逐步進入半農半牧階段,蒙古人開始放棄蒙古包,修筑土屋、磚瓦房、馬架子屋等;飲食也由傳統的畜牧品為主的單一飲食結構轉變為畜、農產品兼顧的多種飲食結構,開始食用小麥、拉面、粉條、紅茶、花茶等;服飾也由傳統的蒙古袍、羊皮襖等轉變為以土布制作的漢式服裝等。
漢族移民在開墾之后大多在蒙地定居生活,形成蒙漢雜居的局面,增加蒙漢兩族接觸頻率,解決蒙漢交流的時間和距離問題,深入全面吸收雙方文化,甚至雙方的宗教信仰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融合和發展,有利于消除民族間的偏見。
2.蒙漢民族各階級矛盾尖銳
南京國民政府竭力鼓吹國民黨同化蒙藏滿回等民族為一個大中華國的民族政策,即 “不分彼此,更無所謂五族之分”,只字不提孫中山倡導的“對于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不顧蒙古民族反對開墾的各項要求,強行放墾,使得中華民族不但面臨著日俄等帝國主義入侵的民族危機,還需要解決國內蒙漢民族之間的矛盾。蒙漢民族矛盾不但包括蒙古統治階層和漢族地主階級的矛盾,也包括傳統牧民和漢族移民的矛盾。
蒙古封建王公貴族通過出租自己享有占有權的土地向前來耕種的漢人收取地租等租金,給傳統游牧社會下的貴族帶來巨大利益。他們甚至利用權勢,以犧牲蒙旗共有的土地為代價,收斂財富,在各類土地中,王公札薩克私有地(即“內倉地”)穿線最早,數量也最大〔10〕。 然而由于其占領的世襲領地日漸縮小,各項封建特權和利益削弱,傳統的對土地的所有權被掠奪,再加上長期以來蒙古王公貴族揮霍浪費嚴重,花錢行賄的社會風氣盛行,因此他們對南京國民政府“既收其地,復分其租”的政策也表達了強烈的不滿。1929年3月25日至4月19日,哲里木盟各旗王公札薩克等50多人在長春開會,會議通過了致蔣介石決議書,提出“蒙旗土地惟有由蒙旗保管,蒙民享用,不得再行強制處分,以符地方自治及保障民生之原則”的要求,還向東北邊防軍總司令張學良提出一致反對在哲里木盟放墾土地的決議書〔11〕。
放墾之后的土地占有關系發生巨大變化:首先,漢族移民掌握更為先進的農業耕種技術,在土地開墾方面相對于蒙古傳統牧民有很大優勢,大多數土地都被出租給漢族人耕種,一部分牧民被迫到環境更為艱苦的地區尋找適合放牧的草地,“良場無多,蒙人游牧僅在山邊池隙之地”〔12〕。其次,由于土地被大規模的占有在數目極多的大地主手中,許多被迫由牧民轉為農民的蒙古人民也因為耕作技術差和耕種面積少等原因面臨收益微少的問題,生活貧困,蒙漢矛盾加劇。第三,南京國民政府采取剝奪蒙民的土地所有權、鞏固種地民的土地管業權的開墾方針,蒙民因此喪失了土地的贖回權,僅剩極小的收租利益。蒙漢兩族在蒙地土地占有上的地位發生明顯的變化,以至于最后出現“蒙民向外交租”的局面,“民國時期,卓索圖盟至蒙民所吃之租,均為數無幾,而向外交租者,尤居多數”〔13〕,交租的對象已轉為漢族移民地主。
(四)生態環境視角下的消極影響
南京國民政府實質上繼承了清末和北京國民政府的土地開墾政策,這一政策施行影響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當數對現今內蒙古地區的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草原土地大面積沙化。對蒙地開墾采取的一系列不負責任的墾殖方式是造成這一問題的罪魁禍首。1934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年鑒》也說:“察省地高而多大風,農民開墾,第一年收獲必豐,第二年次之,三年又次之,四年收獲很少,因為冬季多暴風,將地中細土吹去,下剩者多為砂石。”〔14〕(P57)適合在干旱地區生長的植物被大規模的挖掘,也加劇了土地沙化和貧瘠化,甚至一些不適合種植農業的區域也被當地墾務局大規模放墾,加速土地沙化進程。內蒙古現今已成為我國土地荒漠化最嚴重的省區之一,沙化土地和潛在沙化面積已經占到全區總面積的30.8%。粗放式的大規模開墾不但使傳統游牧的蒙古民族失去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也使得大量野生動物面臨滅絕的困境。草原面積大規模沙化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包括頻繁發生的和涉及面積不斷擴大的自然災害、降雨量普遍減少和水土流失現象嚴重等問題。
三、蒙地開墾政策的歷史認識
南京國民政府采取的蒙地開墾政策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內陸與邊疆地區人地分布不均的壓力,同時促進了內蒙古地區的社會發展和蒙漢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但是南京國民政府采取的蒙地開墾政策具有明顯的民族壓迫性,是大漢族民族主義發展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蒙漢民族矛盾,不利于民族團結與進步。而蒙地開墾采取的不當措施也導致了內蒙古地區現今的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蒙地開墾政策的歷史教訓是沉痛的,在當今社會發展中,處理少數民族問題,既要遵循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也要尊重和保護自然,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與進步。
〔1〕總理對于蒙藏之遺訓及中央對于蒙藏之法令〔C〕.自蒙古民族通史編委會.蒙古民族通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
〔2〕阿.馬.波茲德涅夫.蒙古及蒙古人(卷二).〔M〕.劉漢明,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3〕廖兆駿.綏遠志略〔M〕.南京:正中書局,1937.
〔4〕勞亦安.古今游記叢鈔(第 11 冊)〔M〕.上海:中華書局,1924.
〔5〕閆天靈.漢族移民與近代內蒙古社會變遷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馬福祥.蒙藏狀況〔M〕.蒙藏委員會,1931.
〔7〕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文書組.綏區屯墾第一年工作報告書〔M〕.太原:西北實業公司印刷廠,1933.
〔8〕錫盟條陳意見呈文〔B〕.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代號141,檔案號1296.
〔9〕徐世昌.退耕堂政書(卷 5)〔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10〕王衛東.1648—1937年綏遠地區移民與社會變遷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1〕長春蒙旗會議建議書〔B〕.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代號141,檔案號1206.
〔12〕蒙藏院總務廳統計科.四王子旗〔Z〕.蒙藏院調查內蒙沿邊統計報告書,1919.
〔13〕卓昭兩盟各旗差稅概略〔J〕.蒙藏周報,1930,(13).
〔14〕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中國經濟年鑒〔M〕.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1934.
K25
A
1009— 2234(2017)10— 0053— 03
2017— 10—04
張亞濤(1994—),女,山西臨汾人,碩士研究生,以近代蒙古族歷史文化為研究方向。
〔責任編輯:張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