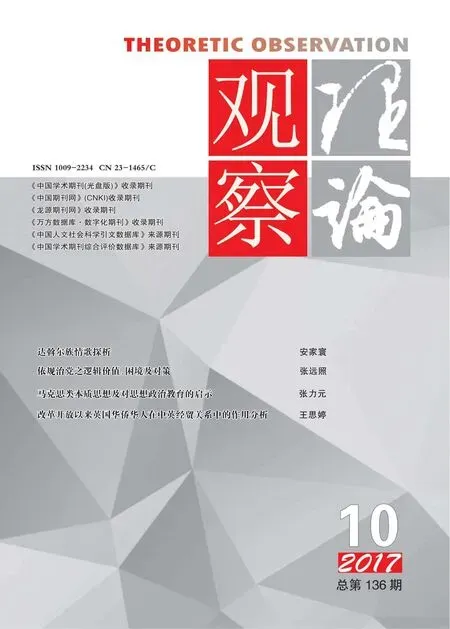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英國華僑華人在中英經貿關系中的作用分析
王思婷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華僑華人研究院,廣州 510632)
改革開放以來英國華僑華人在中英經貿關系中的作用分析
王思婷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華僑華人研究院,廣州 510632)
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愈來愈多國人走出國門,英國華僑華人也愈發引人注目。他們既是中國與英國溝通的橋梁與紐帶,也是中國國際化進程中的參與者與受益人。長期以來,中英經貿關系具有多變性和重要性的特點,華僑華人的生存發展與中英經貿關系的走向緊密相連。華僑華人需要揚長避短,在這一領域發揮自身的優勢并對中英經貿關系間接發揮積極作用。本文就改革開放以來英國華僑華人對中英經貿關系的影響及制約華僑華人在中英經貿關系中作用的因素進行論述分析,并嘗試在中英“黃金時代”和英國脫歐等新形勢、新挑戰下探索出一條“雙贏”之路。
改革開放;英國華僑華人;與中國經貿關系;影響;對策措施
隨著改革開放和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深入,華僑華人成為了我國“走出去”戰略中的重要載體。近年來,中英關系成為了我國對外交往的重要雙邊關系之一,英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提升到全球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層面的國家。長期以來,英國奉行實用主義的均勢外交政策,把現實的經濟利益置于首位,同時它也是我國企業進入歐洲市場的跳板。華僑華人在不斷變化的中英經貿關系中,如何趨利避害,把握好發展的歷史機遇,甚至對中英經貿關系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引人深思的。
一、英國華僑華人數量及結構的提升
(一)數量直線上升
據英國的人口普查資料記載,關于在英國合法居住的“中國人”的統計數,最早出現在1851年。二戰之前英國華僑華人并不多,主要從事苦力、小商販等較為低端的經濟活動,靠著“三把刀”生存。二戰后,隨著英國經濟的緩慢復蘇并需要大量勞動力,華僑華人數量也開始上升。70年代,由于印度支那半島發生動蕩,許多華人選擇再移民,移入原來的君主國——英國,這其中包括了大量香港人。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升,越來越多富有的中國人走出國門,為英國新生代華僑華人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這可視為中國人移民英國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移民數量和多樣性大幅增加。2013年,英國統計局宣布“中國公民首次成為英國人數最多的移民群體,達到60萬人”。截至2017年,這一數字已升至620674人,同比增長20%。
(二)結構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國際地位較為落后,外遷移民的主要類型為難民申請者、非法移民和家庭團聚移民,鮮有特殊專業才能。在“推拉模型”的理論框架下,他們多是被戰亂和災難“推”向海外,以求生存。1978年是改革開放的開端也是實行派遣留學生和開放出國政策的一年,此后,中國海外移民的種類發生了顯著變化。國人主動通過學習移民、商務移民、家庭團聚等形式,步入對他們有吸引力的英國。相較之老一代華僑華人,改革開放后的新生代華僑華人受過新式教育,具有國際化的觀念,熟悉市場經濟和新經濟,掌握了經營管理技巧和外語溝通能力,并在國外有較好的經濟基礎,可以視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橋梁和紐帶。
從就職行業來看,他們的選擇日漸多元化。英國華僑華人從傳統的“三把刀”逐漸轉向財會和金融等中高端職業,他們是此行業中僅次于白人的第二大族裔。教育背景方面,31%的華人有大學或以上的學位(英國白人的比例為17%);目前,中國在英國留學生超過15萬人,占英國華裔人口的32%,英國一躍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歐洲國家,因而從華僑年齡結構來看,也趨于年輕化。較高的起點、豐富的專業知識,再加上中國人勤奮上進的良好品性,使他們更容易融入英國主流社會,成為英國所需要的人才。
二、改革開放以來英國華僑華人對中英經貿關系的作用與表現
英國華僑華人在中英關系中飾演 “奔走的跨國經紀人”角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頒布了多項有關鼓勵外商來華投資的法律、法規,通過法制配套工作的完善引導華僑華人為英國企業投資中國“穿針引線”。英國華僑華人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在投資貿易上引薦英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發揮“以僑引外”的作用。2002年進入中國的約2億英鎊的外國直接投資中,約有一半是英國華人移民牽線,若沒有他們,外商投資不會達到如今的規模和水平。這其中,在外商投資的跨國公司身擔要職或與跨國公司有密切來往的英國華僑華人在引薦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近年來,在中企國外投資的大潮中,英國已晉升為“寶地”。中企在美投資,困難相對較多,堅持保護主義的領域會反對外資的競爭。相較之下,在以自由貿易為傳統的英國投資阻力較小,其核電、基建都向外國投資者開放,英國華僑華人在為“欣克利角”核電站等項目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牽線搭橋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英國中國商會與塞浦路斯商會、英中貿協就聯手舉辦了塞浦路斯“一帶一路”倫敦推介會,目的是吸引中資企業及英國企業投資塞浦路斯的相關項目。塞浦路斯是“一帶一路”沿線上的重要節點,對東歐乃至非洲市場都有輻射作用。截至2015年,我國對英國直接投資高達184816萬美元,從英國引進外資49648萬美元;2017年中英第一季度進出口為16011724元人民幣,同比上漲13.7%。在英國華僑華人的牽線下,兩國的利益環流越來越大,中英關系上升為“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步入“黃金時代”。
三、制約英國華僑華人在中英關系中作用的因素分析
(一)英國的國內背景
英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情況直接影響到英國華僑華人的生存與發展狀況。通常在政治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會激發帶有種族色彩的右翼政黨迅速抬頭。種族主義是一種具有寄生性和雜食性的意識形態,它與權力掛鉤,依附于政治運動。歐債危機后,右翼政黨將經濟低迷作為宣揚反移民思想的最佳武器。當地政府迫于壓力對華商們采取了各類強制性、歧視性的措施,給英國華僑華人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創傷。此外,英國移民政策更苛刻了,政府打擊非常規移民的態度愈加堅決。在困難時期,華僑華人總是第一批被淘汰的人,也是當之無愧的政治綁架對象,是“替罪羊”。
(二)中英關系的發展狀況
在華僑華人與近代國際關系的互動進程中,國際關系的運動始終是主導的,而華僑華人的運動是第二位的。衡量中國與華僑華人居住國國家關系的標準之一,就是看居住國政府如何對待當地的華僑華人。因而中英關系的好壞與英國華僑華人的社會地位變化是直接掛鉤的。在中英關系順利發展的時候,一切都相安無事,雙方經濟合作情況良好;但若是兩國關系發生矛盾,英國華僑華人則落為替罪羔羊,其經濟發展也將首當其沖受到負面影響。
(三)華僑華人經濟地位不高
固然英國華僑華人的經濟貢獻有所提升,但其經濟實力仍然不夠強大。在英國公布的全英1000名首富排行榜中,華人的名字寥寥無幾,甚至比印巴富翁的數量還少,且華族企業的貢獻對于英國經濟來說是不大的。英國華族企業的一個明顯漏洞就是可持續性較弱。英國華族企業大多數為家族企業,公司剛建立時,親屬關系對于公司籌集資金和提供勞動力、建立關系網至關重要。在國人眼中,重點是使家庭中的所有權永久化。如蘇氏家族的七海(冷凍食品)集團,雖然蘇氏家族與其他華族合作開展了無數企業,但本集團目前在股權方面完全受到家族控制,也尚未擴大海外市場。更糟的是,大多第二代華人都在大學里學習非常優秀,很少有人想要接管父母的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代際變化導致了家族企業后繼無人的危機。此外,英國華族企業的同質化較高,同行的競爭激烈,某個行業的雇員很快就會建立自己的企業,甚至成為他們以前雇主的競爭對手,且英國市場小,資源十分有限。歐債危機后,同行間的惡性競爭愈發嚴重,倫敦唐人街的中餐館自助餐最低時大約只要7英鎊,華商利潤微薄。若不提升自己的經濟地位,難以在兩國經貿合作中發聲。
四、英國華僑華人推進中英關系的幾點建議
(一)積極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
中英關系正值“黃金時代”,兩國在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往及合作都如火如荼,尤其是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合作將成為近年來中英關系的亮點,相信這一系列的合作會讓英國盡快走出“脫歐”的陰影,恢復經濟創傷。中英雙方在多個領域具有互補性,如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而英國公司則在項目設計、工程建設、可持續和綠色發展以及管理咨詢等方面可提供眾多幫助。英國脫歐白皮書中提到,英國脫歐后希望成為一個全球的英國,這個概念與“一帶一路”倡議有異曲同工之妙。英國華僑華人應穩穩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在推動中英關系不斷發展的同時發展自身事業。在經貿領域,英國在關稅、公司稅等方面都十分優惠,華僑華人可以推動我國企業實現國際化經營。華商較早步入英國市場,較之普通國人積累了豐富的人脈資源及經營經驗,可以為投資英國的中國企業帶來便利,降低其適應英國市場的成本,實現企業的本土化。
再者,“一帶一路”倡議剛提出時在英國也存在一些質疑甚至是抵制的聲音。英國華僑華人通曉中英文化、語音及習俗,若能很好的發揮這一優勢,在共建“一帶一路”,可以開展僑務公共外交,推動中英相互深入了解。建構主義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國家行為體在外交中扮演著更加靈活的角色,公共外交的直接目的就是影響外國公眾輿論。鮮活的華僑華人能塑造和宣揚更真實的中國國家形象,更確切、客觀地傳達“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消除英國國民對此倡議的誤解。
(二)完善和轉變企業經營模式
英國華人雖然有發展生產性企業的潛力,但很少投資研發新產品或生產優質商品所必需的產品,因而他們需要提高創新力度,實現多元化經營。此外,華族企業需從封閉的家庭體制邁向開放式。英國早已推出了三大政策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大型家族企業所有者可以考慮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以吸納更多資金擴大再生產。華族企業需有一顆開放的心態,根據自身狀況聘請精英擔任董事會和管理層的成員,這些管理者受過較好的教育有能力開發企業,利于保持企業的健康持久運轉。再者,構建先進的家族企業文化也勢在必行。華人企業家需拋棄傳統家族倫理中非理性的血緣、親緣思想,擬定公平公正的獎懲機制,以建成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的業緣、事緣理念,這樣才能提升雇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提高企業活力。
(三)國家要成為華僑華人的堅實后盾
長期以來,中國國務院僑辦為英國華商、華社搭建了許多合作交流的平臺。然而,面對新形勢、新挑戰、與老一代有別的新移民,我國的僑務政策也需與時俱進,得到進一步的完善。首先,緊扣當下英國脫歐等難點熱點問題,需正確定位英國華僑華人的生存發展環境,更新有關政策法規建設,幫助勞動力流失的中餐館和存在風險的中國在英投資企業渡過難關。其次,深入了解并立足英國現有制度框架及逐步縮緊的移民政策,引導國人理性思考,積極深入了解英國的人才需求,織出一張保護英國華僑華人的大法網。
五、結語
與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華人能夠在影響英國對華政策和中國對英政策方面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英國華僑華人從“沉默的大多數”到今天這樣活躍在兩國關系中,這一切都源于其經濟地位的改善,族裔意識的提高以及我國地位的不斷提升。不過他們仍有進步的空間,相信將來英國華僑華人在英國會繼續扮演重要的社會角色并在中英經貿關系中繼續施加影響力。
〔1〕李明歡.歐洲華僑華人研究述評〔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04).
〔2〕宋全成.歐洲的中國新移民:規模及特征的社會學分析〔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2).
〔3〕周聿峨,龍向陽.關于“華僑華人與國際關系”的思考〔J〕.現代國際關系,2002,(06).
〔4〕王曉萍,劉宏.歐洲華僑華人與當地社會關系〔M〕.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5〕Wai-ki E.Luk,“Chinese Ethnic Settlements in Britain:Spatial Meanings of an Orderly Distribution” 〔J〕.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09,(04):575-599.
〔6〕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Gregor Ben ton,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ESSENTIALIZING OF CAPITALISM:CHINESE ENTERPRISE,THE STATE, AND IDENTITY IN BRITAIN,AUSTRALIA,SOUTHEAST ASIA” 〔J〕.East.2003,(04):3-28.
F752.7
A
1009— 2234(2017)10— 0075— 03
2017— 10— 11
王思婷(1993—),女,湖南郴州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歐洲政治經濟。
〔責任編輯:孫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