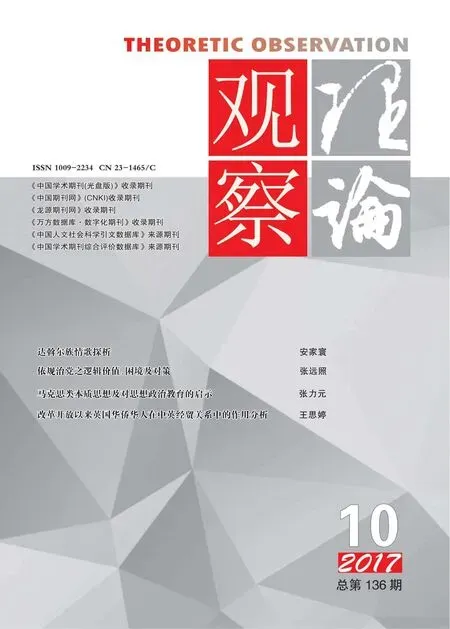從平面到立體的異形轉換是否屬于復制之法律探究
陳妮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 430073)
從平面到立體的異形轉換是否屬于復制之法律探究
陳妮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 430073)
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單一形式的復制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作品的利用。近年來,關于將平面作品轉換成立體作品的“異體復制”方式是否侵犯復制權的糾紛層出,而我國法律條文對此并未有明確的規定。立法上的不明確、學術界的爭論不一、司法實踐中的同案不同判。這種不明確不僅有礙權利人對行為的預期可能性,也有礙穩固司法權威性。因此,本文將從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兩方面分析從平面到立體的異形轉換是否屬于復制這一問題。
異體復制;復制權;文義解釋;體系解釋
一、問題的提出
2016年12月一家名為杭州大頭兒子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將央視動畫和幾家玩具廠商訴至法庭,控訴央視未經許可擅自授權玩具廠商制造、銷售動畫片衍生玩具,侵犯了其著作權的復制權和發行權。與此前的騰訊公司“QQ”企鵝案、范英海訴北京市京滬不銹鋼制品廠著作權侵權案、迪比特訴摩托羅拉案、復旦開園訴福建冠福公司著作財產權糾紛案等等頗為相似的是,這些糾紛的爭議焦點均為根據平面設計圖將作品制成立體形態是否侵犯了原作品的復制權,即從平面到立體的異形轉換是否屬于復制。翻閱我國著作權相關法律規定,對于從平面到立體的異形轉換是否屬于復制這一問題,法律條文并未給出明確的規定。在學術界中,學者們對這一問題觀點不一;在司法實踐中,則出現了同案不同判的情況。這種不明確不僅有礙權利人對行為的預期可能性,也有礙穩固司法權威性。因此,本文從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兩方面分析從平面到立體的異形轉換是否屬于復制這一問題。
二、關于世界各國和地區對復制權保護范疇的立法規定
(一)《保護文學與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以下簡稱《伯爾尼公約》)。《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1款規定受本公約保護的文學藝術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權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復制這些作品的專有權利〔1〕。 “任何方式”、“任何形式”表明可以任何物質形式,而不僅僅局限于印刷、復印、拓印、錄音、錄像等方式。“以任何方法或任何形式”這種表述涉及廣泛,《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中對包括所有的復制法進行了說明:打樣、雕版印刷、拓印、膠印和其他所有印刷過程,打字、照相復制(攝影膠片、縮微膠片等),靜電復制、機械錄制或磁性錄制(唱片、盒式帶、磁帶等),以及其他所有已知的和未知的復制過程。復制僅僅是一個用某種物質形式將作品固定下來的問題,它顯然既包括對聲音也包括對景物的錄制〔2〕。
(二)美國。《美國版權法》第101條規定:“復制品,指以現在已知或將來出現的方法固定作品的物體,通過這種物體人們可以直接或借助于器械或者裝置感知、復制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作品,錄音制品除外。”但在第106條中又規定了:“復制是將享有版權的作品制作在復制品或錄音制品中。”1990年美國專門制定了《建筑藝術作品法》,該法認為按照建筑設計圖建造建筑物也構成復制,彌補了以往立法中的不足,認可了將平面轉化為立體屬于復制。
(三)英國。英國的法律對“異體復制”進行了認可,明確了藝術作品的復制包括從平面到立體和從立體到平面的復制,但是其在實踐中并不是對所有的“異體復制”都進行保護,它的保護外延僅僅被限定在了包含有藝術性的作品上,對于根據設計圖制作印刷線路板的“異體復制”行為其是不給予保護的〔3〕。
(四)我國臺灣地區。臺灣著作權法第3條規定將平面建筑圖建造成建筑物亦屬于重制。即從現行法律文本來看,臺灣地區對于從平面到立體的異形轉換也認可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臺灣最高法院認為將平面作品單純再現,不改變其形態,能使人一望便知立體作品與平面作品之間的淵源之行為屬于“重制”,而通過建造技巧表現平面作品技術、學術之行為,因圖形著作主要在于以制圖技巧表現技術、學術,但不及于構思,如非一般專業人員,尚難判斷立體之實物系從平面而來,故自平面設計圖至立體實物之制作過程,顯系專利法意義上的“實施”行為,而非“重制”行為,“實施權”乃專利權保護之領域,卻非著作權保護之范疇,如果著作權保護及于實用物品形狀的圖形設計,無異與給予該圖形著作人使用物品常用造形之專屬排他權利,也就給予作者雙重保護,這顯然有礙于人類創作之思維、工作技術的傳播和進步〔4〕。也就是說,根據權力客體為美術作品設計圖時,構成復制,若權利客體為工業產品設計圖,則不構成復制。
(五)中國。我國2002年之前的《著作權法》第52條明確規定了“按照工程設計、產品設計圖紙及其說明進行施工、生產工業品,不屬于《著作權法》所稱的復制。”然而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刪除了此款規定,這使得從著作權法的法律條文來看,復制是否包含平面與立體之間的“異體復制”,并不十分明確。學術界對復制的保護范疇爭論不一,如沈仁干認為:“《著作權法》規定的復制是狹義的,僅指以印刷、復印、臨摹、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或者多份的行為。”〔5〕劉春田也認為我國《著作權法》只保護狹義的復制權,對于“異種復制”或“重制”不加保護〔6〕。 學者王遷、陳嬌嬌、張心全、馮曉青等認為,著作權保護的是作品的獨創性和藝術美感,對于實用功能由于其由專利法等其他法律規范保護,故而不再予以著作權法上的保護。因此有必要對客體種類進行分類,美術作品因其主要價值因素是作品的藝術創造,因而對其進行“異體復制”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相反,圖形作品轉換后,其主要作用是發揮技術功能,體現實用價值,這不屬于著作權法的調整范圍,故而不屬于復制。而其他一些學者持相反觀點:如吳漢東教授認為把平面作品轉換成立體作品或者把立體作品轉換成平面作品也屬于復制;鄭成思先生認為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主要是針對藝術作品、建筑作品的設計圖而言的,從立體到平面的復制主要是針對攝影作品的制作而言的,既然建筑物的外觀受到保護,那么施工圖紙轉變為立體建筑物之權,就要作為版權中的復制權來進行保護〔7〕。學者唐毅認為,復制應為廣義含義,通過對工程的施工和產品的生產來實現設計的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從而使作品的創作者、使用者和社會公眾在其中實現利益的分配和享有,充分利用作品的價值〔8〕。郭謙認為,實踐中《著作權法》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修訂,異體復制是產業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法律作為上層建筑,應該對這種現象給予及時規制,擴大復制權含義,將異體復制納入復制權范圍是正確的選擇。包括產品設計圖和美術作品〔9〕。
三、“異體復制”屬于復制的解釋論證
著作權制度的基本設計是通過著作權人權利的賦予尤其是經濟權力的賦予而使得作者的作品可以成為商品或服務在市場上給消費者所消費,作者因為消費者的消費而獲得經濟回報,從而實現鼓勵和獎勵創作之目的〔10〕。而其中的復制權是著作權中的基礎權利,復制是將作品由一份變成多份的行為〔11〕。由于文學藝術創作不可避免地是在前人的思想基礎上進行的,并且思想是一種主觀物質,無法確定保護時間,所以賦予思想著作權法的保護不具有可行性。也即,復制權所保護的本質內容是對作品表達的復制,而非思想〔12〕。然而復制權是以復制技術為核心設立的權利,在經歷了印刷時代、電子時代、數字時代后,復制權的保護范圍也隨著復制技術的發展而擴大。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中規定了:“復制權,即以印刷、復印、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權利。”這其中規定了我國所認可的復制方式。然而結合開篇所提到案例焦點,不難發現,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復制的方式也發生變化,從平面到立體的方式(即異體復制)是否屬于我國法律規定的復制范疇?筆者認為異體復制是屬于復制范疇。
從文義解釋來看,我國著作權法對復制方式的規定中包含了“等方式”這樣的字眼。“等方式”是一個開放性的詞匯組合,從我國漢字學角度研究,“等”既可以指該字之前所列舉的所有復制方式,也可以認為除了之前所列舉的復制方式之外還包括了沒有列舉的相同性質的方式,例如本文所述的異體復制。本文認為“等方式”應做后者理解。理由在于,復制權的本質是著作權人禁止他人復制其作品的行為,其目的是使得著作權人能夠保證市場上其作品的稀缺性,從而為將作品轉變商品銷售提供市場條件〔13〕。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新的復制方式會不斷出現,“封閉式列舉”立法方式很可能將新的復制形式排除在外,從而留下了法律漏洞,因此將其他雖未明文列舉但其行為方式在本質上與復制無異的行為納入復制權涵蓋范圍為法律的適用創造空間〔14〕。
從規范體系來看,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了針對室外的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的合理使用,對于非室外的非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的攝影、繪畫等就不能認為是合理使用的情形,在沒有征得著作權人的同意并支付報酬的前提下,上述行為就會構成對權利人著作權的侵犯。可以看出我國著作權法的這一條規定的前提是認可 “異體復制”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的,因為其對藝術作品合理使用情形的規定實際上是對著作權的一種限制,屬于侵權的例外。在討論哪些情形構成對著作權的合理使用時,前提條件是認可這些情形是侵犯了著作權的,但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等方面因素的考量,由法律規定將這些情形予以例外。故而,《著作權法》第 22條規定合理使用的情形就是對“異體復制”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的認可。雖然《著作權法》第10條對這種復制類型沒有進行明確的列舉,但是根據體系解釋的原理,著作權法本來應該是一個符合邏輯的制度體系,它的各章和條文之間往往是互相證明的,既然第22條認可了“異體復制”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第10條的規定自然不能與其相矛盾也應認可此種復制類型。
再者,《伯爾尼公約》第9條規定:“成員國有義務保護本國著作權人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行使復制權。”我國作為該公約的成員國,并未對此作出保留,則應遵循上述規定,而《伯爾尼公約》對復制權的定義采用的是廣義的復制權,因此,我國應當將從平面到立體的轉換歸入復制權的保護范疇。同時我國1992年頒布的《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中第19條規定:“本規定施行前,有關著作權的行政法規與本規定有不同規定的,適用本規定。本規定與國際著作權條約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著作權條約。”這也進一步說明,在協調國內立法與國際條約之間的條文沖突時,我國傾向選擇遵循國際條約。在本文中,也就是應將“異體復制”納入復制權的保護范疇。
四、結語
美國斯托里大法官曾這么評價:“相比其他各類在法庭上爭論的案件,版權更加接近于所謂的法律的形而上學,其特征是,至少看起來可能是如此的微妙與精巧,并且有時幾乎是轉瞬即逝的。”也即是說,版權是一種要求裁判專業水平高、專門化程度高的權利。但版權也是經濟社會中十分重要的權利之一,在知識經濟的今天,復制權的界定甚至關系到國家利益。如果這些問題法律不予以明確,都交給法官來處理,這不僅會加大司法處理難度,而且會由于不同法官對這些問題的觀點不同而造成同類案件之間的相互矛盾,這將不利于我國從宏觀上實施知識產權戰略〔15〕。因此,從法律規范的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將從平面作品轉換成立體作品的“異體復制”方式應納入到復制權的保護范疇。
〔1〕劉波林.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6〕〔14〕焦和平.“異體復制”的定性與復制權規定的完善——以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為契機〔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4,(04):119-126.
〔3〕〔7〕趙曼姿.“異體復制”的法律問題研究〔D〕.蘭州大學,2016.
〔4〕張心全.論異形轉換是否構成復制——以“平面到立體”為視角〔J〕.時代法學,2008,(04):91-96+104.
〔5〕謝乒.論從平面到立體的轉換屬于著作權法上的復制〔J〕.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3):65-67.
〔8〕唐毅.從平面到立體——對圖形作品復制方式的理解〔J〕.人民司法,2009,(02):57-60.
〔9〕郭謙.3D打印中異體復制行為之定性〔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5,(10):100-102.
〔10〕〔13〕吳偉光.著作權法研究:國際條約、中國立法與司法實踐〔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11〕吳漢東.知識產權基本問題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12〕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理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15〕殷紅艷.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權研究〔D〕.中國政法大學,2010.
0000
A
1009—2234(2017)10— 0111— 03
2017— 10—17
陳妮子(1994—),女,湖南株洲人,2016級法律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知識產權法。
〔責任編輯:陳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