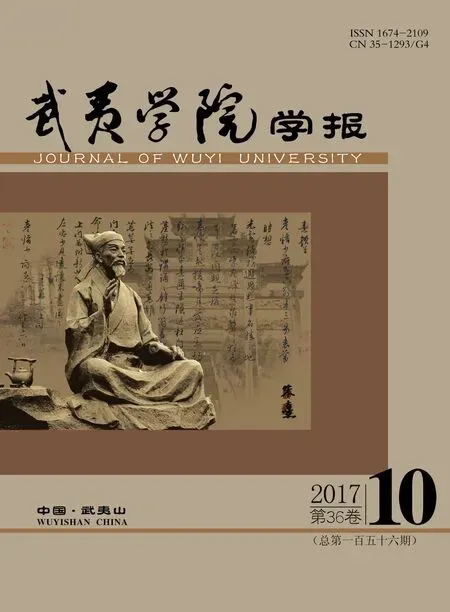敘事·回憶·創傷
——解讀《向蒼天呼吁》的創傷敘事和創傷歷史
余小玲
(福建商學院 外語系,福建 福州350016)
敘事·回憶·創傷
——解讀《向蒼天呼吁》的創傷敘事和創傷歷史
余小玲
(福建商學院 外語系,福建 福州350016)
詹姆斯·鮑德溫在小說《向蒼天呼吁》中采用了獨特的跳躍性的敘事方式和回憶性敘事的結構模式,再現了黑人群體所遭受的文化、種族和心理等方面的創傷,通過敘事、回憶和創傷三者在文本中的交織架構出“此在”和“彼在”。詹姆斯·鮑德溫強調直面創傷歷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揭示安度創傷歷史對主體成長和繼續當下歷史和生活的深層主題和意義。
《向蒼天呼吁》;敘事;回憶;創傷
詹姆斯·鮑德溫(1924-1987)的小說《向蒼天呼吁》(1953年)自問世以來,就受到廣大讀者和專家的關注,作品中展現的黑人種族和生存境遇問題、黑人的身份訴求、父子關系、黑人兩性問題和黑人宗教信仰等問題受到廣大讀者和評論家的關注。可以說角度多樣,觀點各一。因其為帶有半自傳性質的小說,小說中所采用的敘事手法也多有學者付諸筆墨論述,但文章僅僅圍繞敘事本身對人物塑造和情節推進的作用展開討論,并未把敘事和創傷歷史結合。本文從創傷寫作的角度來分析鮑德溫在小說中運用的敘事策略和回憶性敘事的結構模式如何在文本中再現和展演創傷歷史經驗,鮑德溫通過敘事、回憶和創傷三者在文本中的交織架構出創傷主體的“此在”和“彼在”,強調直面創傷歷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安度創傷歷史對主體成長和繼續當下歷史和生活具有深層的意義。
一、敘事、回憶與創傷
在歷史中,人們形成并且反映了他們和其他人的認同感、歸屬感,以及與他者的差異,可以說歷史是個體和群體觀照自我和他人的語境。傳統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即為事實,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當代理論界逐漸對傳統的歷史觀提出質疑,尤其是后結構主義思想家從理論上對歷史真相和歷史書寫都發出了質疑之聲,從而引發學界重新思考歷史和敘事之間的關系,質疑了傳統史學敘事的可信性和權威性,換言之,大寫的歷史(History)是書寫出來的無數的小寫的history構成,跟敘事息息相關,其價值判斷大于事實判斷。帶自傳體的小說可以視為一種小寫歷史的書寫,受到作者敘事角度和敘事模式的影響和塑造。隨著理論的漸進深化,學者們也逐漸從歷史文本的敘事結構或表現方式轉移到歷史認識的深處——記憶,尤其是創傷記憶。“只要記憶與‘實際發生的’經驗相關,歷史就仍然是對集體記憶中這種經驗因素的一種言說。”[1]可以說歷史的書寫也是在修辭地進行的,包含著虛構和人為的因素,同樣也與某一群體人群的記憶相關。
“心理創傷是個體對某一事件或持續狀況的特殊經驗,這種特殊經驗導致個體失去統整其情緒經驗的能力遭淹沒......讓人感到害怕死亡,消滅,毀壞,精神異常等。”[2]
“集體創傷指的是對于社會基本紋理的一擊,它損害了將人群聯系在一起的扭結,破壞了普遍的共同感受……不知不覺地潛入了為其所苦者的意識里……人們逐漸了解到社群不再是有效的支持來源,自我的重要部分消失了……“我們”不再是廣大的共同體里有所連結的組合,或是有所關聯的細胞。”[3]
以上界定可知,對于創傷的研究重點不在于創傷事件本身,而在于主體在遭遇創傷之后的反應和措施。過后,當主體回憶或者逃避面對創傷事實時,回憶就成為創傷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創傷、記憶和敘事被放置到同一個顯微鏡下進行探討和研究,學界的質疑聲引發了思考,簡單的面對歷史真相已經成為過去式,當下如何感知過往的歷史,又該如何去擁有一個真實的歷史,并且如何背負沉重的歷史在當下生活,成為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記憶被推到了探討的前臺,成為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的關鍵因素。“回憶成為建立個人和集體身份認同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為沖突也為認同提供表現的場所。”[4]在記憶中,創傷不僅發生過,而且成為建立過去與現在的紐帶,過去的歷史是在各自當下的基礎上的一個自由建構,主體在“此在”中不斷利用回憶和記憶的敘事來直面缺場的“彼在”,并連接二者,在此過程中,有沖突爭斗,更有認同協合。
鮑德溫小說中的人物在敘事開始時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有肉體的,有精神的,有心理的等,現實生活的危機迫使他們回顧總結過往,與此同時黑人的歷史也一步步地在讀者面前展開。鮑德溫筆下的人物皆是背負創傷而生存的人們,在他們的一生中經歷了種種災難,痛苦等創傷事件,使得小說的主人公與其周圍的人和社區的關系變得疏離,溝通難以進行。同時他們都希望通過對歷史的追溯,來尋求觀照現實存在的意義,讓詩和遠方繼續進行。總之,作品中的黑人和整個黑人群體都面臨如何面對創傷歷史的問題,并在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展演創傷,難以逃避創傷所帶來的種種影響,因此必須和創傷達成和解和安度。
二、跳躍性的敘事——規避創傷
當代創傷研究已經指出創傷與敘事之間的緊密聯系。創傷是過去發生的創傷事件對受創主體產生的影響,使得受創主體在潛意識中形成一種心理防御機制。因此敘事就成了對創傷事件的回顧和記憶再現的方式之一,在這一過程中,創傷主體在回憶中重新構建完整的創傷事件時,因為難以直面,就有可能有意識地否認,壓抑或規避創傷體驗,從而和現實生活達成和解。因為內心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使得小說的人物在敘述的過程中就體現了敘述的不可靠性及其背后的敘述倫理。
在《向蒼天呼吁》的敘事中鮑德溫在“說”和“未說”,“寫”與“未寫”之間自由切換,來傳達一種不確定性和分裂性,使得讀者和作品的人物同時都產生一種認知的搖擺,而這些與作品中跳躍性的時空敘述和多變鏡頭緊密相連。小說分為三個獨立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支離破碎式地各自在自己的回憶中敘述遭受的創傷事件和體驗,在回憶創傷事件時都有意識地否認和轉移真實的創傷體驗,并且不斷使用 “當下”的視角來看待過去的歷史和記憶,有意識地粉飾和美化,使得創傷事件本身的暴力性和殘酷性被削弱消弭。結果是,這種無法正視和規避創傷體驗,使得主體在現實生活中更是感到難以排遣的主體分裂感、破碎感和孤獨感。
以時間為指向的記憶模型強調了時間的非持續性,具有遺忘的優先性和回憶的不可預測性。《向蒼天呼吁》被歸為小說,但在敘事進程中,采用了破碎的時空拼接法,來展演主要人物和其群體所遭受的不堪回首的歷史經驗和記憶。在時間維度上,采用的是非線性的敘事時間,作品描述了從南北戰爭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黑人的歷史和共同的遭遇,在小說敘事的時間時態上,頻繁插入引語、對話、典故等,不斷在現在時和過去時之間切換,在記憶和經驗上切換,這主要體現在作品人物對創傷經歷的閃回、幻覺和夢境上。在空間維度上,作品的人物從南到北,從鄉村到城市,物理空間數度異置,這種變化性就形成了一種搖擺性和不確定性。小說中創傷的夢魘總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看不見任何線性的進程和任何終結,正好與文本中體現的生活破碎性和身份認同分裂障礙相契合。
實際上,變化的是時間和空間,不變的是人物遭遇的來自歷史、族群和個人的創傷體驗,以及由此產生的身份缺失和主體意識的分裂。顯然,創傷就像烙印一樣深深地印在每個黑人的靈魂和內心,但是他們卻通過自己的方式,來拒絕和規避創傷。割裂了現實與歷史的聯系,越是想要逃離創傷的過往,越是難以擺脫這一夢魘。小說由三個獨立又相連的部分拼貼而成,看似分離,實則緊密不可分割,共同點是運用清晰的跨越時間性的日常記憶,來表征無時性的創傷記憶。尤其是小說的第二部分,通過三位敘述主體佛羅倫斯,伊麗莎白和父親加柏利的回憶來展現了黑人遭遇的種種創傷。這一部分鮑德溫運用倒敘的手法,采用第三人稱敘述,時態上現在時和過去時相混合,對過去的敘述都附著著現在的視角,可以說敘述主體在敘述故事事實時,不斷的加入價值判斷,不斷辯解和粉飾,這種敘事聚焦方式都有可能導致 “不可靠敘述”。小說中弗洛倫斯通過回憶和禱告的方式來追憶她六十年生活,有母女關系,有兄妹關系,有姐妹情誼,有婚姻關系。在敘事中文本之間產生了“互文性”,插入了引語、典故,以及現在時態的“對話”,主體被投放到在巨大的互文性話語空間中去,所有的這些文本都是為了對過去創傷體驗按照主體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和編輯,以適合敘述主體的價值系統。另一個主人公伊麗莎白在新的家庭生活中不斷的追憶前夫的種種過往,她們的記憶都在閃回又閃出,卻沒有形成連貫性的記憶,有時候甚至出現遺忘的間歇,而且在敘事上不斷的插入當下生活的場景,如禱告,歌聲,使得創傷的延展模糊支離了原來的情景,從而在創傷記憶和敘事創傷記憶上形成了不對等現象。
三、回憶性的敘事——創傷的展演和安度
“意識總是可以延展的,而且可以延展到過去的時代,它可以把同一個人的時間上相去甚遠的存在和行為聯合一起。這個目前正在思考著的人的意識所能聯合的東西,正是組成這個人的成分,并且和它一起而不是和別的什么構成這個自我。”[1]和笛卡爾思考式的主體不同,洛克式的主體是回憶式的,他認為自我并不具備客觀的延伸和延續性,必須借助意識,也就是借助記憶或回憶獲得生命的過去階段,并且將其整合到自我當中。而回憶首先意味著反思,在時間的河流中自我觀察,回望自己,自我的分裂和化身雙重的自我。回憶、反思和對話是創傷展演和安度過程中的關鍵因素。在小說中,主要人物通過回憶或記憶的方式,不斷的正視創傷的歷史,并且在不斷的回望中展演創傷帶來的影響,同時也在不斷反思和批判,審視了自己在創傷事件中的倫理選擇,意識到對他者造成的傷害,放棄了作為受害者的道德優越感,并從封閉走向用“愛”來擁抱他者,從而安度了創傷。
回憶性的敘事結構是鮑德溫在小說中采用的主要手法,再現了非裔美國人遭受創傷的歷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在回憶中,小說中的人物規避和粉飾創傷經驗和歷史,并未使她們擺脫歷史創傷對她們身心造成的種種影響,反之,不愿正視歷史和創傷而產生主體的碎化,身份認同的危機,使得小說人物和黑人群體無法活在當下,可以說,在創傷歷史經驗的認知上遭遇了困境,實際上,這正是創傷的展演,過去的經驗像幽靈一樣時刻侵擾著現在的生活。在奴隸制時期,第一代非裔美國人蕾切爾與兒子的隔閡,與丈夫的疏離以及與女兒觀念的沖突;在大遷移時期,第二代非裔美國人伊麗莎白遭受的經濟,種族和性別上的壓迫,對幸福家庭的愿景的破碎;在哈萊姆時期,第三代非裔美國人面臨的宗教困境和在都市生活的身份認同危機。“代際間幽靈是典型的內并創傷。家族隱秘的創傷在后代的心理空間中重復表演,形成作為創傷間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5]這種創傷的記憶在代際間傳遞和延展,雖然歷史時期不同,造成創傷的原因不同,但創傷在現實生活的表征相同,黑人個體內心中都充滿憎恨,憎恨自我,憎恨他人,因此他們都與他人隔離,與群體隔離,在痛苦的牢籠中不能自拔。但是鮑德溫通過回憶性的敘事結構,不僅僅是為了揭示批判創傷歷史根源,更為了喚起黑人的反思和審視,并做出積極的倫理選擇。
鮑德溫在小說中運用帶有狂歡化特質的 “救贖”的敘事手法,為主要人物提供了一個梳理記憶的場所以及建立和外界聯系的機會。“只有開始懺悔的時候,精神才開始真正的存在。”[6]教堂是狂歡化的場景,展現了狂歡化的精神訴求。小說的第一部分“第七日”就展現了狂歡色彩的禮拜儀式,在圣壇前,默默的祈禱是人物的內心獨白,在狂歡化的世界中感受思想感情的裂變,父子關系的否定與肯定,約翰對自我夢想生發與滅亡的雙重體悟,伊麗莎白對弗蘭克情感的由恨到愛和懷念……既是人與神互文性的對話,也是個體對歷史和現實的和解對話。小說的結尾,主要人物通過“愛”,尋回了姐妹情誼,手足情誼和父子情誼,同時融入到美國社會文化中。黑人個體得到成長并尋回失去的身份。同時鮑德溫也提出了他的倫理選擇,他認為“認知罪惡的關鍵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我們內心中拒絕去了解他人,拒絕接受差異性,拒絕愛人愛己。”[7]
詹姆斯·鮑德溫在小說《向蒼天呼吁》中不斷將敘事、記憶和創傷三者交織在一起,來批判非裔美國人所受到的歷史、文化和種族的創傷,同時反思在遭受創傷和面對創傷時非裔美國人的倫理選擇和訴求。小說采用了獨特的跳躍性的敘事方式和回憶性敘事的結構模式,表達了只有正視創傷歷史和經驗,審視自己在創傷中的行為,并與他者建立關系,用“愛”擁抱彼此,才能安度創傷,使生活指向詩和遠方。
[1]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M].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I,103.
[2]蘇忱.再現創傷的歷史[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16.
[3]ERIKSON K T.Everything in Its Path:De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BuffaloCreek Flood[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6:153-154.
[4]ANTZE P,LAMBEK M.Tense Past:Cultural Essays in Trauma and Memory[M].New York and London,1997:VII.
[5]陶家俊.創傷[J].外國文學,2011(04):117-125.
[6]宋春香.他者文化語境中的狂歡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11.
[7]余小玲.弱者的呼喚:解讀《向蒼天呼吁》中的身份認同[J].太原大學教育學院學報,2010(03):68-72.
Trauma in the Narrative and Memory in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YU Xiaoling
(English Department,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Fuzhou,Fujian 350016)
In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James Baldwin adopted the unique leaps of narrative and the structure of memory narrative to represent the cultural trauma,the racial trauma and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that the black community had suffered.In the context combined by narrative,memory and trauma,James Baldwin strongly stressed the necessity and the possibility to confront the trauma history in order to reconcile with the past trauma and to welcome the new future.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narrative;memory;trauma
I106.4
A
1674-2109(2017)10-0048-04
2017-03-02
余小玲(1981-)女,漢族,講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和西方文論研究。
白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