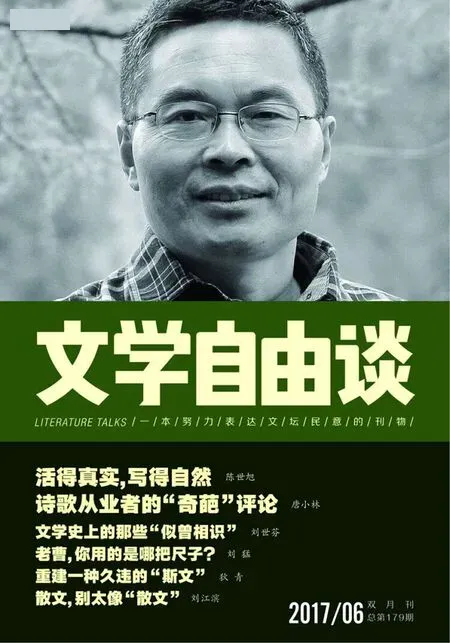當風雅遭遇風塵
川 湄
當風雅遭遇風塵
川 湄
經典作家寫的文章,大抵不會使人失望。最近重讀了陳忠實十幾年前的散文作品,《沉重之塵》中的一段話,我覺得挺有意思——
官辦的縣志不惜工本記載貞婦烈女的代號和事例,民間歷史不衰傳播的卻是蕩婦淫娃的故事——這個民族的面皮和內心的分裂由來已久。我突然電擊火迸一樣產生了一種藝術的靈感,眼前就幻化出一個女人來,就是后來寫成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里的田小娥。
記得當初讀這段話時,我感興趣的是與《白鹿原》的創作過程有關的信息,而此次再讀,我忽然注意起“蕩婦淫娃”這四個字了。我揣度著,這四個字只能出自男作家之口。不論是民間話本,還是文人小說,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當然大多數都是男性視角下的男主人公),應該都是風雅不如風流——不風流何來韻事?但往往,韻事的最后卻蕩盡浪漫的云雨,淋漓現實的風霜。
湊巧的是,我最近又讀到了“女性主義作家、詩人”海男的一篇舊作,注意到這位女作家對待妓女的態度別有一番意味——鮮有浪漫,特別現實:
妓女的生活原則是墮落——用無窮無盡的肉體和心靈的墮落來證明她們的肉體是可以毀滅的,如果用圍墻來禁錮她們,那么這群已經習慣用肉體來換取金錢的婦女無疑會逃跑,因為她們喜歡享受鉆石上的眼淚和悲劇般的顏色中徒勞無力的呻吟,她們喜歡金錢甚于喜歡男人和女人。在此,D告訴我妓女們攀越圍墻逃跑時,我想起了她們墮落的唯一信念:那就是悖離道德和律法,悖離純潔和高尚,因為她們追求“自由”,當她們脫衣服時,身體已經滑落在危崖之下,她們脫衣服的方式很快……(海男《頹廢時期的生活方式》)
看這語氣,多么像一個與獄警同仇敵愾的人啊!我對于她的語態忽然警覺起來,我很意外也很抱歉地,讀出了她靈魂中的“小”來。我實在無法想象,作為女性作家,她對于妓女這樣的特殊群體,不是跟我一樣滿懷同情,而是人云亦云地表示輕蔑。她居然批評妓女脫衣服的方式!
我幾乎不敢再讀她寫的那段文字,因為我不能對那種措辭無動無衷。一股悲哀的情緒襲擊了我。這悲哀不是為妓女悲哀,不是“哀其不幸”的悲哀,而是為身為女作家的海男悲哀,是為那高高在上的道德優越感而悲哀。我感覺,她走過了生活而不是走進了生活,她冷眼旁觀而不是換位思考,不曾顧及妓女作為人的感情和尊嚴。
海男的那段話,寫的是自己對妓女的想象。1993年,她去看望滇西勞教所三百多名正在接受勞動改造的女犯,聽獄警說這些女犯都是妓女,常常越墻逃跑卻都沒有成功。女作家于是有些激憤起來了,這種激憤在文字里面也有被加強的可能。
寫作當然要有充沛的感情,但有時候,作家必須首先運用理智。一個寫作者,至少要意識到寫作的責任,要對社會人心進行干預。三百多名妓女,是一個群體性存在。作家當然也不能僅僅對她們表露一下同情心,或者大肆渲染同情心;誰也沒有資格同情別人。但是作家至少要想到,現實中的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會有它的天然缺陷,需要我們深入考察。三百多名妓女嗎?她們并不因為人數多就具有破壞鐵墻似的制度或者秩序的能力,她們是在公眾面前喪失了話語權的邊緣人甚或犧牲者,無力逃出拘囚她們的一道又一道高墻。
作家如果沒有歷史的眼光,就容易陷入狹隘和狂妄。妓女的存在是一個歷史問題,歷史名人管仲被稱作“世界官妓之父”,而現代中國因為男女比例失調等因素,還有呼喚妓女合法化的聲音。有人說,妓女畢竟也是一種職業稱謂,從業者并沒有不勞而獲,世人為什么不能夠對這個職業有一點寬容心呢?曾經有報紙記載,一位進收容所的姑娘對警察說了一句話:“找不到工作,擺個攤你們又要沒收,不干這個干什么呢?”圣徒的靈魂渴望天堂,妓女的靈魂只渴望人間。她們受盡屈辱,茍且偷生,大多只是為了活命。
有生命然后才有道德尊嚴。古今中外文學名著中很多妓女形象,都是有血有肉、美麗善良的,有的還是品格杰出的女性典范,有的甚至是出色的詩人詞人。優秀的作家并不對妓女進行道德審判,反之,托爾斯泰的《復活》竟讓一位妓女對一位貴族進行道德審判,而《復活》的偉大就在于,它表現了一種幾乎是不可企及的人性的偉大,一種敢于自剖和反思的文化品格。
好作家應當有自剖和反思的能力。當有些人不得不像動物一樣謀生的時候,我們應當質疑人類社會的道德水平。如果人世間有一些人生活悲慘,那么其他一些人是不是應當受到心靈的拷問?但是,我們不能拷問妓女!生為弱者,這個世界已經虧待了她們。莫言說過類似的話:有兩百雙鞋子的女人是有罪的。他說出了社會的不公。盡管他只是說出,但他言說的立場,對于弱者是一種支持,對于缺少同情心的人是一種警醒。除了上帝,沒有誰可以高高在上,杜絕世俗生活的損害和玷污。他人的痛苦之中有你的痛苦,他人的罪孽之中有你的罪孽。妓女只不過是為了活命而犯下罪孽,作家怎么可以炫耀自己活著的高尚,而蔑視妓女存活的卑微?
作家不是上帝,他的心不是用于仲裁,而是用于感動。作家不能在作品中強調自己的道德優越感,或者進行粗暴的道德判斷,甚至自以為是地對弱勢群體進行道德訓誡。作家當以勢利眼為可恥,以同情心為可貴。作家要能理解人的困境,撫摸世人的創口,體恤世人的悲哀,體現人道主義情懷。優秀作家能把特殊境遇下的個體表現得可親可近:生而為人,誰自甘墮落到人所不齒呢?作家要表現弱者的生命力和精神力。妓女越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她們作為人的本能的體現,因為豬圈里的豬是不會冒險越獄的。誰能把墮落和反抗的妓女,放在道德的砧板上細細地砍呢?在社會對妓女進行殘酷的生存拷問的緊要關頭,如果道德能給妓女以光榮的生路,她們何嘗不愿意選擇高尚和純潔的生活呢?假如作家粗暴地踐踏妓女的感情和尊嚴,那就是想當然地認為妓女賣淫都是為了快感。作家不能貢獻社會的公平,但或許可以貢獻一點良知和同情,這是寫作者最基本的思想立場。偏離了人道主義的核心軌道,作家就會滑入可笑復可悲的境地中。
《那些人那些事》
王國華著 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
全書以“帝王們”“將相們”“文士們”“百姓們”四輯分列,從中國古代野史筆記中挑選出趣味性強、曝光率較低的人物,一一進行解剖,角度新穎刁鉆,寫作方法別具一格,篇幅短小而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