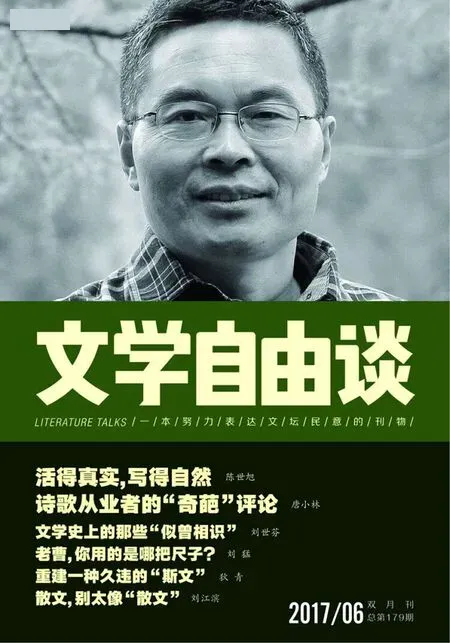閱讀的懲罰
[美]江 嵐
閱讀的懲罰
[美]江 嵐
我家鄰居,猶太裔的Kala是一位小小學老師。
所謂“小小學”,是在經濟寬裕、辦學和師資條件都比較好的學區里,專門為五到七歲的孩子們設立的獨立校園。美國孩子在小學階段的教室和班級是固定的,午餐和餐后休息時間也統一,天氣好的時候,孩子們會到戶外活動。戶外活動場地有老師、教工和家長志愿者監護,但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年幼的孩子們被大孩子欺負,保障他們的安全,便有了這種和二至五年級分離的“小小學”的設置。
小學老師們除了體育之外,各科目教學一把抓,從英文、算術到繪畫、手工,都在自己的專屬教室里完成。Kala便是這樣一位堪稱“十項全能”的小小學老師。她的教學態度之認真就不必說了,對學生要求之嚴格,有時連我也驚詫。
比如那天她說,午休回來上課不到10分鐘,班里有個小男生舉手要求去上廁所。她當然不能不同意,但是,這個孩子只顧貪玩,沒有利用好午休時間來處理個人私事,卻必須被懲罰。
沒有規矩難成方圓,Kala有她的道理。于是我問:“怎么懲罰?你又不能學我們中國老師,打他的手掌心。”
“罰他面壁啊,”Kala哈哈大笑,“接下來我們全班的閱讀時間里,他只能獨自坐在角落里,不得和我們一起看書。”
閱讀,是一旦犯錯便不能享受的賞心樂事!這才是有原則有智慧的好老師呢。既給了這個小男生一個有形的教訓,又為他以及全班孩子無形地強化了閱讀的重要性與趣味性,我簡直要佩服她的手段高明了。
在美國的教育系統里,像Kala這樣的老師并非鳳毛麟角。培養學生們的閱讀習慣并不是教學大綱里明文規定的內容,可絕大多數老師都會自覺地把這一點融入他們教學的過程,用各種形式鼓勵孩子們多讀書。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被培養出來的,他們深深懂得,閱讀乃是一種技能,一種良好的學習習慣。文科知識必須經過精讀泛讀的積累自不必說,數理化等等其他各學科也必須經過閱讀理解才能通向應用。
至于廣泛閱讀幾乎是滋養個人綜合素質最重要的養分來源,早已無可爭議,人所共知。書中或許不見得真有顏如玉,那些字詞句也不見得真能換來黃金屋,卻必然存在于一個人的氣質和胸襟里。然而對書籍的喜愛并非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生理性反應,閱讀完全是后天的習得行為。博覽群書的結果需要天長日久地堅持不懈才能逐漸顯現,因此特別需要成人的世界有意識地去熏陶,幫助孩子將閱讀養成一種習慣,生活習慣。在這一點上家長的責任更重,甚至于更重要,因為這個熏陶的過程早在孩子學齡前就應該開始了。
前年夏天,幾位到中國講學的美國教授要從南寧乘高鐵去桂林。當天的一行人中,有男有女,有中有洋,年長的六十余歲,兩名教授同事的孩子還是高中生,都不到二十歲。到了高鐵站候車室,廣播通知我們這一班車將晚點半小時。大家聽了不約而同,順手把小行李箱放平坐下,各自掏出一本書來讀。
這就是習慣。公園的草坪上,地鐵的車廂里,周末的圖書館,隨時可見讀書的大孩子或聽大人念書的幼兒,閱讀作為一種成了自然的生活習慣,是美國大眾閱讀量之大、涉及層面之廣、能夠居于世界前列的最重要原因。問題在于,這種習慣是怎么養成的呢?
閱讀的最初起點當然是睡前故事。我們那個經驗豐富又有權威的德裔兒科醫生早就指導過,讓孩子的日常生活作息時間相對固定,是培養他們心理安全感的第一步。從我來說,我家兩個孩子從八九個月大起,每天晚上八點半到九點之間洗澡,九點到九點半之間講故事,講完故事睡覺。
小娃娃聽故事,聽著聽著就會選出自己最喜歡的那一本,讓你反反復復講,有時一個晚上要講無數遍,講到書都翻爛了,又買一本新的———肯定不少媽媽都有過這種被逼到瀕臨抓狂邊緣的講故事經驗——可是還得再繼續講啊。其實這時候孩子對故事的內容也已滾瓜爛熟了,干脆讓她講給我聽,自己躺在一邊姑且閉目養神。盡管還是同樣的句子同樣的詞匯,不識字的孩子奶聲奶氣地煞有介事,總要比自己強壓著無奈又無聊講下去感覺好得多。
然后她們長大了,學會認幾個字了,講故事變成講書,還是每晚半小時。然后,我家先生轉往加州工作,我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又恰逢調任新職,每天忙得恨不能雙腳都放到書桌上干活兒。五歲的妹妹放了學,全靠十二歲的老大去接。兩姐妹餓了,自己胡亂吃些點心充饑,我時常到晚上七點多才能回到家。等吃完飯,她們就該上樓去睡覺了,我自己又埋頭干活兒。
這一折騰,不僅再也難有講故事這回事,我和她們姐妹甚至幾乎沒時間在一起。這種“在一起”,倒不是一定要做什么或聊什么,而是親親熱熱地體膚相親。親子之間,先要有孩子幼年時期身體的無距離,才會形成將來孩子們長大以后彼此心理上的無距離。我知道,自己必須想出一個有效解決現狀的方案。
思來想去,我把八點半到九點改成了我們的讀書時間,讓她們姐妹九點以后再上樓洗澡睡覺。
從此,每天晚飯后半小時,我不洗碗不接電話,我們母女三人擠在一張沙發上,各看各的書。她們看什么,我不干涉;是不是能看懂,有沒有感想,我也不過問,我們就是各自找一個最舒服的姿勢,很簡單很純粹地擠在一起,看書。我對她們唯一的要求是只能看紙質書,而不能看“電子書”。我認為一個人對書籍的喜愛,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捧在手里的紙的質感,來自于一頁頁翻過的細響,以及書頁間若有若無的油墨的味道。
當然,我的這種“認為”不無迂腐的嫌疑,所以后來的某一天,我終于遭到已經升入初中的老二的質疑:“為什么,媽媽?為什么不能看電子書?!”
“沒有為什么,”我在沙發里翻一個白眼。“Because I said so.(因為我是這樣說的。)”
然后我們的讀書時間繼續,各自捧一本由我定義的“書”。
也有媽媽們憂心忡忡地問過我:你就不怕孩子們看了什么壞書?哎呀呀,書海里還是開卷有益的多啊,姑且給我們自己一點兒信心吧,自己雙手養大的孩子,哪里這么容易就無聊到去搜尋“壞書”來讀?還有,要不要他們寫讀后感?要不要摘抄做筆記?要不要背誦?……這些其實都是“怎么讀”的問題。在這類問題上,姑且給孩子的智力一點兒信心吧。只要閱讀的習慣成了自然,他們遲早會明白應該怎么去讀的。
再然后到了現在。老大上大學住校了,老二上了高中,我自己時常在國內講學,我們母女的讀書時間無法按常規持續了。但老大每周往返于家里和學校,隨身的包里總有一本書;老二有時聊起的一些作家,連我都不大知道了——她們的閱讀習慣已經養成,我的任務也已經完成。
而且,她們那些越來越多的小秘密,越來越復雜的青春的心事,我都一清二楚,這也算是過去近十年來每天晚上那半小時閱讀帶來的另一方面成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