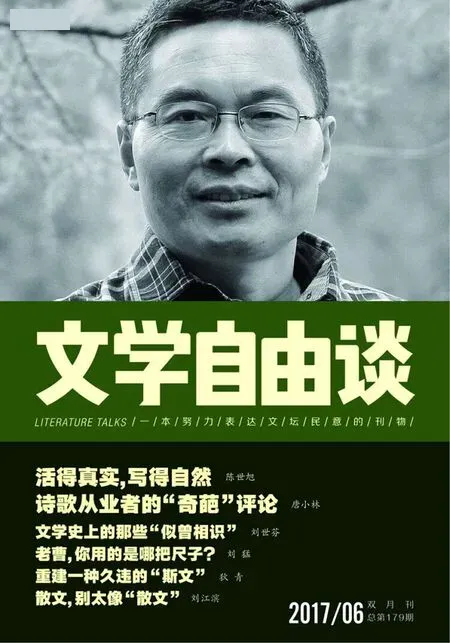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陳忠實年譜》引發的思考與期待
陳紅星
《陳忠實年譜》引發的思考與期待
陳紅星
如果說,2016年出版的 《陳忠實傳》(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評論家、作家邢小利關于陳忠實一生個人生活和文學活動的宏觀總結,那么2017年出版的《陳忠實年譜》(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年譜》)則是其關于陳忠實一生個人生活和文學活動的微觀展示。它將是陳忠實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進一步了解陳忠實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閱讀《年譜》之前,我就是想通過了解這位當代著名作家的日常生活細節,尋找它們與其文學創作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再次豐富此前我對于他的認識。我想了解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更為真實的陳忠實,在這樣的參照下,我們也許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偉大和永恒。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幾個令我頗感興趣、也令我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一、關于譜主本人
1.對于寫個人傳記的接受過程
關于寫自己的傳記,陳忠實有一個逐漸接受認可的過程。在《年譜》里,邢小利詳細記載了其發展脈絡。
在2002年3月13日到2003年4月1日這一年多的時間里,陳忠實的態度似乎并沒有什么改變。那么在此期間,陳忠實認為對他影響很大的一些事,到底是哪些事,這是讀者最想知道的。也許限于具體的歷史條件和人事關系,一些人和事只能留待將來去說;我認為,這是生活本身的要求和藝術。而到了2009年12月17日,陳忠實打電話給邢小利,說同意讓邢寫他的評傳,并強調了兩點:“多寫與創作有關的,不要關注那些尿的多了還是尿的少了那些瑣碎事”;“放開寫,大膽寫”。這時的陳忠實已經進入花甲之年,對于人事和世事應能以平常、平淡的心態來看待,但我們可以看出,他更關心更在意的還是他的文學創作,而不是對于個人的功過褒貶。他希望將一個真實的陳忠實留給世人。這大概可以視作陳忠實人格風范的具體表現吧。陳忠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文化符號,如同他所樹立的“墊棺作枕”的創作高標一樣,他的這種謙遜謹慎的人格風范,為我們當代及后世的作家樹立了一面鏡子,成為作家們做人行事的一種人格參照。
2.對文化、文學發展的支持
《年譜》中記載,2013年6月,北京人藝在西安演出話劇《白鹿原》,陳忠實買了3萬元的票贈送給西安有關人員。這讓我頗為吃驚。3萬元,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絕對不算一筆小數目。陳忠實有此胸懷,實屬難能可貴。此外,由陳忠實出資提供獎金的“白鹿當代文學編輯獎”的壯舉,則更為不易。這兩件事所體現出來的遠見卓識和深遠意義,已非具體的金錢多少可以衡量。
作為參照的是,《年譜》提供了陳忠實每一人生階段的具體工資狀況,我們從中可以發現,正如陳忠實自己所言,他屬于中農或者下中農。陳忠實的經濟收入固然非普通的工薪階層可比,但是他為文化、文學的發展助一臂之力的事實和意義,卻不容置疑,也不容忽視。這是陳忠實留給后人在對待文化文學活動時的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眾所周知,文學活動,其本質上是一項系統性的社會活動,除了作家的主體作用以外,它的發展進步還離不開各方面物質力量的大力支持。
3.日常生活中的謹慎與堅決
從《年譜》的相關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社會名人的陳忠實在日常生活和文學活動方面的謹慎,在自覺維護個人公眾形象方面的小心,也可以看出他內心深處極強的自律意識。在做人原則方面,陳忠實表現得非常的堅定。陳忠實的小心謹慎和堅定不移是辯證統一的,這兩者本質上都體現了他做人行事的根本準則,也體現了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真實性的一面。人們尊敬愛戴陳忠實,不僅因為其經典巨著《白鹿原》的深遠影響,更重要的原因還是感佩其人格魅力和道德風范。
4.陳忠實晚年深刻的反思意識
《年譜》中記載了陳忠實對自己人生的三次重大失敗的回顧,和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的深刻反思。亞里士多德說,所謂反思就是“對思想的思想”。個體都是歷史的參與者與制造者,誰也無法站在歷史之外,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看待和審判歷史。陳忠實沒有把自己作為“文革”的受害者,而是作為這一段歷史的參與者來看待,這表現了他對歷史的深刻反思的精神。只有對個人的歷史進行清醒的反思,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
陳忠實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那么他也就具有人性的弱點,也就會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犯一些多數人會犯的錯誤。難能可貴的是,同一些從歷史中走來而依然執迷不悟的人相比,陳忠實在人生晚年認識到了自己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所犯的錯誤。我想,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人的存在狀態。
5.其他趣聞逸事
《年譜》中記載,陳忠實特別愛聽陜北民歌《上河里的鴨子下河里的鵝》,聽了后常常會特別感動。陳忠實為什么喜歡聽這首歌?他是用這首歌懷念上世紀80年代初在車上歪頭唱它的小兄弟路遙,還是有感于它所表達的農村男女之間質樸的愛情?這顯然是一個饒有趣味的作家心理研究話題。
《年譜》記載了陳忠實對社會生活的一些個人言論,記載了他關于父子之間的責任和義務的認識,表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在他身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這些都會成為后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在我看來,一個作家流傳下來的逸聞趣事和生活佳話,都是其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常常從側面傳遞著作家的性情和旨趣,也默默地滋養著那些喜歡他的讀者的精神世界。
二、關于作者和譜主
在《年譜》中,僅正式提到的陳忠實給作者邢小利打電話的次數,就有20次之多,由此,讀者可以窺見兩人聯系之密切、關系之親近。讀者要了解邢小利和陳忠實的關系,《年譜》中的記載就是最好的依據。作為讀者,我深切地感受到一點:邢小利和陳忠實年齡相差約16歲,可以說是屬于經歷了不同時代的兩代人,但是因為工作的關系,因為文學的關系,因為人格理想的關系,他們的人生卻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讓他們之間有著太多的生命交集。在我看來,在陳忠實的晚年,他們兩人之間的關系已經遠遠不再是普通同事的關系,而是一種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生命情感關系。邢小利成為陳忠實可以理解、可以信任、可以依賴的志同道合的文學兄弟。從《年譜》中可以看出,陳忠實在諸多的文學活動和個人生活事件中,都會征求邢小利的意見和建議。可以說,進入新世紀以后,邢小利全程參與了陳忠實的文學生活。這樣,兩人之間自然有著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邢小利在《陳忠實的寂寞》一文中說:“晚年的陳忠實,人是孤獨的。但他的內心也翻滾著波瀾。這種波瀾,化成了他后來寫成的近百萬文字。晚年的文字,透著深重的寂寞,也翻滾著滾滾的波瀾。”也許,只有他能夠理解陳忠實的這種孤獨。山中玉少石頭多,世間人稠知音稀,偉大,也是要有人懂的。
對邢小利個人,陳忠實充滿了關心和鼓勵。《年譜》中記載:“2002年1月22日,在和邢小利的聊天中,陳對邢說,你這個人心性淡泊,現在房子和家庭問題都解決了,安頓下來以后,要多寫東西,搞評論,應該關注并參與全國性的文學話題討論,研究一些全國性的文學問題,普遍性的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樣才能造成更大的影響。然后,陳忠實又以自己的人生體驗談到了人生的緊迫性問題。”“2009年6月17日,(陳忠實)早上打電話給邢小利,說在今天的《西安晚報》上看到邢寫的《五十一歲感懷》,說能理解邢的心態,陪孩子、閑散一些是可以的,但邢現在正是成熟的時候,還要在事業上有進取心。”這些都表明了,陳忠實在以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影響著邢小利。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當年魯迅先生寫給瞿秋白的這句聯語,如果套用來形容陳忠實與邢小利的關系,大概也是十分恰當的。這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間關系的最高境界吧!從作者和譜主的這一關系看來,正因為如此,《年譜》才顯得字字是思,句句是情,在情真意切里,寄托著作者對于故人的無限懷念。
當然,作為讀者,我們也應該明白一點,任何年譜,無論編者多么追求客觀地展示譜主生平事略的編纂目標,事實上都難以擺脫其個人眼光和自身見解,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程度上的片面性。邢小利的《年譜》自然也沒能擺脫這一局限,所以,我們希望這一局限被以后其他的同類著作所彌補。辯證地看,無論哪一種年譜,作者的視角都可為讀者提供全面理解譜主的嶄新視角,而這正揭示了譜主生命存在的無比豐富性的一面。與此同時,以愚之見,個體生命的豐富性,又絕非某一本年譜——邢小利的《陳忠實年譜》自然亦不例外——可以一勞永逸地一網打盡,自然還需要人們——包括原編者——付出更艱辛的努力,不斷去補充完善那些后來發現的對研究譜主有重大意義的細節,而這正是一本年譜的開放性之所在,也正是作為讀者的我所期待的。
《歡樂詩學:泛審美時代的快感體驗與文化嬗變》
傅守祥著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以辯證思維和跨學科視野,直視大眾文化崛起及其相關文化現象與審美變遷;以鮮明的文化自覺和理論自信,展示時代進步、引領社會風尚。從美學分析與哲學批判高度,研究現實性極強的、以大眾文化現象為焦點的文化泛化與美學變革,原創性地提出大眾文化審美化的文化合理性與時代弊病,深刻闡明社會學美學的理論范式,力倡文化化人、藝術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