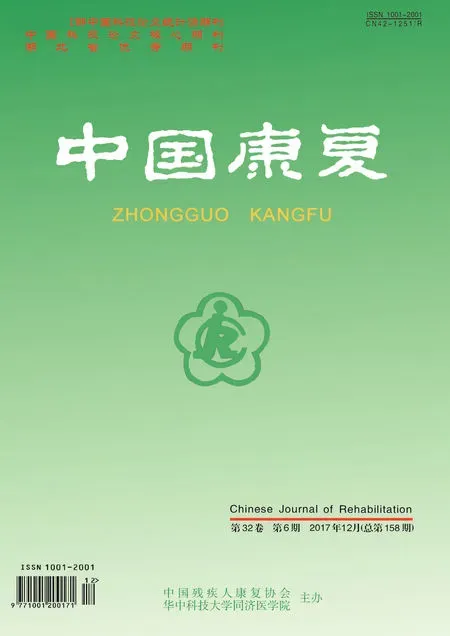強化呼吸訓練聯合常規康復訓練對吉蘭-巴雷綜合癥患者功能康復及心理變化的影響
梁文銳,吳小平,張啟富,莫明玉,李鑫
吉蘭-巴雷綜合癥(Guillain-Barre Syndrome,GBS)是一種常見的神經肌肉疾病,臨床表現為四肢癱瘓及呼吸困難,易發缺氧、肺部炎癥等并發癥,伴有焦慮、抑郁、失眠等心理障礙[1]。呼吸功能康復及改善負面心理狀態是康復治療的重點。在胸廓下緣季肋部應用呼吸帶能使患者的腹內壓增高,利于強化呼吸肌的訓練,同時強化核心穩定性訓練,利于肢體功能康復,減輕心理的負面影響[2]。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重點觀察強化呼吸訓練聯合常規康復訓練對吉蘭-巴雷綜合癥患者功能康復、心理變化的康復作用,從而探討一種對GBS功能恢復更為合理、有效的訓練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2月~2017年1月期間在我院神經內科住院治療病情平穩后轉入我科住院治療的40例吉蘭-巴雷綜合癥患者,入選標準:首次發病,符合GBS診斷標準[3];有肢體癱瘓及呼吸肌受累,病情平穩,不需要呼吸機支持,能聽懂簡單的指令,配合康復訓練及呼吸訓練;發病前無肺部先天性疾病如先天性胸廓畸形和肋骨骨折疾病,無精神病;無認知功能障礙;入選患者、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簽治療同意書。排除標準:臨床診斷未明確;不配合治療,影響康復訓練;病情較重,有嚴重的肺部感染、發熱者,有嚴重的心肺等臟器功能不全者;有精神病或認知功能障礙。患者隨機分為2組各20例。①觀察組:男11例,女9例;平均年齡(46.61±7.83)歲;平均病程(16.72±6.29)d;②對照組:男12例,女8例;平均年齡(44.73±8.91)歲;平均病程(17.37±5.48)d;2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2 方法 2組患者早期均在我院神經內科住院治療,給予激素、血漿置換、營養神經等治療,平穩后轉入我科治療,轉入后繼續按神經內科轉入時意見行藥物治療,改善微循環、營養神經等治療,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康復干預,每天訓練120min,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加以應用呼吸帶強化呼吸訓練治療,2組患者每周訓練5d,共訓練8周。①常規康復干預:a.遲緩性癱瘓期:早期的被動活動,預防關節腫脹和僵硬,體位及患側肢體的擺放,床上活動(雙手交叉上舉、翻身、橋式運動等),物理因子治療(功能電刺激、肌電生物反饋治療等);b.恢復期:主動運動,坐位活動,站立活動(站立平衡訓練,下肢負重、上下臺階運動);減重步行訓練,平衡桿內行走,作業治療等;物理因子治療(如低頻脈沖電療法、功能電刺激、肌電生物反饋等)、吞咽訓練等。②呼吸帶強化呼吸訓練:治療前治療師首先與患者溝通,將治療的作用及注意事項與其說明,取得患者的配合,每天訓練2次,每周訓練5d,共訓練8周。選取有一定彈性的透氣尼龍粘帶為材料, 測量患者的胸圍大小,呼吸帶的長度約為患者胸圍的1.1倍,寬度約33cm,可依據患者的胸圍適當增減,束帶一端縫制自粘扣,使約束下胸季肋部時牢固。首先在患者的下胸廓季肋部綁上呼吸帶,呼吸帶的上緣剛好平肋骨下緣,松緊適當,以綁緊后尚能伸入以一個手指為宜。在呼吸訓練時均綁上呼吸帶,具體呼吸訓練方法如下。a.縮唇呼吸法:依據患者的功能評估情況采用前傾坐位或前傾站立位,雙手置于腹部,并放松腹肌,使胸、肩膀、手臂放松,降低腹部肌肉的張力,允許下胸及腹部運動,為了防止患者前傾時跌倒等意外,助手可雙手固定患者的肩部協助患者保持前傾的體位,患者吸氣時縮唇呼吸(微微張開嘴唇),呼氣口的壓力大約是5cm H2O,在4~6s內將氣體緩慢呼出,每次訓練10~15min,3次/d[4-5]。b.腹式呼吸法:患者仰臥位,髖關節、膝關節稍屈曲,治療師將他/她的手放在患者前肋軟骨下方的腹直肌上,并通過口令讓患者通過鼻子緩慢深吸氣,當腹直肌被抬起時,治療師對腹直肌施加適當的阻力,以誘發深層肌肉力量的出現。在上述訓練后立即讓患者嘴唇縮小,進行縮唇呼吸,持續呼氣一段時間。每次訓練10~15min,3次/d[6-7]。⑤注意事項:強化呼吸訓練時應在進餐30min后進行,以免呼吸帶使用導致腹部不適,出現嘔吐、反流等癥狀,如果出現上述癥狀,應及時休息,松開呼吸帶,注意調整松緊度。癥狀緩解后繼續訓練治療。不訓練時松開并取下呼吸帶。
1.3 評定標準 于治療前、治療8周后分別對2組患者進行以下評定:①肺功能評定:觀察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第一秒最大呼氣量(First Secon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FEV1),FEV1/FVC;②Fugl-Meyer 量表進行運動功能(FMA)評定[8]。;③ADL能力評定:采用改良Barthel指數(MBI)進行 ADL 能力評定[9]。④心理評定:采用醫院焦慮和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對2組患者評定心理功能[10],上述評定均由本科室不知情分組情況的治療師評定,采用盲法評定。

2 結果
治療8周后,2組患者FEV1、FVC、FEV1/FVC均較治療前顯著提高(均P<0.05);且觀察組上述指標高于對照組(均P<0.05),見表1。
治療后,2組FMA、MBI評分均較治療前顯著提高(均P<0.05),且觀察組上述指標均高于對照組(均P<0.05),治療后,2組HADS評分均明顯低于治療前(均P<0.05),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3。


組別n時間FEV1(L)FVC(L)FEV1/FVC對照組20治療前1.46±0.052.35±0.170.62±0.03治療后1.97±0.12a2.52±0.43a0.78±0.02a觀察組20治療前1.43±0.082.32±0.120.61±0.05治療后2.39±0.16ab2.92±0.31ab0.83±0.03ab
與治療前比較,aP<0.05;與對照組比較,bP<0.05


與治療前比較,aP<0.05;與對照組比較,bP<0.05


與治療前比較,aP<0.05;與對照組比較,bP<0.05
3 討論
GBS是一種免疫介導的疾病,表現為涉及周圍神經系統的急性多發性神經系統疾病,通常出現下肢遲緩性癱瘓,逐漸上升累及上肢及延髓,出現呼吸困難,嚴重者需要呼吸機通氣支持[11]。肢體的癱瘓導致患者肌張力減低,伴有肢體感覺的缺失,使其進食、穿衣、坐位、站立、行走等日常生活能力明顯受限,因此在恢復期研究重點多數放在肢體的感覺恢復及運動功能上,如上肢及手功能訓練、行走訓練、功率自行車訓練等,而忽視了呼吸功能康復訓練,在心理方面的康復研究更少見。
由于呼吸肌功能下降,咳嗽及咳痰能力不足,免疫功能下降,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是其重要的并發癥,呼吸肌和吞咽的損害是影響死亡率的主要原因[12]。呼吸功能受損,導致呼吸肌和輔助呼吸肌的肌力下降,通常表現為呼氣和吸氣的肌肉的最大力量及耐力下降,胸廓運動的異常[13-14]。本研究中使用呼吸帶強化呼吸訓練是我科近年來依據臨床實踐創立的一種強化呼吸訓練方法,該療法的優點及注意事項包括:①所使用的呼吸帶為具有一定彈性的布帶,材質柔軟,不易傷及患者,取材方面,制作簡單,操作方便。②臨床觀察中我們發現吉蘭-巴雷綜合癥患者前胸廓通常向外翻,胸部前挺,出現胸廓的畸形。應用呼吸帶強化訓練能利用呼吸帶的約束力,糾正胸廓的畸形,增加軀干部位的本體感覺刺激,綜合運用感覺統和訓練,同時增加腹內壓,對核心肌群如腹直肌、腹內斜肌、腹外斜肌、腹橫肌、胸腰筋膜、膈肌等的核心穩定性訓練時給予額外施加阻力,充分應用了肌力訓練時的阻力原則,強化核心肌群,使訓練的效果更明顯。呼吸肌訓練的原理是改善橫膈肌和肋間內外肌、腹肌的力量[15]。③使用呼吸帶限制了胸廓的過度擴張,使腹肌在吸氣時隆起,增加腹壓,有助于建立腹式呼吸模式,使呼氣時最大限度擴張腹部,呼氣時最大限度收縮腹部,避免了傳統方法需要治療師使用雙手壓患者胸部,提高訓練效率,改善低下的呼吸肌。腹式呼吸訓練是核心穩定性訓練的訓練內容之一,通過腹式呼吸訓練,起到訓練膈肌、腹肌、肋間肌、腰、胸背部肌群等核心穩定性肌肉,提高核心穩定性。本研究結果顯示,2組患者經過8周治療后,其呼吸功能(FEV1、FVC、FEV1/FVC)評分、FMA評分、MBI評分均較治療前有明顯提高,并且上述指標以使用呼吸帶強化呼吸訓練聯合常規訓練組的改善幅度較顯著,提示使用呼吸帶強化呼吸訓練聯合常規訓練能提高吉蘭-巴雷綜合癥患者的肺功能評價指標,提高了生活質量,主要是強化呼吸訓練使呼氣肌肉得到鍛煉和功能恢復,由胸式呼吸轉變為腹式呼吸,增加肺活量,同時強化核心穩定性訓練,提高肢體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這與邵燕兒[16]、于碧馨等[17]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運動神經元疾病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如出現抑郁、焦慮、恐懼、悲觀等心理問題,負面心理變化明顯影響康復過程及結果,因此康復不僅要加強肢體功能的康復,還應重視心理、認知、行為方面的康復[4]。研究顯示呼吸訓練對情緒和心理功能產生積極的影響,運用HADS、36項健康調查簡表、疲勞影響量表對患者進行心理變化評價,治療后抑郁及焦慮均較訓練前明顯改善[10]。呼吸運動訓練可通過調控內啡肽、單胺類物質、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及神經傳導通路等多種途徑改善負面心理狀態[18]。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前2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及焦慮表現,治療后2組患者的抑郁及焦慮均有所改善,以觀察組的改善更為明顯,提示經過呼吸訓練后患者的負面心理狀態得到了改善,而良好的心理狀態有利于患者增強重建自信心,提高訓練依從性,配合康復治療,提高訓練效果,促進肢體功能恢復,這與張進等[19]的研究結果一致。
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呼吸訓練時使用呼吸帶,強化了呼吸訓練,證實了在使用呼吸帶強化呼吸訓練聯合常規康復訓練在吉蘭-巴雷綜合癥患者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少,觀察時間短,引起吉蘭-巴雷綜合癥的原因未能統一,此外未能觀察如何選擇訓練的強度、訓練方式才能使訓練效果最明顯,上述的不足之處有待后續繼續深入的研究。
[1] Sonali ,Sihindi, Chapa Gunatilake.Guillain-Barré syndrome presenting with Raynaud's phenomenon: a case report[J]. BMC Neurology ,2014, 14(35):174-179.
[2] Reed CA,Ford KR,Myer GD,et al.The effects of isolated and integrated core stability training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measures :a systematic review [J].Sports Med,2012,42(8):697-706.
[3] 安得仲.神經系統感染性疾病診斷與治療[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578-584.
[4] 黃曉琳,燕鐵斌主編.康復醫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4:234-423
[5] Gosselink R. Controlled breathing and dyspne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J]. J Rehabil Res Dev, 2003, 40(9):25-33.
[6] Seo K, Park SH, Park K.Effects of diaphragm respiration exercise on pulmonary function of male smokers in their twenties[J]. J Phys Ther Sci, 2015, 27(11):2313-2315.
[7] Seo KC, Lee HM, Kim HA.The 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inspiratory diaphragm exercise and expiratory pursed-lip breathing exercise on pulmonary functions of stroke patients[J]. J Phys Ther Sci, 2013, 25(7): 241-244.
[8] 朱槦連.神經康復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1:151.
[9] 閔瑜,吳媛媛,燕鐵斌.改良Barthel指數(簡體中文版)量表平的腦卒中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效度和信度研究[J].中華物理醫學與康復雜志,2008,30(3):185-188.
[10]Johannes B, Bussmann PhD ,Marcel P. Garssen.analysing the favourable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relationships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fatigue and functioning in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and 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J]. J Rehabil Med ,2007,39(11): 121-125.
[11]Flachenecker P. Autonomic dysfunction in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and multiple sclerosis[J]. J Neurol,2007, 254(2):96-101.
[12]Adam Ogna ,Helene Prigent ,Michele Lejaille. Swallowing and swallowing- breathing interaction as predictors of intubation in Guillain- Barré syndrome. Brain and Behavior[J]. Brain and Behavior,2017,61(7): 11-17.
[13]Pollock RD,Rafferty GF,Moxhan J.muscle strength and training in stroke and neurology:a systematic review[J].IntJ Stroke,2013,25(8):124-130.
[14]Britto RR,Rezende NR,Marinho KC.Inspiratory muscular training in chronic stroke survivor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Arch Phys Med Rehabil,2011,92(5):184-190.
[15]Prasad SA, Pryor JA.Physiotherapy for Respiratory and Cardiac Problems Adults and Paediatrics[J]. Churchill Livingstone Elsevier,2008, 32(7):156-165.
[16]邵燕兒,周磊.呼吸功能鍛煉對老年慢性阻塞性肺氣腫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J].中國康復,2015,30(5):370-371.
[17]于碧馨,朱佳,楊曉紅.藥物聯合呼吸康復訓練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穩定期患者的影響[J].中國康復,2015,30(3):219-220.
[18]魏利娟,馬亞飛,伍軍,等.吸氣肌訓練對食管癌根治術后患者心肺功能及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華物理醫學與康復雜志,2015,37(1):40-41.
[19]張進,楊鯤鵬,侯向生,等.呼吸訓練器對重癥肌無力患者胸腺切除術后肺功能及心理變化的影響[J].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志,2017,20(5):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