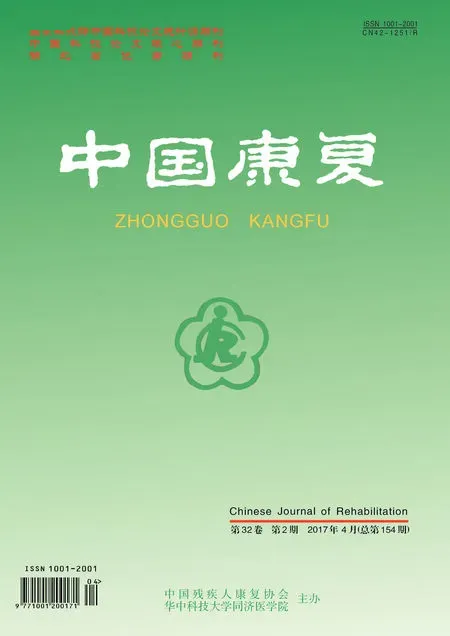認知雙重任務訓練對青年人動態平衡的影響
莊霽雯,鄭潔皎,陳秀恩
平衡是指身體所處的一種姿態以及在自身運動或受到外力作用時能夠自動調整并維持姿勢的一種能力[1]。人類大部分日常任務的完成都依賴于身體的平衡功能[2],近年來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證明認知是影響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3],并已有關于認知結合平衡訓練對靜態平衡的研究[4]。為此,本研究將觀察認知結合平衡訓練對動態平衡的影響。另外,許多研究已發現我國青年人體質有所下滑[5]。青年的體質健康狀況關系到國家、民族未來的發展,重視他們的體質問題并對其進行干預訓練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平衡能力是評定運動機能及健康水平的重要身體素質指標,是反應人體體質水平的重要指標[6]。國內外研究證明,科學合理的訓練能夠改善正常人平衡能力并預防跌倒[7]。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6年3月~2016年7月隨機選取20名在我科實習的治療師作為研究對象。入選標準:運動系統、神經系統及耳鼻喉科病史系統回顧和體格檢查無異常;無眩暈史;偶爾但非定期參加體育鍛煉;實驗前未曾接觸平衡測試儀、未進行過特殊的平衡訓練。采用隨機數字法分為2組各10例。①觀察組,男性5例,女性5例,年齡(22.0±1.41)歲,身高(164.7±6.99)cm,體質量(60.2±11.37)kg。②對照組,男性5例,女性5例,年齡(22.0±1.49)歲,身高(170.8±9.67)cm,體質量(62.3±9.84)kg。2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2 方法 ①2組在訓練開始之前均進行數字字母連線測試并記錄用時和錯誤數。②2組在訓練開始之前采用NeuroCom Balance Manager動態平衡測試儀進行感覺統和測試和姿態穩定極限測試并記錄結果。③訓練方法:使實驗對象站在測力臺指定位置,并在治療師的指示下將重心分別移動到顯示屏幕上的中、前、后、左、右五個指定光標中,在每個光標中保持2min。觀察組在控制重心移動的同時利用“六六腦·腦功能認知障礙診治系統軟件v1.0”完成Stroop沖突抑制任務訓練。④2組均訓練5次/周,10min/次,共2周。訓練結束后實驗對象需再進行數字字母連線測試與動態平衡儀上的四項測試并記錄結果。
1.3 評定標準 采用NeuroCom Balance Manager動態平衡測試系統獲得客觀數據,該系統包括18cm×18cm的精密測力板、醫療隔離電源、計算機、專用平衡處理和分析軟件及打印機。軟件將壓力傳感器上的力學信號記錄并轉換成數字信號傳入電腦中,并進行分析處理。被測試者脫鞋,穿上保護裝備,雙足站在測力板上依據身高分配的指定位置。①感覺統和測試(Sensory Organization Test,SOT):動態平衡測試系統依次提供6項環境,每項測試3次,每次10s,每項測試得分取3次的平均值。第1項:睜眼,環境和地面穩定;第2項:閉眼,環境和地面穩定;第3項:睜眼,地面穩定,環境晃動;第4項:睜眼,環境穩定,地面擺動;第5項:閉眼,環境穩定,地面擺動;第6項:睜眼,環境晃動,地面擺動。要求受試者雙手自然下垂,眼睛平視前方,盡量保持身體穩定站立。測試系統將重心晃動速度、幅度、軌跡長等綜合計算出分數。數據記錄每一次測試得分以及感覺統和測試綜合得分(即動態平衡能力得分)。②姿態穩定極限(Limit of Stability,LOS)測試:受試者現將重心保持在兩足中間,根據屏幕提示,依次將重心移動到前方、右前方、右方、右后方、后方、左后方、左方、左前方這八個方向的最遠距離。每一個方向測試完后都要將重心移回中間再重新開始下一個方向的測試。數據記錄每個方向的反應時、移動速度、端點行程、最大偏移、方向控制,以及每個指標的綜合值。

2 結果
2.1 感覺統合測試 訓練2周后,觀察組SOT綜合得分及第5、6項測試得分均明顯高于訓練前及對照組(P<0.05,0.01),訓練前后觀察組第1、2、3、4項得分及對照組各項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SOT各項測試2組訓練前后比較 分,
與訓練前比較,aP<0.05,bP<0.01;與對照組比較,cP<0.05
2.2 姿態穩定極限測試 訓練2周后,觀察組反應時較訓練前明顯降低(P<0.05),移動速度、端點行程距離、最大偏移距離及方向控制能力較訓練前明顯提高(P<0.05,0.01);對照組在訓練后移動速度、端點行程距離及最大偏移距離較訓練前明顯提高(P<0.05,0.01),而在反應時和方向控制方面訓練前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組間各項評定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參數觀察組(n=10)訓練前訓練后對照組(n=10)訓練前訓練后反應時(s)0.8±0.30.5±0.1a0.8±0.20.6±0.2移動速度(deg/s)4.9±1.86.8±1.7a4.2±1.36.5±1.9a端點行程(%)69.2±15.784.7±7.3b70.0±8.383.4±12.2b最大偏移(%)83.7±12.596.5±4.2a81.8±10.093.7±7.3b方向控制(%)73.7±7.481.9±2.7b79.0±8.380.1±4.7
與訓練前比較,aP<0.05,bP<0.01
3 討論
近年來國內對于平衡訓練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有平衡功能障礙的人群上,如偏癱、腦癱、運動器官損傷患者和平衡能力衰減的老年人[8-9],以及運動員、宇航員等對平衡能力要求很高的專業人員[10],對普通健康人的平衡能力的訓練研究和相關報道都很少。另外,國外的一些研究指出,擁有較好平衡能力的運動員或大學生,在他們平時的比賽或者運動中發生運動損傷的幾率較低[11-12],這說明平衡能力的提高,確實有助于人體在運動過程中較好的控制身體,以降低傷害的發生率。同時也提示我們,對運動員甚至非運動專業的普通大學生進行平衡能力的訓練,在對于預防他們在運動中損傷的發生,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國國民體質監測中對人體平衡能力進行測定,認為平衡功能最佳年齡在20~25歲之間[13-14],因此研究此段年齡的青年人平衡能力有重要意義。
人類的平衡感覺系統包括視覺、本體感覺和前庭覺。感覺統合測試通過改變環境或人體感覺輸入條件,測試出人體在動態環境下的平衡能力。動態平衡能力包括2個方面[15]:①自動態平衡,即人體在進行各種自主運動,例如由坐到站,或者站著將重心向各個方向移動即本研究中的LOS測試;②他動態平衡,即人體在外界干擾下保持平衡,例如推、拉力下恢復穩定狀態或者在環境、地面狀態改變影響姿勢的同時,保持自身姿勢穩定的能力,即本研究中的SOT。感覺統合測試會通過隔離受試者一種或多種感覺,測試出某一種感覺功能是否正常。比如其中第5項,要求受試者在閉眼,足下地面擺動的情況下保持平衡。此時受試者主要是運用前庭覺來維持自身姿勢控制。人體對姿勢和平衡的控制,不僅受大腦皮質、脊髓等運動中樞的調控,還涉及認知和感覺加工過程[16],是知覺、認知和運動系統交互作用的結果。研究認為,當總認知負荷未超出機體可承受的認知負荷時,可以有多余認知負荷供使用,這為完成雙重任務操作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當總認知負荷超出機體可承受的認知負荷時,認知負荷不足會導致任務完成率下降[17]。
認知平衡雙重任務訓練被定義為同時或交替性進行兩項或兩項以上的認知和平衡訓練[18]。認知訓練包括一系列記憶或注意任務(涉及工作記憶和執行功能),如數字計算、視覺尋找、言語流暢性及反饋訓練等。常見的平衡訓練形式包括走路、平衡板、平衡儀等[19-20]。認知功能主要包括記憶力、執行功能、空間定向能力、言語功能等。平衡功能的維持是大腦全面信息處理系統的一部分,與認知過程相互影響,尤其是空間記憶[21]。前人對老年人進行空間記憶-平衡雙重任務訓練后,發現與空間記憶相關的認知資源可用于動態平衡的恢復[22]。其原因在于使用空間記憶用于指導空間注意力和運動的空間位置,可通過額葉前部皮質空間編碼形成,提高大腦前額的鍛煉[23-24]。
Vuillerme等[25]研究了青年人的認知注意如何影響著站立時的平衡能力,發現認知注意的焦點對壓力中心擺動速度有影響,并從神經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有意的動作控制會調動額外的身體動作單元,使神經肌肉的活動增加,反而影響站立姿勢的控制。前人以年輕人為被試,通過控制認知任務和平衡任務的難度探討對平衡能力的影響,發現當認知任務難度增加,姿勢擺動降低[26]。認知任務難度的提高使受試者把注意力從平衡相關的因素轉移開,避免對姿勢的過度矯正,從而增加姿勢穩定性。前人采用了音樂雙重任務對青年人進行干預,發現對平衡的影響不明顯。這可能是因為音樂是一種被動接受的外部刺激,會被作為一種干擾信號被大腦接收,但由于沒有認知的主動參與,對大腦認知的影響較小[4]。也可能是因為音樂作為認知干預時,對年輕人的注意力影響太小,從而不能影響平衡能力。Silsupadol等[27]考察了對平衡受損老年人的兩種平衡訓練方式的效果,一種為單任務平衡訓練,另一種為雙任務訓練,即在進行平衡訓練時執行記憶任務。結果發現,雙任務下的訓練效果可持續3 個月,并且在被試在新的雙任務中的操作也得到了改善,證實了雙任務訓練的遷移作用。而Stroop沖突抑制認知訓練需要受試者主動參與,經過認知訓練,對沖突信號起監控作用的前扣帶回皮層激活程度降低,而執行沖突解決的前額皮層激活程度增加,加強了自上而下的認知控制能力,進而導致干擾控制能力的提升[28-29]。本研究發現訓練結束后,觀察組動態平衡提高的結果明顯優于對照組,這驗證了前人的研究結果:與空間記憶相關的認知資源可用于動態平衡的恢復[30]。并且觀察組認知測試提高的結果也優于對照組,這驗證了我國學者認知平衡雙重任務訓練可以同時促進平衡和認知能力的結論[21]。
另外,對于認知雙重任務訓練對提高維持平衡的哪種能力提高最顯著,目前還沒有統一定論。有研究指出,雙任務訓練對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阿爾茨海默病、癡呆、腦卒中、帕金森病等老年患者認知功能的積極效應更為顯著[31-32]。也有研究認為,認知雙重任務對視覺在維持平衡時的能力提高可能更有效[4]。而本研究在感覺統合測試中發現第5項(閉眼,環境穩定,地面擺動)和第6項(睜眼,環境晃動,地面擺動)測試中觀察組訓練后成績均有顯著提高,這提示認知平衡雙重任務訓練可能在提高人體感覺統合中的前庭覺方面更有效果,這需要我們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1] 鄭潔皎, 趙尚敏, 陳秀恩, 等. 運動習慣對老年人平衡能力的影響[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08, 14(1): 73-73.
[2] 宋利娜, 張洪斌. 腦卒中偏癱患者平衡功能康復方法研究進展[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12, 27(8): 781-783.
[3] Wang XQ, Pi YL, Chen BL, et al. Cognitive motor intervention for gait and balance in Parkinson's disea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lin Rehabil, 2016, 30(2): 134-144.
[4] 戚維璜, 鄭潔皎, 安丙辰. 認知雙重任務干擾平衡功能的研究[J]. 中國康復, 2014, 29(2): 83-85.
[5] 鄧希泉, 鄒宇春. 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健康的主要問題研究[J]. 北京青年研究, 2015, 12(1): 23-42.
[6] 華冰. 加滑擾動訓練對大學男生平衡能力影響效果評價[J]. 中國學校衛生, 2016, 37(5): 776-780.
[7] Logghe IH, Verhagen AP, Rademaker AC, et al. The effects of Tai Chi on fall prevention,fear of falling and balance in older people: a meta-analysis[J]. Prev Med, 2010, 51(3-4): 222-227.
[8] Cho KH, Lee KJ, Song CH. Virtual-reality balance training with a video-game system improves dynamic balance in chronic stroke patients[J]. Tohoku J Exp Med, 2012, 228(1): 69-74.
[9] Fourtassi M, Rode G, Tilikete C, et al. Spontaneous ocular positioning during visual imagery in patients with hemianopia and/or hemineglect[J]. Neuropsychologia, 2016, 86(2): 141-152.
[10] Lee BA, Lee SH, Oh DJ. Effects of peripheral injury in athletes with long-term-exercise participation in modern pentathlons[J]. J Exerc Rehabil, 2013, 9(5): 481-488.
[11] Trojian TH, Mckeag DB. Single leg balance test to identify risk of ankle sprains[J]. Br J Sports Med, 2006, 40(7): 610-613.
[12] Steinberg N, Eliakim A, Zaav A, et al. Postural balance following aerobic fatigue tests:A longitudinal study among young athletes[J]. J Mot Behav, 2016, 48(4): 332-340.
[13] 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 年國民體質檢測報告[M]. 北京: 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 2002: 234-237.
[14] 國家體育總局. 國民體質測定標準手冊. 成年人部分[M].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 2004: 357-359.
[15] 劉崇, 任立峰, 史建偉, 等. 人體平衡能力的評價系統[J]. 中國組織工程研究, 2009, 13(2): 363-367.
[16] Yogev-Seligmann G, Hausdorff JM, Giladi N. The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ttention in gait[J]. Mov Disord, 2008, 23(3): 329-342.
[17] Fraser KL, Ayres P, Sweller J. Cognitive load theory for the design of medical simulations[J]. Simul Healthc, 2015, 10(5): 295-307.
[18] Shin SS, An DH. The effect of motor dual-task balance training on balance and gait of elderly women[J]. J Phys Ther Sci, 2014, 26(3): 359-361.
[19] Pichierri G, Wolf P, Murer K, et al. Cognitive and cognitive-motor interventions affecting physical functioning: a systematic review[J]. BMC Geriatr, 2011, 11(1): 29-33.
[20] Rahe J, Petrelli A, Kaesberg S, et al. Effects of cognitive training with addi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compared to pure cognitive training in healthy older adults [J]. Clin Interv Aging, 2015, 10(3): 297-310.
[21] 陳秀恩, 鄭潔皎, 施海濤, 等. 認知注意力、平衡功能雙重任務訓練對預防老年人跌倒的臨床研究[J]. 中國康復, 2016, 31(3): 215-217.
[22] Cheng KC, Pratt J, Maki BE. Do aging and dual-tasking impair the capacity to store and retrieve visuospatial information needed to guide perturbation-evoked reach-to-grasp reactions[J]? PLoS One, 2013, 8(11): 794-801.
[23] Bai CH, Bridger EK, Zimmer HD, et al.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testing: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J]. Front Behav Neurosci, 2015, 9(3): 248-255.
[24] Huppert T, Schmidt B, Beluk N, et al. Measurement of brain activation during an upright stepping reaction task using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J]. Hum Brain Mapp, 2013, 34(11): 2817-2828.
[25] Pradels A, Pradon D, Hlavackova P, et al. Sensory re-weighting in human bipedal postural control: the effects of experimentally-induced plantar pain[J]. PLoS One, 2013, 8(6): 655-660.
[26] Swan L, Otani H, Loubert P, et al. Reducing postural sway by manipulating the difficulty levels of a cognitive task and a balance task[J].Gait & Posture, 2007, 26(3): 470-474.
[27] Silsupadol P, Shumway-Cook A, Lugade V, et al. Effects of single-task versus dual-task training on balance performance in older adults: a double-blind,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Arch Phys Med Rehabil, 2009, 90(3): 381-387.
[28] Millner AJ, Jaroszewski AC, Chamarthi H, et al. 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training-induced cognitive control improvements[J]. Neuroimage, 2012, 63(2): 742-753.
[29] Protopapas A, Vlahou EL, Moirou D, et al. Word reading practice reduces Stroop interference in children[J]. Acta Psychol(Amst), 2014, 148(2): 204-208.
[30] Cheng KC, Pratt J, Maki BE. Effects of spatial-memory decay and dual-task interference on perturbation-evoked reach-to-grasp reactions in the absence of online visual feedback[J]. Hum Mov Sci, 2013, 32(2): 328-342.
[31] Reijnders J, Van Heugten C, Van Boxtel M. Cognitive interventions in healthy older adults and people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 systematic review[J]. Ageing Res Rev, 2013, 12(1): 263-275.
[32] Muniz R, Serra CM, Reisberg B, et al. Cognitive-motor interven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long-term results from the maria wolff trial[J]. J Alzheimers Dis, 2015, 45(1): 29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