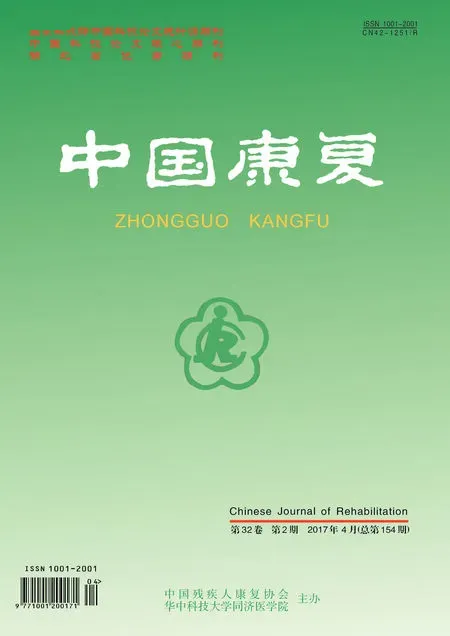家庭及社區環境對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的影響
萬宏偉,王靜,陳長香
腦卒中具有復發率、致殘率、死亡率高及并發癥多等特點[1],隨著醫學診斷和治療技術的提高,患者生存率也大大提升,然而殘疾者眾多,以往腦卒中患者的康復結局評價一般以患者的身體結構和功能,以及身體狀況對于日常生活活動的影響為依據[2],而社會參與功能應作為康復結局評定的重要指標,因它不僅體現了新醫學模式的轉變和循證醫學的發展,更是腦卒中患者出院后社會水平的康復結局[3]。了解目前腦卒中患者的的社會參與功能及其家庭及社區的人文和物理環境對其的影響,為采取應對措施,促進患者社會回歸提供臨床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10月~2016年9月遷西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病房住院診斷腦卒中的患者共298例,納入標準:年齡>18歲,符合中華醫學會編著的《臨床診療指南·神經病學分冊》中的診斷標準[4],并經CT或MRI確診。經住院治療后神志清,能完成問卷;排除標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嚴重心、肝、腎功能不全、呼吸衰竭及惡性腫瘤患者;癡呆病史和精神疾病史者;語言表達不清或溝通障礙者;盲、聾、失語患者。出院8周后于患者門診復查或上門隨訪時評價,回收問卷281份,有效回收率為94.3%。年齡45~88歲,平均年齡(61.68±10.01)歲。其中男172人,女109人;在婚231人,非在婚50人;小學及以下93人,初、高中131人,大專及以上57人。
1.2 方法 于患者出院8周后進行自主參與問卷調查。①自主參與問卷(Impact on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Questionnaire,IPA)評測[5],IPA由荷蘭學者研制,第二軍醫大學完成中文版IPA的漢化[5]。該量表包括室內自主參與、家庭角色自主參與、室外自主參與、社會生活自主參與4個維度共25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0~4級評分法,0分視為無參與功能障礙,1~4分為不同程度參與功能障礙,評分范圍為0~100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感知日常生活的參與可能性越小[5]。②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PGAR Index, APGAR)評測,量表評分范圍0~10分,總分越高說明家庭功能越好[6]。該量表共5個條目,每個條目均采用0~2分評分法。總分為7~10分即視為家庭功能良好;4~6分即視為家庭功能中度障礙;0~3分則視為家庭功能重度障礙[6]。③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該量表是用來評定個體社會支持度的問卷[7]。量表包括3個維度共10個條目,總分越高,說明社會支持程度越好。總分>30分代表高水平的社會支持度;20~30分代表一般水平的社會支持;<20分代表獲得社會支持較少[7]。同時進行一般人口學資料、卒中類型、家庭及社區的人文環境和物理環境資料收集。

2 結果
2.1 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狀況 281例患者IPA總分為(41.91±20.65)分,室內自主參與維度(9.45±6.37)分,家庭角色維度(12.48±8.55)分,室外自主參與維度(10.15±5.86)分,社會生活維度(8.12±5.36)分。
2.2 影響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的單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年齡、卒中類型、家庭功能、社會支持、能否自行出入家門、自我形象滿意度、地面障礙物清除與否、有無小區活動設施、對小區活動設施利用情況、小區有否無障礙通道與IPA總分明顯相關(P<0.05)。見表1。

表1 影響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的環境因素分析
2.3 影響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的多因素分析 以腦卒中患者IPA總分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卒中類型、自行出入家門、清除室內障礙物、形象滿意度、社會支持進入回歸方程。影響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自行出入家門、形象滿意度、卒中類型、年齡、清除室內障礙物、社會支持(P<0.05)。見表2。

表2 影響腦卒中患者IPA總分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患者IPA總均分為(41.91±20.65)分,提示腦卒中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參與功能障礙,與馬景全的報道相一致[8],與病變部位損傷遺留后遺癥,許多患者患病后出現肢體運動功能、認知功能、語言等方面的障礙,影響了日常生活能力,也影響了家庭和社會參與功能有關。
本研究結果表明年齡與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緊密相關,與類似相關研究一致[9]。年齡增大,血管彈性下降、脆性增加,發生卒中的嚴重程度高,復發率也高,通過臨床治療后并發癥較多且預后差,加之自身各器官功能和抵抗力也在不斷下降,生理、心理等均發生明顯改變,從而使患者的軀體功能下降,導致自主社會參與功能低下[10]。張碩等[11]的研究也顯示,年齡越大的老年人其越缺乏社會參與的主動性,社會網絡越小。另外,有部分老年人因退休,淡出社會造成自身參與社會功能的下降,提示我們可以充分發揮殘障老人的余熱,支持和鼓勵其繼續參與社會工作[11],增加他們自身“被社會需要”、“被家人需要”的信念;同時,社會上也應該提供這樣的平臺,促進和提高他們的社會參與度,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卒中類型是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水平的影響因素,且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社會參與功能較差,與杜蕾等[9]研究結果相一致。臨床上出血性腦卒中的死亡率大大高于缺血性腦卒中,出血性卒中患者往往病情危重,患者的意識障礙程度和肢體癱瘓程度均較缺血性卒中患者嚴重,或由手術治療帶來的創傷,使其自主參與社會及生活意識較差[12],影響了社會參與功能。因此疾病康復期應該對患者的運動功能、認知功能、感知覺、言語功能等進行準確的評估和訓練,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及心理功能,降低致殘率,促進患者回歸家庭,融入社會。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人文環境中的社會支持與IPA相關,高水平社會支持IPA評分低,即社會參與功能好,與相關報道一致[13]。社會支持是人們維持心態平衡的重要條件,當人們遭遇挫折困難時,來自家庭、社會中的親朋好友給予了最大的包容和支持,可提高患者的自信和自主的感覺,增強患者主觀回歸社會及家庭的信心[13]。家人、朋友的探望可以調節因疾病期醫源性的限制,導致社會參與功能的缺失,幫助患者感受外界社會,促進患者萌生主動進行社會參與的意愿,體驗社會變化,以期早日回歸原有的生活狀態。
本研究結果顯示物理環境中室內障礙物清除、能自行出入家門的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較高,與國外研究結果相一致[14],腦卒中患者感知到最大的參與受限是活動是否自主,腦卒中患者大部分伴有軀體障礙[14],如能借助輔助器械達到自主活動的目的,家庭、小區及公共場所如果能設立無障礙通道設施,考慮到該類人群的需求,使行動不便的卒中患者自主活動的空間和范圍增多,能夠體現社會對他們的尊重更有利于他們融入社會。社區醫務人員和家屬應鼓勵患者實施早期康復訓練,參與交流,走出家庭,實現社會回歸。
[1] 蘭天, 呼日勒特木爾. 腦卒中流行病學現狀及遺傳學研究進展[J]. 疑難病雜志, 2015, 14(9): 986-989.
[2] 邱卓英, 荀芳. 基于ICF的康復評定工具開發與標準化研究[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11, 17(2): 101-105.
[3] 張君梅, 蔡飛鳴, 王樸, 等. 針對腦卒中的ICF核心分類模板[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08, 14(12): 1124-1127.
[4] 中華醫學會. 臨床診療指南神經病學分冊[M].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0: 5-6.
[5] 邱卓英, 李沁燚, 陳迪, 等. ICF-CY理論架構、方法、分類體系及其應用[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14, 20(1): 1-5.
[6] 李榮風, 徐夫真, 紀林芹, 等. 家庭功能評定量表的初步修訂[J].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 2013, 21(7): 996-1000.
[7] 王曉晰, 張志強. 腦卒中患者社會支持與日常生活能力和焦慮關系[J]. 中國公共衛生, 2015, 31(4): 501-503.
[8] 馬景全, 王靜, 陳長香. 康復治療的介入與否對腦卒中患者社會參與功能的影響[J]. 現代預防醫學, 2016, 43(19): 3556-3559.
[9] 杜蕾, 陳長香, 姜研, 等. 身體功能狀況對腦卒中患者自主社會參與功能的影響[J]. 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16, 22(10): 1218-1221.
[10] Hamzat TK, Peters GO. Motor function and participation among Nigerian stroke survivors: 6-Month follow-up study[J]. Neuro Rehabilitation, 2009, 25(2): 137-142.
[11] 張碩, 陳功. 中國城市老年人社會隔離現狀與影響因素研究[J]. 人口學刊, 2015, 37(4): 65-75.
[12] Jin M, Pelak VS, Curran T, et al. A preliminary study of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a MCI subjects during different episodic memory tasks[J]. Magn Reson Imaging, 2012, 30(4): 459-470.
[13] 賀亞楠, 胡琛, 周蘭姝. 首發腦卒中患者出院后1周的社會參與水平及影響因素分析[J]. 護理管理雜志, 2013, 13(8): 543-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