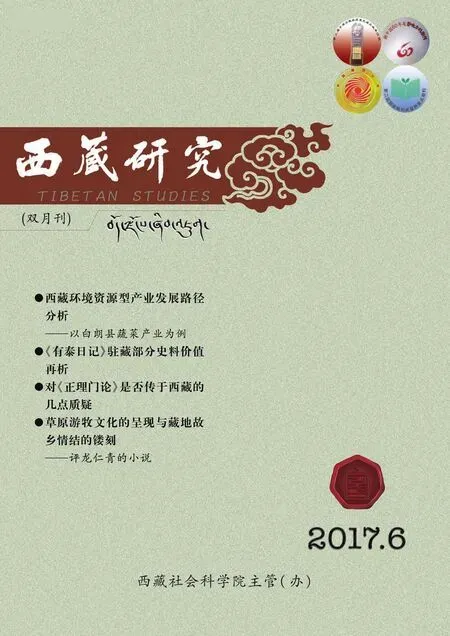倉央嘉措詩歌新出譯本三種
——兼談詩歌復譯問題
榮立宇
(天津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387;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央文獻翻譯研究基地,天津 300204)
一、引言
隨著21世紀一系列的因緣際會,倉央嘉措詩歌在本世紀第 1個 10年(2001—2010年,特別是2006—2010年)在漢語文化圈中迅速完成了華麗的轉身,作者一躍而成為紅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著名詩人,贏得了與南唐李煜媲美,與清代納蘭性德爭輝的盛名。然而,在這之前,倉央嘉措還只是一個在藏地家弦戶誦,在漢地僅見諸藏族文學史或宗教史,只在漢族學者群體小眾之間獲得有限知名度的人物。這個人物的生前身后事終于在經歷了歷史大潮300年的起伏跌宕之后走進了當下普羅大眾的閱讀視野,在21世紀第1、2個10年之交掀起了所謂的“倉央嘉措詩歌熱潮”。流年進入21世紀第2個10年,倉央嘉措熱潮稍稍消退之后,再來看、再來談倉央嘉措詩歌似乎會更加客觀、理性。
二、倉央嘉措詩歌的新出譯本
倉央嘉措詩歌在中國大眾文化消費領域如同狂飆般突進,蔚為大觀。如是說的根據有很多,比如近些年來與倉央嘉措相關書籍的大量涌現,倉央嘉措詩歌偽作的火熱炒作,倉央嘉措詩歌在通俗文學讀物上的不斷刊出以及丙申年初倉央嘉措舞劇在北京的成功上演,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根據,那便是倉央嘉措詩歌的漢語譯本的常譯常新。2013年曾有學者對倉央嘉措詩歌比較嚴肅的漢語譯本做過仔細的考察與統計,當時得到的數字已有21個之多[1]。近兩年來,人們對倉央嘉措詩歌重新翻譯的熱情絲毫不減。兩年之內,倉央嘉措詩歌又有3個新的漢語譯本與讀者見面:它們分別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尋找倉央嘉措》(廖偉棠,2014);《此生雖短意纏綿:倉央嘉措情詩珍本》(無患子,2015);清華大學出版社發行的《一個人的倉央嘉措》(鄭迪菲,2015)。這3個新出譯本的質量如何,各自具有哪些特征,對于詩歌復譯又有哪些啟示,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從英譯來的轉譯——廖偉棠的譯文
廖偉棠,詩人,詩歌譯者,曾獲得多項文學獎,出版有詩集《少年游》《黑雨將至》《八尺雪意》等10種,同時有攝影、雜文、小說等集子問世。
從結構方面來看,《尋找倉央嘉措》一書包括以下幾個部分:倉央嘉措的源頭與反哺、倉央嘉措詩選、詩人倉央嘉措、尋訪筆記、小說、雪匪謠、詩歌、另一個、魂攝后記、附錄。其中倉央嘉措詩選部分提供了譯者的新譯文,凡53首。
對于該譯文的底本,譯者在書內的兩個地方做了明確說明:一則是在卷首,“據Coleman Barks①Coleman Barks的倉央嘉措詩歌英譯前后有兩個版本:一為1992年美國推出的版本;一為2004年印度推出的版本。及于道泉、泰林英譯為藍本”[2]7;另一則是在“詩人倉央嘉措”的部分,“于是我斗膽從Coleman Barks的英譯本去翻譯那個我的倉央嘉措,這樣的‘翻譯’,以前我曾拿杜甫、李白、姜夔等古詩詞試驗過,就像不懂中文的龐德(Ezra Pound)從拉丁文譯本‘轉譯’中國古詩(這拉丁文譯本又是從日文譯本而來)一樣,我用我的半桶水英文在此轉譯Coleman Barks的倉央嘉措,就是想尋找一個以前的譯本所隱匿的詩人”[2]77。
兩處說明略有沖突,但從整個譯詩的排序與詩歌的建行來看,后一種說法更接近真實。從排序來看,廖偉棠譯詩與Coleman Barks的譯本完全一致,而與于道泉的譯本大相徑庭;從詩歌建行來看,廖偉棠譯詩雖以四行詩為主,但也包括為數不少的五行、六行詩,而五行、六行詩正是Coleman Barks譯本的常見建行形式,這一特征恰恰是于道泉譯本所不具備的。
如倉央嘉措詩歌第13首②這里說的排序是按照于道泉譯本的排序。,此首原詩為四行詩,于道泉的漢、英譯本皆為四行譯詩,此首在Coleman Barks的英譯序列中排在第6首的位置,英譯文以6行建行。此首在廖偉棠譯本中排在第6首,漢語譯詩同樣以6行建行。具體譯詩如下:

于道泉譯詩[3]311 Coleman Barks譯詩[4]16 廖偉棠譯詩Words written with black ink,Have been effaced by water drops.Unwritten designs in the mind,(You)cannot erase them even if(you)wan t to.The ink of lovesongswashes of f in the rain,but the love itself,that which cannot bewritten down,staysinside*here*墨水抄寫的情歌被雨水一洗就無但愛情本身——那些不能被寫下的,如雨水長留在雨水之中(廖偉棠,2014:15)
可以看出,廖偉棠的譯詩完全貼近Barks譯詩的建行與表達進行,而距離于道泉的英譯則比較遠。從排序、建行、行文等幾個方面進行觀察,可以印證上文提及的觀點,即廖譯本最可辨認的底本當為Barks的英譯本無疑。
正如廖偉棠在書中對Barks的介紹所揭示的,“此君為美國當代詩人,以翻譯魯米詩歌著稱——雖然他不懂波斯語,但不妨礙他用當代感十足的自由詩翻譯那些神秘主義格律詩。”[2]76同樣地,此君翻譯倉央嘉措“也不懂藏語,他依賴的是前人的英譯,卻秉仗其詩人天賦‘創作’出另一個倉央嘉措”[2]76。
由此可見,廖偉棠譯本的底本是一種來自美國詩人的創譯性譯本,廖偉棠譯本本身則構成經由另一種英譯的轉譯。援引柏拉圖的一句經典,即為“影子的影子”。鑒于廖偉棠所依據底本的創譯性質,雖然他對于底本的參閱尚稱得上亦步亦趨,然而,以倉央嘉措詩歌的原文為坐標,這依然屬于創譯的本子。
(二)再現格律的新譯——無患子的譯文
無患子其人,正式出版物上提供的信息極少。根據《此生雖短意纏綿:倉央嘉措情詩珍本》一書護封上的介紹,此人“閑靜少言,好讀書飲酒,不喜與人交結。常獨行于山川日月之間,偶作文字自娛,亦不示人,多付諸火炬”[5]。這些介紹性質的文字很明顯出自本人手筆,據此判斷,此人當屬詩人一族無疑。
從結構方面來看,《此生雖短意纏綿:倉央嘉措情詩珍本》包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詩、倉央嘉措生平略傳、倉央嘉措的秘密傳說3個部分。倉央嘉措情詩部分搜羅了于道泉的英、漢譯本、曾緘的七言譯本、劉希武的五言譯本,并在此基礎上增添了無患子的今譯本、品賞和旅藏手記。
在此書的題記中,無患子特別提到了于道泉、曾緘、劉希武等人的譯本。并且言明,自己的今譯參照的底本為于道泉的漢、英譯本,同時又指出,“概考慮到原詩是每句六言,姑且削足適履,勉強為之”[5]。
應該說無患子的今譯在性質上屬于間接翻譯中的轉譯,體式則為一個漢字對一個藏音的寬泛格律體①因為嚴謹的漢語格律體譯詩在音節的一一對應之外還涉及到平仄問題,所以這里稱為寬泛的格律體。。在倉央嘉措詩歌漫長的漢譯歷史上,屬于轉譯者不乏其人,曾緘、于貞志、高澤言、伊沙、馬輝等人的譯本皆在此列。屬于漢字——藏音音節對應者則有1979年毛繼祖的譯詩、2013年羊本加的譯文。毛譯作為其論文“試談倉央嘉措情歌”一文的舉例發表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涉及倉央嘉措詩歌凡52首,譯本并未按照于道泉譯本確立的詩歌順序排列。羊譯本作為藏族同胞漢譯倉央嘉措的第二次嘗試,第一次以單行本出版的形式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推出②1932年7月,藏族人劉家駒翻譯的倉央詩由上海新亞細亞月刊社出版,題為《西藏情歌》,其中包括了倉央詩數首,但不限于此。。而無患子的六言譯詩則屬于此類漢譯的第三種。
除漢字對應藏音之外,無患子譯詩的另一個特點為講求押韻,但韻式并不統一。涉及aaaa(如第3首)、abab(如第2、5首)、abaa(如第 1首)、abca(如第26首)、abcc(如第 27首)、aaba(如第 4、6首)、abcb(如第7、23首)等,當然也不乏一些不押韻的譯詩,如第49首。
漢語六言譯詩其利在于與原詩形式特征的相似③倉央嘉措詩歌的體式為藏族文學中的“諧體”,其主要的形式特征為:每首以四行為主,偶見六行,每行六個音節,形成三個停頓,押韻偶有,但不常見。,然而,其弊端也十分明顯,即譯者在閃轉騰挪的過程中受到譯詩格局的限制,很多表示信息的實詞與表示關系的虛詞在譯詩中不得不去掉,與此同時,在另外一些場合,一些用于湊足音節的小詞又會被憑空添加進來。
如倉央嘉措詩歌第1首,無患子的譯詩,“從那東方山巔/升起潔白月亮/瑪吉阿媽的臉/心頭漸漸涌現”[5]6三四兩句之間表示明顯的位置關系的“在”字,由于譯詩格局的限制而不得不被省去。再如第49首,無患子的譯詩,“走遍拉薩街頭/瓊結的人最甜/來會我的姑娘/家就住在瓊結。”[5]110這里“瓊結的人”明顯是“瓊結人”為了湊足音節在字面上所做的稀釋與添加。
事實上,漢語六言譯詩格局的限制構成毛繼祖、羊本加與無患子3種譯本的共同挑戰。而3位譯者在很多地方選詞用字的差異則彰顯了不同譯者在同樣的鎖鏈束縛下舞出的不同舞姿。如倉央嘉措詩歌第33首④此為于道泉譯本的排序,也是多數漢語譯本的排序,羊本加譯本中此首位列第35,毛繼祖譯本則無所謂順序。,無患子的譯詩為“姑娘不是娘養/怕是桃樹所生/為何她的戀情/快過桃花凋零”[5]76,同一首詩毛繼祖則譯為“姑娘不是養的/怕是桃樹長的/喜新厭舊無情/比花開謝還急”[3]397,羊本加的譯詩為“姑娘非母所生,難道長在桃枝?喜新厭舊勁頭,堪比桃花一現。”[6]51。我們可以看到前兩種譯詩中的押韻傾向,如第一種中的“生”“情”“零”,第二種中的“養”“長”,同時也可以看出在譯詩格局限制下不同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如第一種中的“快過桃花凋零”是出于押韻考慮對于“比桃花凋零還快”所做的句式改造,而第二、三種中的“喜新厭舊”成語的引進則是為了譯詩在體式限制下的內容豐滿。
(三)散文詩體的嘗試——鄭迪菲的譯文
鄭迪菲,所知信息不多。根據《一個人的倉央嘉措》護封上的介紹,她是一個“喜歡寂靜、獨行的女孩”“喜愛美術、攝影、文學”,被雷抒雁稱贊為“九零后詩壇十大領軍人物之一”,由此我們可以約略判斷出她的詩人身份。
她與倉央嘉措的淵源頗深,按照她自己的話說,“在她十七歲花季的年齡里愛上了一抹靜謐的藍,愛上了三百年前雪域高原的一位活佛——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從此她跨越了時空、看開了浮云、進入了自己的宗教,仿佛是一粒意念里的塵埃,在愛的世界里游離。”[7]
《一個人的倉央嘉措》在結構上除去引言和后記之外,主體分為三大部分:前世情、今生夢、來生緣,共11輯。就結構上三生的劃分與命名來看這是很明顯的受到佛教影響。
就全書體例來看,該書可謂是十分新穎。譯者“根據全書結構的需要,設定了與倉央嘉措的對話、唱和、獨白、組章和往來情書等體例。”[7]186但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全書涉及以上諸多體例,但是可以辨認出來的倉央嘉措詩歌的新譯本出現在第一輯“風中對語”中,這個小的設置包括倉央嘉措詩歌凡53首,從排序上可以看出受于道泉譯本的影響。
事實上,譯者在書中對自己譯詩的底本問題做了詳細的說明。在解構和演繹的過程中,參閱的現有譯本多達20多種。這個數字無疑十分驚人。具體來說,在詩意上“重點參閱了莊晶、王沂暖和曾緘等名家的經典譯本”,在語言表現手法上“重點借鑒了高澤言、馬輝、苗欣宇、伊沙等老師的創譯、衍譯和潤色的手法”,在保留原詩意的情況下“用自己真實的情感做了一次全新的‘創譯’”[7]186。
就詩歌單篇的設計來看,此譯本也堪稱獨到,這表現在兩個方面:1.對話體譯文,譯者化身為倉央嘉措的轉世戀人“林微塵”,與佛教法王展開了涉及情感問題的隔空對話;2.散文詩譯詩,原詩格律體被譯詩解構成散文詩,這在倉央嘉措詩歌的漢譯史上未見先例。
這里以倉央嘉措詩歌第66首為例,一窺鄭迪菲譯本的風貌。
苦相思[7]27
王:不相見便可不相戀,不相知便可不相思。
林微塵:都說相思苦,來世相見難。我尋遍了雪山,你已無了蹤影,而我卻為此等了三百年。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嚴格意義上的倉央嘉措詩歌漢譯為王所言的部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于道泉的譯本“第一最好是不相見/如此便可不至相戀/第二最好是不相識/如此便可不用相思”[3]26從四句被壓縮成兩句,而林微塵的言說則是譯者化身為倉央嘉措隔世戀人的回應,在進一步詮釋相思苦的基礎上再次言明了等待了300年之久,而這個時間正是倉央嘉措詩歌流傳至今的時間跨度。
關于散文詩的問題,已有一些前輩做過探討。嚴格意義上講,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很長一段時期未見散文詩的蹤影。但寬泛意義上看,也有一些可以看作散文詩的文字,正如郭沫若所言,“我國雖無‘散文詩’之成文,然如屈原《卜居》《漁夫》諸文以及莊子《南華經》中多少文字,是可以稱為‘散文詩’的。”[8]。
嚴格來說,以散文詩來譯格律詩的案例在中國的翻譯史上十分罕見。但是翁顯良等人倡導并且踐行的散體譯詩可以約略看作是散文詩翻譯格律詩的先例。例如下面這首“采桑子”(見下頁)為典型的格律體詩歌,分上下兩闕。譯文將之處理成上下兩個小的散體段落。如果說我們可以姑且將之視為散文詩體譯詩的一種先在嘗試,那么鄭迪菲的倉央嘉措詩歌新譯則是這種譯法在傳統上的延續。
三、倉央嘉措詩歌三種新出譯本的共同點
傅惟慈指出,“文學翻譯——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創作,至少是語言上的再創作。每一個譯者都受個人的文化素養和創作個性影響而形成了一套習慣性的表達手段。”[9]在上文中,我們探討了倉央嘉措詩歌三種新出譯本的個性問題,而在這里我們將重點探討一下它們之間的共性問題。

源詞譯詞[10]采桑子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I’d Rather Not Tell When I was young,to sorrow yet a stranger,I love to go up the tallest towers,the tallest towers,to compose vapid verses simulating sorrow.Now that I am to sorrow fallen prey,what ails me I’d rather not tell,rather not tell,only saying;It’s nice and cool and the autumn tints are mellow.(許淵沖,2010:369)
事實上,這3個新出譯本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共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就譯者身份來看,三種譯本皆屬于詩人譯詩
考察三種譯本的譯者身份,很容易了解到三位譯者在詩人身份這一點上的相似性。而“詩人譯詩、譯詩為詩”恰恰是很多名家所提倡的[11]。
(二)就翻譯模式來說,三種譯本皆屬于間接翻譯
筆者曾專門探討過中外翻譯歷史中的間接翻譯及其模式問題,其中最為主要的一種間接翻譯為轉譯。上述三種譯本皆為轉譯。轉譯作為間接翻譯的一種,其主要問題在于“在一次又一次的間接翻譯中,過多的中間環節的涉入必然導致源文固有意義的一定程度上的喪失……伴隨著間接翻譯過程中源文信息損失的基本‘遞減律’而來的必然是終極譯本中譯者創造性的發揮與添加,從而使終極譯本向目的語文學中的文學創作方向趨近。”[12]因此,三種譯本中都必然涉及到譯者創造力在一定程度的添加。
(三)就語言能力來說,三位譯者皆為漢族人
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對于藏語的陌生境地。這與中國現實環境中藏族詩歌翻譯的詩人傳統具有一定程度的承上啟下的關聯。在現有比較著名的倉央嘉措詩歌漢譯本中,曾緘、于貞志、馬輝等人皆是在不明藏語就里的情況下全憑詩人的靈光與詩性的智慧進行的漢譯。而這一傳統與深諳藏語的學者型譯者進行的詩歌翻譯傳統構成了鮮明的對照與互補。
(四)就參閱底本來說,三種譯本的底本都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面貌
僅按照譯者本人在各自譯本中的說法,廖偉棠參閱的底本涉及英譯三種,無患子參考的底本是同一位譯者的英漢譯本兩種,而鄭迪菲參閱的底本皆為漢語譯文,多達20多種。這種復雜的底本參閱的情況,從文本分析的角度來看,是“博采眾家之長”的謹慎做法,無疑是十分值得譯界推崇的。然而若從具體的文本譯本比對來做條分縷析的梳理,我們發現的情況卻有些不同:即很多譯本的產生并不像譯者在書中某處所宣稱的那樣參閱了諸多的版本,而僅僅如同《西游記》中孫悟空為朱紫國王診斷病情后所開處方在“見藥就抓”掩蓋下的偷天換日。換言之,其實譯詩真正參照的底本只是其宣稱的諸多譯本中的一個,或以其中某一個為主。如前面分析的廖偉棠的譯本,最可辨明參閱痕跡的底本當為Coleman Barks的英譯,于道泉、泰林的英譯對他的影響卻很難尋覓。若從譯者操作的層面考慮,像無患子聲稱的對于同一譯者雙語版本的參閱,其實是一種讓業內人士啼笑皆非的故弄玄虛,因為同一位譯者的譯文盡管語言不同,但不會有質的差異性存在。
(五)就譯本體例來說,三種譯本體例的設計皆呈現出譯詩附加創作(攝影)的新穎格局
廖偉棠的譯本中適時地添加了自己拍攝的藏地圖景,此外,自己創作的小說、詩歌也附加其后;無患子的譯本則添加了自己做的倉央嘉措詩歌鑒賞與旅藏手記;鄭迪菲的譯本除了嚴格意義上的倉央嘉措詩歌漢譯部分,其余各部則皆為自己托名倉央嘉措隔世戀人林微塵的個人創作。事實上,即使是在嚴格意義上的倉央嘉措詩歌漢譯部分,由于對話體、散文詩體的體例設計,其中許多文字也都出于譯者一廂情愿理解倉央嘉措詩歌深意之后的主觀添加。
以上幾點,一分為五,構成倉央嘉措詩歌三種新出譯本在不同層面投射出來的景觀;倘若合五為一,則又可以用“詩人譯詩、譯詩為詩”的傳統措辭來加以表述。因為體例的創新、藏語的陌生、底本的多元、轉譯的模式、詩人的身份等方面的因素在倉央嘉措詩歌的翻譯過程中,匯集在一起共同作用,便促成了詩人在譯詩過程中創造性的恣意發揮與詩意的盡情拓展。
四、詩歌復譯涉及的問題
復譯,作為一種翻譯現象,在翻譯歷史和翻譯市場上十分多見。對此,學界已有許多探討。如魯迅撰有《非有復譯不可》一文,在指出復譯幾種重要功能的同時,為之鼓而呼。他指出:
復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復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后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語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復譯本的[13]。
對魯迅的上述文字進行提煉,復譯的功能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擊退亂譯、造就定本、適應和促進語言變化,這些可以看作是復譯所具有的主要功能。
奈達認為,復譯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一個譯本,不管它多么接近原作,多么成功,其壽命一般只有‘五十年’。”[14]89翁顯良指出,復譯之所以必要,全在于“翻譯的目的是向讀者介紹原作,是要人家懂而不是要人家不懂,所以不能不現代化,而且要不斷地現代化,過了一定時期又得把譯過的作品重新再譯。”[14]89兩位學人談到的是復譯的時效性問題。
許鈞面對文學作品復譯本的不斷出現指出,“有一些非文學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特別是受經濟利益的驅動。”[14]89這又涉及到復譯的社會經濟學問題。許鈞在另外的場合指出,“復譯是一種文化積累”,前譯與后譯之間“不應該是一種對立的關系,而應該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是一種繼承與拓展的關系。”[9]155談及的是復譯中后譯與前譯的關系問題。
詩歌復譯,作為復譯中十分常見的一種,當然涉及以上的方方面面。同時,詩歌復譯,作為復譯中十分獨特的一種,在具有復譯共性的同時也彰顯出了一些獨具的個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曰詩無達詁。由于譯者各人先天稟賦、后天所學、析出問題、切入角度有異,對同一首詩歌的解讀必然不同。這也是現代闡釋學的精神所在。二曰譯創關聯。若論及詩歌翻譯的功用,向讀者介紹以不同語言創作的詩歌佳作,當為第一要義。然而,在介紹之外,為本鄉詩人提供參考,激發創作,生產更多的名篇佳作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何況翻譯與創作相關聯,也可作為原創性作品的靈感與語言的資源,也未可知。
五、結語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倉央嘉措詩歌新出的3種漢語譯本是在21世紀第2個10年出現的幾種新譯。這些譯本的問世是在中國步入消費社會、文化更加多元、社會環境更加寬松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與之前的一些譯本相比表現出十分明顯的時代特征,同時與前出譯本構成了相互補充、相映生輝的關系。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倉央嘉措詩歌新出的3種漢語譯本堪稱詩人譯者在文學求美的道路上的進一步探索與演繹,與學者譯者在學術求真的道路上的嘗試和努力構成一種相互補充、相映成趣的關系。從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3種新出譯本又牽涉出詩歌復譯問題的探討。詩歌復譯,在具有一般文學文本復譯特征的同時,也彰顯出了不同于其他文學文本復譯的風貌,即是詩無達詁與譯創關聯。從社會大眾傳播的角度來看,3種新出譯本則為倉央嘉措詩歌在漢語文化圈中經典化背景下的進一步世俗化提供了新的注腳①關于倉央嘉措詩歌在漢語文化圈中傳播的經典化與流俗化問題,可以參閱筆者的兩篇論文,《倉央嘉措詩歌在漢語文化圈中傳播的流俗化傾向》,刊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倉央嘉措詩歌在漢語文化圈的傳播與經典化》,刊于《民族翻譯》2016年第1期。。
[1]榮立宇.倉央嘉措詩歌翻譯與傳播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2013.
[2]廖偉棠.尋找倉央嘉措[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
[3]黃顥,吳碧云.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
[4]Barks,C.Stallion on a Frozen Lake: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M].Varanasi:Pilgrims Publishing,2004.
[5]無患子.此生雖短意纏綿:倉央嘉措情詩珍本[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
[6]羊本加.心兒隨之而去——倉央嘉措詩歌新譯[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
[7]鄭迪菲.一個人的倉央嘉措[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8]孫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9]柳鳴九,等.譯書記[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0]許淵沖.中詩英韻探勝(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1]海岸.詩人譯詩、譯詩為詩[J].中國翻譯,2005(06).
[12]榮立宇.間接翻譯及其類型芻議[J].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15(06).
[13]魯迅.非有復譯不可[A]//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翻譯研究論文集[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242—243.
[14]許鈞.翻譯論[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