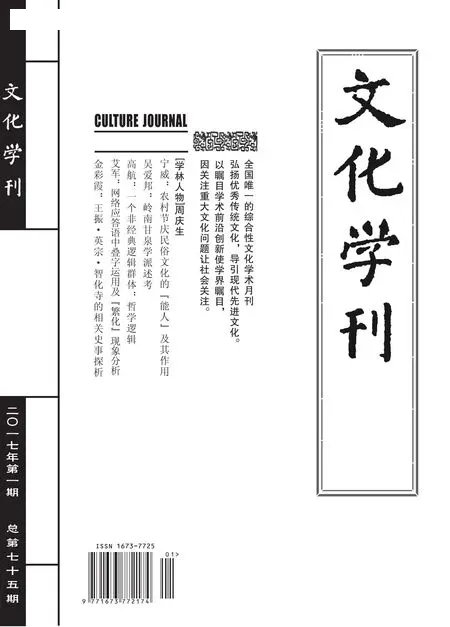喬治·奧威爾作品中動物化人物群像及其文化內涵探析
唐翠云
(唐山師范學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文學評論】
喬治·奧威爾作品中動物化人物群像及其文化內涵探析
唐翠云
(唐山師范學院,河北 唐山 063000)
奧威爾在創作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莊園》之前,就已經在其早期作品中表現出了將筆下人物動物化的傾向。奧威爾動物化的人物形象描寫經歷了從簡單服務于外貌描寫向揭示其象征意義轉化的過程。本文就主要分析奧威爾作品中動物化的人物群像,并探討其具有的文化意義。
奧威爾;動物化;人物群像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筆下的人物往往帶有象征化的色彩。奧威爾經常把他們比擬成各種動物,到其創作后期,他干脆采用寓言的形式,借動物革命諷喻人類革命,創作了《動物莊園》。他筆下的主人公常常擁有矛盾的思想,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常因清醒而在大環境中淪為孤獨者。奧威爾在塑造這些主人公的過程中表現出對尋找人與動物共同點的濃厚興趣,于是就在筆下勾勒出了動物化的人物群像,形成了奧威爾文學創作的顯著特點。
一、奧威爾作品中的動物化人物描寫
在揭露殖民統治罪惡的《緬甸歲月》中,奧威爾對人物的描寫隨處都可見到動物的影子。赤身裸體的園丁,拿著水罐走在花叢中間,“樣子活像某種吮吸甘露的大鳥[1];俱樂部管家的眼睛非常明亮,“像是狗的眼睛”[2];麥克格雷格先生肩膀寬大,總有往前伸頭的怪癖,“讓人奇怪地聯想到一種海龜”[3]。奧威爾在《牧師的女兒》中,描寫教徒梅菲爾小姐祈禱時把自己的身體對折,“像一條毛毛蟲”[4]。在《讓葉蘭在風中飛舞》中,奧威爾形容黑壓壓的上班人群往車廂里走去,像“媽蟻進洞,密密麻麻,微不足道”[5]。表現生態主題的《上來透口氣》中,主人公保靈回鄉后看到自己的初戀情人變得邋遢、骯臟,“巨大的下垂的下巴,嘴角耷拉著,眼睛深陷,還長著眼袋,跟斗牛犬一模一樣”[6]。反極權主義力作《一九八四》中,奧威爾把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的大洋國的國民比作老鼠、兔子或媽蟻:住在貧民窟破落大門內的人則就像住在耗子洞里不見天日的耗子;聽到警報聲后,人們像兔子一樣四處逃竄;在大洋國的洗腦下,人們只記得沒用的小事情,卻忘記了所有重要的事情,人們就像媽蟻一樣,只能看到小東西,卻忽略了更為重要的東西。
二、動物化人物群像描寫的演變
奧威爾對人物動物化的描寫是不斷發展的,正如泰勒觀察的那樣:“他早期的每一本小說的開頭都是稍稍描繪一下主要人物的面相,但是,這種做法并不能永遠引人入勝,因為有的面相描繪并沒有解釋其隱匿的標志。”[7]創作初期,奧威爾在《緬甸歲月》里只是將人物比擬成各種動物,目的只是為了說明人物外形的差別,還沒有引申到人物性格特征上來。而在《一九八四》里,這種純粹的外形特征比擬則具有了明顯的象征意義。如上文提到的他將大洋國國民比喻成老鼠、兔子、媽蟻,這些動物自身的特征就暗示了極權統治下,人民生活得心驚膽戰,日子黯淡無光。人物的動物化描寫,也從以前一味貶義的語體色彩轉變為包含著作者一部分的欣賞。如在溫斯頓和裘莉亞密會地點旁的院子里,有個女人不知疲倦地來回走著,一會兒放聲歌唱,一會兒又默不作聲,沒完沒了地晾著尿布。溫斯頓注意到她的姿態、粗壯的胳膊、肥大的母馬似的屁股,于是對她產生了一種神秘的崇敬。[8]因為勞作婦女的辛勞、強壯和對生活的歌唱使溫斯頓找到了極權統治下沒能扼殺的生命力,讓他又看到了未來世界的希望。奧威爾通過動物化的人物群像,構建了創作中的“動物農場”,為《動物莊園》的寫作做了充分準備。
三、動物化人物群像描寫:反觀人類文化的獨特鏡子
奧威爾動物化人物群像的描寫基于身體表達的時代。20世紀上半葉先后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們強烈感受到社會與個人、自然與人類、物質與精神以及人與自我之間的矛盾,對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感,表現在文學創作中就是使其刻畫的人物具有了非人化的特征:“人們失去了外部形態、完整性格、正常情感和邏輯也理,成為虛幻的人,機械的人,空必的人,或者變形的人。”[9]西方文學作品中出現了一大批被現代西方社會“異化”的人。如在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人類長出豬尾巴,老人長出巨大的翅膀,女孩因為不同意父母的話變成了蜘蛛;尤涅斯庫在其荒誕派戲劇《犀牛》中,讓一個小鎮上的人接二連三地變成了犀牛;阿斯圖里亞斯的代表作《總統先生》,孤獨邪惡的總統先生最后變成了一只令人厭惡的,且瀕臨滅絕的超級怪獸;卡夫卡的《變形記》,主人公格里高爾在沉重的精神壓迫下變成了巨大的甲蟲。
馬克思曾經指出:“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動物能適應其生存環境,而人則能有意識地控制環境,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有意識的控制因素卻喪失了,勞動者又被還原到動物的地位了。”[10]奧威爾通過動物化的人物群像,揭示了人體在非人的社會環境中承受的各種壓抑,以及在精神壓迫下人與動物之間的區別微乎其微。
總之,奧威爾敏銳地捕捉到了現代人各種被奴役的狀態,通過描寫人物明顯的動物特征揭示了現代文明的衰落。同時,奧威爾將人與自然緊密相連,賦予筆下人物以鮮明的動物性,使作品呈現出新奇的審美感。動物化人物群像的塑造刺激了讀者與作者在文本背景知識上的交換與互動,從而使讀者更好地領悟小說的隱含意義,并做出積極的價值評判。
[1][2][3]喬治·奧威爾.緬甸歲月[M].李鋒,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15.18.25.
[4]George Orwell. A Clergyman's Daughter,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M].London:Secker & Warburg,1997.10.
[5]George Orwell. 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3.70.
[6]喬治·奧威爾.上來透口氣[M].孫仲旭,譯.南京:譯出版社,2002.492.
[7]D.J.泰勒.奧威爾傳[M].吳遠恒,王冶琴,劉彥娟,譯.上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67.
[8]喬治·奧威爾.奧威爾文集[M].董樂山,編.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181.
[9]汪介之.20世紀歐美文學史[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76.
[10]陸玉珍.黑格爾、海德格爾與馬克思異化觀的比較[J].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8,(3):155-156,158.
【責任編輯:王 崇】
I561.074
A
1673-7725(2017)01-0078-02
2016-10-20
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廳高等學校英語教學改革重點項目“基于語料庫的后方法時代英美文學課程模式改革探究”(項目編號:1006005);河北省唐山師范學院院內科研基金項目“河北省高校英語專業英美文學教學現狀調查及對策研究調查報告”(項目編號:06C1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唐翠云(1971-),女,河北豐潤人,副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與英美文學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