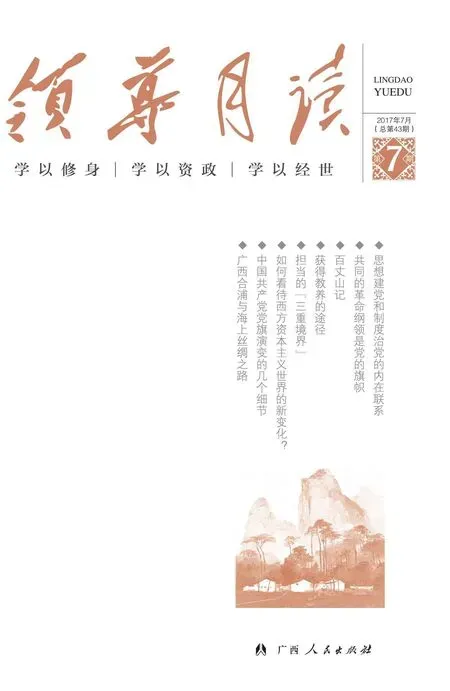張之洞之官品
蔡建軍
張之洞之官品
蔡建軍
為官之首要:忠正
張之洞 (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由科舉步入仕途,歷任學政、巡撫、總督、大學士、軍機大臣,是晚清政壇上活躍了半個世紀的風云人物。
張之洞的一生,勤于政事,一身正氣,用權不結黨,用人不謀私,始終做到心正、言正、行正、身正。
“公在晉三年,勞頓過度,心忡氣喘,須發多白。”“勤于政務,無片刻暇,詩文皆輟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忠誠勤勉的本色始終沒有改變。
為官之胸懷:擔當
在張之洞看來,在其位,就要謀其政;身為官,就要有作為。
張之洞所處時代,正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大變革時代,所謂“千古未有之變局”,內憂與外患交加,危機與生機并存。作為傳統的官僚士大夫,他不僅是一位國學大師,而且也是一個志氣過人、膽氣超人、才氣高人的改革者。
《清史稿·張之洞列傳》說張之洞“蒞官所至,必有興作”,而且“務宏大”。他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求一條穩健的改革之路。為廣興實業,增強國力,張之洞可謂絞盡腦汁,不留余力。抓工業,他創辦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和紡織四局,主持、督辦修筑蘆漢鐵路、粵漢鐵路、川漢鐵路;抓教育,他開辦實業學堂并籌劃廢除科舉制;抓軍事,他編練新軍,建設一支以鐵甲艦船裝備起來的新式海軍,加速了中國軍事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進程;抓經濟,他發行彩票、開鑄銀圓;抓國防,他維護民族利益、抵御外侮的愛國主張與振興中華實業的政績,在客觀上于民族和國家既有利,更有功……
這些都是“當驚世界殊”的大事和開風氣之先之新事。張之洞從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諸方面進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成為近代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也順應了時代的先聲,符合中國人民求強求富的抉擇。
張之洞所做的這一切,用兩個字來形容,就叫作“開放”。在一個人存政興、人亡政息的年代,張之洞以他個人的能量使得地處內地、經濟封閉保守的武漢得到了一次飛躍。毛澤東在講到中國的重工業時,曾特別提到,不能忘記張之洞。
“應省之事必須省,應辦之事必須辦,應用之財必須用。”這是張之洞求真務實的鮮明特點。無論是地方治理,還是大興洋務,他敢為人先,政績昭然,口碑在民。“天下艱巨之事,成效則俟之于天,立志則操之在己。志定力堅,自有成效可觀。”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千難不懼,萬險不辭,無不展示了他超凡的意志、超前的觀念、超人的政績。這正是張之洞思想性格、為官品格中最為光彩的一筆。
為官之境界:善任
張之洞一貫主張“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竭須得人”。他任用部屬的首要標準,是人品、才氣、氣節。他的聚才之心、容才之量、用才之能、護才之膽,常令幕僚欽佩不已。
張之洞在廣攬人才的初期,積累了豐富的用人經驗,形成了高超的馭人之術。在用人問題上,張之洞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用人原則。1880年2月,他在《邊防實效全在得人折》中指出,“破格勿計年資,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艱巨之任不限疏戚”,“南船北馬各用所長”。這些觀點,可以說是張之洞用人實踐的總結。
1884年5月,張之洞署理兩廣總督,統籌前線軍事。危急關頭,他力排眾謗,大膽起用具有軍事奇才的愛國老將馮子材。
此時,馮子材已近古稀之年。以前有人建議李鴻章起用馮赴越作戰,李鴻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可張之洞認為:“馮雖老,聞未衰;舊部多,成軍易;由欽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習;用土人,補遣便。將才難得,節取用之。”
勇士之風總是在最“吃緊”處擔當,英雄本色總是在最“要緊”處彰顯。1885年3月24日,馮子材率軍在鎮南關擊敗法國侵略者,進而攻克諒山等地,不僅扭轉了中法戰爭的局勢,而且還大長了中華民族的志氣,是19世紀中國對外戰爭中空前絕后的一次重大勝利。張之洞稱“自中國與西洋交涉,數百年以來,未有如此大勝者”,可謂“言不為過,前無先例”。
張之洞“無臺無閣,無湘無淮”,不分派系,不分畛域,唯才是舉,力求道合。時至今日,張之洞選人用人的膽識和方略,仍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
為官之本色:清廉
張之洞是一個有操守的封建士大夫。他以身作則,保持清廉,還要求各級官員不要接受屬吏的饋贈。這樣,“于陋規少一分沾潤,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做到公事公辦,不徇私情。
張之洞一生對上不行賄,對下不攤派。歷任兩廣、湖廣總督二十余年,經手的銀子數千萬,筆筆有交代,款款有著落,自己不取分文,雖然總有人指責和彈劾他“糜費巨款”,但指不出他有“中飽私囊”的任何事實。在即將坍塌的末世王朝,這是極為罕見的。
《清史稿》記載,張之洞“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云”,連他的喪事,也是靠門人幕僚送的“賻儀”辦下來的。在漢口傳教的英國人楊格非曾寫道:“張之洞在中國官吏中是一個少有的人才。他不愛財,在這個帝國中他本可以是個大富翁,但事實上他卻是個窮人。財富進了他的衙門,都用在公共事業和公共福利上。”
一個人只有從內到外散發出高山仰止的迷人風范,才能穿越千古,令人仰慕。張之洞是個好官,做官當如張之洞。
(摘自2015年4月7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