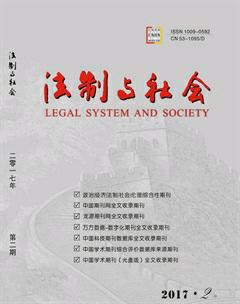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背景下死刑案件辯護意見采納機制研究報告
摘 要 死刑,作為最為嚴厲的刑罰手段,應當受到最為嚴格的程序限制以及最為公正的制度保障。這種限制和保障不僅體現在審判程序之中,也要反映在審判程序的結果——判決書中。尤其是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之后,防范冤假錯案成為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死刑案件的辦理應當更加注重辯護律師的意見,明確采納與不采納的依據,并將其體現在裁判文書中。實踐中,經分析發現,當下刑事辯護意見整體采納率不高、辯護意見質量有待提升、委托辯護效果好于指定辯護。
關鍵詞 死刑案件 辯護意見 采納
基金項目:本報告為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創新項目成果之一,項目編號2015BSCX28。
作者簡介:李逍遙,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146
在刑事訴訟中,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的堅定捍衛者,辯護律師的重要作用無需贅言。尤其在死刑案件 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面臨性命之虞,辯護工作更應當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和保障。自2012年《刑事訴訟法》進一步重視和強化對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到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死刑案件的精細化辦理已經成為不可違背的趨勢,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死刑的正確適用,最大限度地防范冤假錯案,維護社會公正。理論上,在此背景下,辦理死刑案件的法官更應當注重辯護律師所提的意見,尤其注重其發表的不同,對于合理的辯護意見應當予以采納,對于不予采納的應當重點述明不采納的原因。現實中,辯護律師提出了怎樣的辯護意見、辯護意見是否被采納、裁判說理是否充分等問題有待研究。這些問題都制約著死刑案件辯護相關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為此,本報告借助“北大法寶”和“裁判文書網”兩大平臺,收集到100份死刑案件判決,對辯護律師的來源、辯護意見的種類以及采納情況等問題分別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一、所收集樣本基本情況
總的來看,本次所收集的100份案例共有107名被告人被判處死刑,時間跨度大、涉及地域廣、各個審級均有涉及。
(一)樣本時間分布
在時間上(見表1),所采樣本從2000年到2016年大多都有涉及,其中主要集中在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生效之后。
(二)樣本地域分布
在地域上(見表2),所采樣本來源廣泛,共涉及25個省、自治區或直轄市,兼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
(三)案件審級分布
在審級上(見表3),樣本包括一審、二審、再審以及死刑復核案件,其具體情況如下:
(四)被告人認罪情況
依據這100份判決書的內容,筆者對于被告人的認罪情況進行分析,統計得出:在這些案件中,20名被告人在審理過程中明確表示不認罪,5人認罪狀況不明確,其余82名被告人均表示認罪(見表4)。
(五)律師參與死刑案件基本情況
關于死刑案件律師的來源,根據統計,在所收集的案例中,有44名被告人聘請社會律師進行辯護;54名被告人接受了法律援助辯護,其中,有8名辯護律師來自法援處或者法援中心,其余均為社會律師;5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情況從判決書中無法體現;在死刑復核案件中,4名被告人沒有辯護律師(具體見表5)。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師所占比例最大(約為53%)。其中,指定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法律援助處的律師占比較小,法律援助制度的運行主要依靠社會律師。被告人自行聘請律師的比例也超過40%,聘請律師進行辯護成為被告人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手段,即使在認罪的情況下,被告人仍選擇聘請社會律師進行辯護。值得注意的是,在收集的7起死刑復核案件中,其中4起案件沒有律師辯護,這種權利保障顯然與死刑這種最為嚴厲的刑罰不相匹配,對于加強被告人主體地位、防范冤假錯案、依法維護被告人人權極為不利。
二、辯護意見之提出與采納情況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5條之規定,辯護人的職責在于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質言之,提出科學、有效的辯護意見是辯護律師的職責所在,也是依法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的重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在學理上將辯護劃分為程序性辯護和實體性辯護,為研究之需,本報告將其細分為無罪辯護 、罪名辯護、量刑辯護(包括從輕辯護和減輕辯護)、死刑適用辯護 以及程序辯護。
(一)無罪辯護之提出與采納情況
經統計,在100份所收集的案例中,共有12件案件辯護律師提出無罪辯護,87件案件未對案件事實和證據提出異議,1份案件判決書并未出現辯護人以及辯護意見的相關信息。具體而言,提出無罪辯護的12件案件審級分布為:7件一審、5件二審和1件再審案件。在這12起案件中,8件案件中的被告人明確表示不認罪,只有4名被告人表示認罪;在律師來源上,10件案件辯護人都來源于聘請的社會律師,而提出無罪辯護的指定律師只有2人,僅占全部無罪辯護案件的16.67%。
在所收集的裁判文書中,律師提出無罪辯護的意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一是被告人不存在所指控的犯罪事實;二是被告人雖有犯罪事實,但依法不構成犯罪;三是所指控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在上述12件無罪辯護案件中,1起案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并非真正的兇手,其并非犯罪行為人,案件存在其他人作案的可能;4件案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雖然實施了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行為,但因其并非明知而為之,缺乏主觀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8起案件辯護人提出檢察機關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當依照“疑罪從無”之精神作出無罪判決。
有關無罪辯護的采納情況,據統計,上述12起案件中,法院采納無罪辯護意見的案件有3起,其余9起案件的辯護意見均未予采納。詳言之,唯一一件明確指出被告人并非行為人的辯護意見被采納,另外兩種辯護意見也各有一件案件被采納。在闡述不予采納辯護意見的理由時,5份判決書簡單地回應稱律師稱辯護意見“與審理查明的事實相悖,本院不予采納”;1份判決書回應道:“宋某某提出只打一下的事實不能認定,原判認定事實清楚”,存在將舉證責任轉嫁到辯護人一方之嫌;3份判決書針對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詳細地羅列了相應的證據材料,通過細致的分析,全面回應了無罪辯護的意見。在法院依法采納辯護意見的案件中,采納的理由更為簡單,往往只表述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關于公訴機關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辯解、辯護意見依法得以成立,應予采納”之類的語句。
(二)罪名辯護之理由及采納情況
在所有案件中,提出罪名辯護的共有12件,其中,委托辯護和指定辯護案件數均為6件。8件案件被告人表示認罪,3件案件被告人表示不認罪,1件案件中被告人認罪情況不明確。
有關辯護人提出罪名辯護之理由,大致分為如下幾種:(1)被告人是特情人員,不構成販賣毒品罪,最多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2)被告人系特情人員,且身患疾病,為減輕病痛而持有、吸食少量毒品的行為不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3)被告人沒有殺害被害人的主觀故意,而是過失導致;(4)被告人不具有殺人故意,只有傷害故意;(5)被告人只起介紹作用,沒有販賣故意,只是持有故意,應按非法持有毒品罪認定;(6)被告人只有搶劫故意,沒有強奸故意。
在罪名辯護的采納方面,上述12起案件中,僅有1起案件的辯護意見被采納,其余11起案件的辯護意見均未予采納,罪名辯護的采納率約為8.3%。法院不采納律師辯護意見的理由大致包括:(1)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的是特情行為;(2)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殺人故意明顯;(3)現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具有多次販賣毒品的行為,故可以認定金成系販毒人員,對于販毒人員被抓獲后,從其處查獲的毒品,除確有證據證明查獲的毒品并非用于販賣的之外,均應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4)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5)被告人行為屬于間接故意殺人;(6)依照《刑法》規定,聚眾斗毆中致人重傷、死亡的,應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規定定罪處罰;(7)被告人明知駕駛車輛強行奪取他人財物會造成他人傷亡的后果,仍然強行奪取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其行為已構成搶劫罪。與此相對,法院采納辯護意見的理由在于“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其有強奸故意,該辯護意見成立,予以采納”。
(三)量刑辯護之理由及采納情況
死刑案件量刑辯護主要包括從輕辯護和減輕辯護。在立法上,諸多情節,如自首、立功或者因坦白而避免重大損失等,都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而在事實上,通過分析可知,辯護律師在提出辯護意見時,也往往會在列舉有利于被告人的相關事實和證據后,概括性地提出從輕或者減輕刑事處罰的辯護意見。因此,為統計的便利,本研究不再分別統計從輕辯護和減輕辯護及其采納情況,而是統一記錄、分析。
在100份判決書中,共有82件案件的辯護人提出了從輕、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占全部案件的82%,未提出從輕、減輕處罰辯護意見的案件共15件,占全部案件的15%,2件案件判決書并未明確辯護人是否提出該辯護意見,2件案件屬于抗訴案件,辯護人請求法院維持原判。在這些案件中,律師在一審程序中提出量刑辯護意見的案件共34件,在二審中提出量刑辯護意見的案件共44件,在死刑復核程序中提出該辯護意見的有3件,在再審案件中1件。從律師來源角度來看,37個案件的辯護人基于委托關系,而45個案件的辯護人則屬于法律援助律師。
據統計,辯護人提出的量刑辯護理由的頻次由高到低排列如下:(1)被告人能夠如實供述,認罪態度好(51次);(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26次);(3)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21次);(4)被害人存在過錯(17次);(5)被告人主觀惡性較小(16次);(6)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輔助作用(12次);(7)犯罪預備或未遂(9次);(8)犯罪未造成嚴重后果(9次);(9)案件系家庭、鄰里糾紛、民間糾紛引發(8次);(10)被告人有立功表現;(11)被告人文化水平低、年齡較小、家庭貧困、法律意識淡薄等案外因素(6次);(12)被告人積極賠償(5次);(13)被告人系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2次);(14)其他因素也與被害人死亡有關(2次);(15)與同案犯相比量刑不均(2次);(16)被告人積極施救,有中止意愿和行為(1次);(17)被告人年齡存在疑點,若認定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則應從輕處罰(1次);(18)被告人獲得被害方家屬諒解(1次);(19)親屬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1次)。
從采納情況上來看,一審案件的量刑辯護意見采納情況見表6:在所收集的全部一審案件中(共39件),提出量刑辯護意見的案件總數為34件,占比為87.19%。其中,量刑處罰辯護意見未被采納的案件共15件,占提出量刑辯護意見案件總數的44.12%;意見全部被采納的案件共12件,占相應總數的35.29%;意見被部分采納的案件共6件,占相應總數的17.65%。二審案件量刑辯護意見采納情況見表7:在樣本中全部二審案件(共53件)中,提出量刑辯護的案件數為44件,占比為83.02%。其中,未予采納的案件數為31件,占所有提出量刑辯護意見二審案件總數的70.45%;全部采納的案件數為8件,占相應總數的18.18%;部分采納的案件數為5件,占比11.36%。3件死刑復核案件所提的從輕處罰辯護意見均未獲得支持;1件再審案件所提量刑處罰辯護意見被法院采納。

從法院對于辯護意見的回應情況來看,本研究將法院不采納辯護意見的理由出現的頻次由高到低進行排列,可知,不予采納的理由主要包括:(1)辯護意見與審理查明的事實不符(19件);(2)一審判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所提辯護意見已經考慮;(14件);(3)被告人罪刑極其嚴重、人身危險性大(12件);(4)辯護意見依據不足(12件);(5)被告人的民族、文化程度、法律意識包括家庭經濟狀況等均不能作為從輕處罰的理由(5件);(6)不能認定被告人存在自首情節(3件);(7)初犯不能作為嚴重刑事犯罪從輕、減輕處罰的理由(2件);(8)被告人系累犯,應從重處罰(2件);(9)不能認定被告人有如實供述情節(2件);(10)被害人無過錯(2件);(11)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立功表現(1件);(12)被害方不接受賠償,不能從輕、減輕(1件)。
分析被采納的辯護意見,可知,法院認可辯護意見的理由出現的頻次由高到低依次為:(1)被告人認罪態度好,有悔罪表現(11次);(2)被告人有自首情節;(3)被告人有立功表現(3次);(4)被告人主觀危害性不大(2次);(5)被告人積極賠償(2次);(6)因鄰里糾紛導致(1次);(7)被告人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1次);(8)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大小難以確定(1次)。此外,2份判決書中只是提到“部分辯護意見成立,予以采納”,但并未明確采納與不采納的內容和理由。
(四)死刑適用辯護及其采納情況
在死刑適用方面,辯護律師所提的辯護意見集中體現在二審程序與死刑復核程序中。在本課題收集的樣本中,共有13件案件的辯護人明確不同意死刑的適用,具體包括9件指定辯護案件和4件委托辯護案件。辯護人所提的理由基本與量刑辯護所提的理由相同。從最終的辯護意見采納情況來看,上述13個案件中,共有4件案件法院最終采納了辯護意見而依法進行改判,其余9件案件則未采納辯護人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在最終獲得改判的4件案件中,僅有1件案件是指定辯護案件,其余3件均為委托辯護,即在這13件案件中,委托辯護的效果更為明顯,意見被采納率達到75%。
(五)程序辯護及其采納情況
在樣本中,共有3份判決書涉及到了程序辯護問題,占比僅為3%。具體辯護意見與采納情況如下:在(2014)魯刑三終字第79號判決書中,辯護人指出被告人在取證程序中遭受刑訊逼供,法院回應稱“一審庭審中對被告人的訊問筆錄(未作過有罪供述)進行質證時,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均未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申請,且公安機關對被告人的訊問過程進行了錄音錄像,證實沒有刑訊逼供現象發生,故該辯護意見缺乏事實根據”;在(2013)皖刑再終字第00007號判決書中,辯護人提出法院應當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則,對于檢察機關的起訴不予受理,法院回應稱“人民檢察院先以故意傷害罪起訴又撤回起訴,后又以相同的事實以故意殺人罪重新起訴,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宋某某犯罪事實清楚,依法應予追究。不能因此而不追究宋某某的刑事責任”;在(2013)粵高法刑一終字第397號判決書中,辯護人提出偵查程序違反法定程序,對此,法院通過審查訊問筆錄,最終認定偵查程序合法有效,不采納上述辯護意見。
三、相關問題的總結與分析
以上數據的歸納和統計對于在死刑辯護中總結規律、發掘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僅僅立足于100份判決書所呈現的濃縮的、概括的內容,并未深入分析每一個具體的案件,因此,本研究只能夠較為精確地統計辯護意見的性質、數量以及被采納的情況及相關理由,卻無法針對樣本所涉及的案例評判律師所提辯護意見是否精準,也不能推斷法官作出采納或者不采納決定的理由是否充足。因此,本報告將側重于對于當前現象的總結。
(一)整體采納情況不甚理想
從整體來看,在所收集的100份裁判文書中,量刑辯護意見被采納的共有31份,死刑適用辯護意見被采納的共4份,無罪辯護意見被采納的有2份,罪名辯護被采納的有1份,有關程序性辯護的意見均未被采納。從采納率的角度來看,量刑辯護意見的采納率最高,為37.80%,其余依次為死刑適用辯護意見(30.77%)、無罪辯護意見(25%)、罪名辯護意見(8.33%)和程序辯護意見(0%)。在被提及最多的量刑辯護意見中,一審案件量刑辯護意見被采納情況明顯好于二審程序:如上文所統計,在一審程序中,有關量刑的意見被全部采納或被部分采納的比例為52.93%,遠高于二審程序中的29.54%。這說明,在一審案件中,過半數的案件,有關從輕、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是被法官采納了的。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一審案件中,仍有44.12%的量刑辯護意見未被采納,這一比例高于被采納以及被部分采納的比例;而在二審程序中,超過70%的案件最終未采納量刑辯護意見。這種較低的采納率不但侵蝕了公眾對律師行業的信賴基礎,還影響到公民權益的有效保障,更危害到律師行業的健康、穩步發展以及我國“依法治國”理念的貫徹與落實。
(二)辯護意見的質量有待提升
從法院不予采納的理由視角來看,導致辯護意見不被采納的核心因素在于辯護意見的質量不高。根據上述統計,法院拒絕采納辯護意見的首要原因在于辯護意見與審理查明的事實不相符,比如,在提出量刑辯護意見的案件中,就有19件案件因此而未被采納,12份無罪辯護意見中也有7份因此未予采納。除此之外,法院不予采納辯護意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所提的辯護意見依據不足。例如,在量刑辯護意見未被采納原因的統計中,該原因就出現在判決書中多達12次。其他原因,如不能認定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如實供述等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也占據了相當的比例,而這些原因的背后仍舊是辯護律師所提的意見缺乏事實依據或者與事實相悖。
從律師所提的辯護意見的內容角度來看,辯護意見重實體辯護而輕程序辯護、重量刑辯護而輕定罪辯護。在所收集的樣本中,提出程序性辯護的案件僅有3件,只占全部樣本的3%。這并不意味著剩余97件案件全部不存在程序瑕疵,也不是律師素質不高難以發現程序問題,而是部分律師忽視了、甚至放棄了程序性辯護的機會。盡管2012年《刑事訴訟法》新增了針對偵查人員取證行為合法性審查的“程序性裁判”機制 ,程序性辯護逐步興起,但調研顯示,程序性辯護手段似乎并沒有在律師界獲得廣泛運用,程序性辯護的意見也難以受到法官的認同。相反,絕大多數律師仍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實體辯護之上,試圖在現有事實和證據的基礎上,尋求辯護的狹小空間。在罪與罰的辯護側重點上,超過80%的律師都選擇了量刑辯護,而提出無罪辯護、罪名辯護與程序辯護意見的案件僅有23件。在提出量刑辯護的理由時,律師也側重強調對量刑只具有參考性質的品格證據,如“被告人如實供述,認罪態度好”、“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被告人主觀惡性小”等,這些辯護意見在一審程序中還能被法官酌情采納,但在二審程序中,則極少被法官所接納。上述統計也佐證了有些學者對于辯護制度的有關批判:辯護律師在法庭調查階段很少對公訴方的有罪證據和量刑證據提出質證意見;在法庭辯論階段極少做無罪辯護和程序性辯護,大都做量刑辯護;而在量刑辯護方面,律師極少提出新的量刑情節,而主要通過查閱案卷或者當庭聽取公訴方提交的證據,來發表簡單的量刑意見。辯護律師經常強調的量刑情節有“認罪態度”、“偶犯”、“有悔改表現”、“退贓”等,一般只是籠統地建議法院“從輕處罰”。結果,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對法院的判決影響甚微。
上述論證都表明,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應當更加注重案件事實,應當充實自身的事實依據,應當更加注重程序性辯護,應當更為盡職盡責,切實把握被告人的寶貴的辯護機會,保障被告人的重大利益。
(三)委托辯護律師的辯護質量略好于指定辯護
從所有案件的律師來源來看,超過半數的案件由指定社會律師辦理,委托的辯護律師約為41%。在樣本中,這兩類來源的律師數量相近,也為兩者之間辯護質量對比提供了量的基礎。在被提出最多的量刑辯護意見采納情況上,當事人委托辯護人為其辯護的共37件,辯護意見被采納或者被部分采納的共有16件,約占此類案件的43.24%;相比之下,在45個由指定辯護律師辦理的涉及量刑辯護的案件中,共有14件案件中的辯護意見被法官采納或者部分采納,被采納率約為31.11%。在12個提出無罪辯護的案件中,至少兩個案件的辯護人是受委托的律師,另外一個辯護意見被采納的案件的律師來源不明。在12件提起罪名辯護的案件中,最終辯護意見被采納的案件的律師同樣是受委托的律師。同樣地,在提出死刑適用辯護意見的13份判決書中,指定辯護的案件為9個,最終辯護意見被采納的僅有1個,采納率約為11.11%,而在余下4個委托辯護的案件中,最終有3份判決書采納或者部分采納了辯護律師的意見,采納率為75%。盡管統計的數據容量較小,存在不少偶然因素,導致統計的數據不夠準確,但是,根據統計的結果,可知,從整體上看,委托律師的辯護意見采納率要略好于指定律師,而在某些方面,委托律師辯護的效果則明顯更好。
注釋:
本文所指的“死刑案件”,是指罪刑極為嚴重,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的案件,有的故意殺人案件,如(2014)崇刑初字第374號,雖沒有被判處死刑,但也屬于本調研研究的范圍。
此處無罪辯護,包括辯護人認為部分行為應屬于無罪的情形。
此處死刑適用辯護,是指辯護律師是否對罪名無異議,不同意死刑適用的情形。
陳瑞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中國模式.中國法學.2010(6).
陳瑞華.刑事辯護的理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