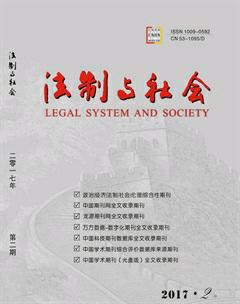從“新政”看直播監管的升級
摘 要 2016年11月4日《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出臺,通過建立實名制、黑名單制及信用等級制度,從資格限制到事中控制,再到對使用者將來資格和行為的規制,首次從全過程和多層次對網絡直播進行了規范。這些制度彌補了ISP雙規則在直播監管適用上的空白,且有利于建立從政府到平臺、從平臺到用戶,三方協同管理的直播監管體系。
關鍵詞 網絡直播 避風港規則 紅旗規則 平臺責任
作者簡介:張墺多,中國政法大學。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164
直播并非新鮮事物,但網絡直播卻是方興未艾。去年是網絡直播元年,盈利性網絡直播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建立,加之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直播從PC端延伸至手機端,“全民直播熱”由此興起。但與此同時,這個新興的互聯網行業也因缺乏制度監管而亂象叢生,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許多主播言語污穢、跌破底線只為刷禮物,有些甚至以此引流從事不法活動;第二,直播內容魚龍混雜,造人、性暴露、窺探隱私等系列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線的內容比比皆是,這在秀場類直播中尤為常見;第三,用戶彈幕互動中,發表內容許多涉黃涉暴力,挑逗、宣泄、起哄等網絡行為隨處可見。
為全面而系統地整治網絡直播中出現的上述現象,國家網信辦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通過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該規定從直播服務使用者注冊到對違規違法內容的處理,均作了詳細的規范,這也是第一次對網絡直播從初始環節到結果環節進行了全過程的制度完善。較之于之前對于直播平臺的責任只得利用“避風港規則”及“紅旗規則”予以追責,本次新規是對這兩項規則的有效補充與完善。
一、ISP雙規則在直播監管中的缺陷
(一) 對直播平臺的性質界定
如今,一些直播平臺制定了諸如版權保護投訴的指引,這些指引對網站提供的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界定。比如,斗魚在指引中聲明:“斗魚根據平臺用戶意愿提供相關視頻的上載及傳播,不事先審核前述被上載的視頻內容。”由此可知,各大直播平臺都將自己定位于服務提供商,也即ISP。
則長期以來,依《侵權責任法》第36條 所確立的兩項規則——“避風港規則”和“紅旗規則”,就應當適用于對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之中。
(二) ISP雙規則在直播監管中的缺陷
1.盈利模式致使平臺濫用“通知刪除規則”
新規生效前,多數直播平臺尚未制定自律公約,甚至沒上述類似權利指引和舉報渠道。在一些發展較為完善的平臺上,避風港規則被明文載入到了相關聲明或指引之中,并為客戶提供了模板和渠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平臺僅是在侵犯版權這個方面做了聲明,并就該項規則的運用進行了細化。表面上看,這些平臺似乎很看重自己作為管理者的責任,其實不然,因為在直播平臺上版權侵權實屬罕見——依《著作權法》之規定,只有侵犯了被法律所保護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等,方屬侵犯版權。然而在“進入門檻低,人人皆可當主播”的直播平臺上,僅需簡單設備、張嘴說話,甚至只是對著屏幕,就足以引來圍觀,這比侵犯版權成本低,也是占比很大的顏藝類和秀場類直播的通常形式。
與此相比,平臺真正應該將避風港規則細化的方面,在于對違規違法內容和隱私侵權這兩方面。從被直播吃面條到潛入女生宿舍搞直播,從色情表演到直播造人,關于直播侵權、違法的報道數不勝數,其內容讓人瞠目結舌。對此,平臺并非沒有意識到,而是有意縱容,并利用用戶知法但未必懂法而將部分應澄清的通知刪除事由隱去了。
這樣做的核心原因在于平臺的盈利模式。目前直播平臺的盈利模式較單一,只有兩種:第一,流量;第二,與主播分成。這就使得平臺對主播的依賴很大,加之主播行業白日化競爭,要想聚集粉絲,刷到禮物,就需迎合觀眾口味——拉低下線為其主要手段,則平臺也只得對此打馬虎眼。不過這只是新規出臺之前,平臺因沒有相關規定而鉆了制度的空白。
2.網絡直播的特征影響“紅旗規則”的效用
“紅旗規則”的原意在于:如果服務提供者知道用戶正在實時侵權行為,則應主動采取必要措施,否則就與該用戶承擔連帶責任。但這一規則在直播監管中效用欠佳,原因在于兩點:一是由于前述盈利模式的限制和制度的欠缺,導致平臺管理者不作為;二是由網絡直播的傳播特征造成的。
網絡直播一個重要的傳播特征就是實時性,這意味著即便監管部門責令平臺關停直播間、斷開鏈接并刪除內容,也無法消除關停前那段時間內視頻對用戶所造成的影響,更為嚴重的是,該內容可能以截圖或轉錄的方式流于網絡之中。以“斗魚直播造人事件”為例,事發是在凌晨卻引來了數千人圍觀,不少網友還在微博等社交平臺上公布了大量截圖,而斗魚官方卻是在被舉報后才關閉了該直播間。鑒于凌晨這一特殊時間段一個直播間卻集聚了眾多觀眾,斗魚的審查部門顯然有義務進行監管。
此事反映出紅旗規則在直播監管中效用不佳:首先,由于缺乏制度規范,使得紅旗規則實際上缺乏約束力,為追求盈利,平臺對違規違法直播多不作為;其次,紅旗規則的懲罰是對事后不作為的問責,但無法消除問責之前直播所造成的影響。
二、新規對ISP雙規則的補充實效
(一) 對主體責任的強化
依前文所述,直播平臺默示違規違法內容傳播和規避相應責任,根源在于盈利模式及系統性規范的缺失。鑒于此,新規首先從機制建設、形式標準及審核管理三方面,對平臺內容審核進行了系統規范 。其中,實時監管制度是針對直播傳播特征的應對之策,是平臺服務提供者在規定生效后所應承擔的一項義務,則這之后如再發生類似于“造人”這樣的違法事件,平臺就不得再以其不滿足紅旗規則之規定為由,來規避平臺責任。其次,新規關于平臺建立信用等級管理體系 的規定,使平臺提供的服務和進行的管理與發布者信用體系掛鉤——這打破了以往平臺對主播的過度依賴。雖然單一的盈利模式仍是直播平臺的軟肋,但信用等級體系與下文將提及的黑名單制度,共同給主播的資質及行為給予了雙重限制。則平臺可因此放下對主播“跳槽”的顧慮,而逐步形成自身健康而中立的經營方式。
新規對主播的規范,核心在于資質。全民直播之所以出現,一是由于手機的普及,二是由于準入門檻低。而新規中第六條 的規定,無疑將使該現象成為歷史。今后,主播如果是通過網絡表演和網絡視聽節目等方式進行直播,則必須取得法律法規規定的相關資質。其中網絡視聽節目包括播放自辦節目,此方面資質的限制主要將對秀場類的主播造成影響。而秀場類直播目前正是獵奇內容的聚集地,其中一些自辦節目很容易對觀眾,特別是未成年帶來負面示范效果。例如,在快手直播中,有個主播自辦了一個節目叫“瘋狂的舌頭”,專門表演用舌頭舔舐公共場所最臟的地方。則今后這種自辦節目將在新規限制范圍內。
此外,彈幕是直播中主播與觀眾互動的方式之一,但也成為了語言暴力的工具。新規賦予了服務提供者實時監管的權力和責任,同時將彈幕納入了相關部門證據收集的范圍。雖然彈幕文化的初衷是為擁有相同興趣的用戶提供一個交流且相對私密的空間,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其放任不管。一些主播跌破底線的行為歸根到底是為了獲得關注,滿足眾人的喜好,則不加規范的彈幕挑逗將助長這一趨勢,最終污染的仍是用戶共同的視聽環境。
(二)全程監管實現源頭治理
雖然“避風港規則”和“紅旗規則”已經成為了解決網絡平臺糾紛慣用標準,但對于新興的網絡直播平臺來說卻難以發揮最好效用,因為它尚缺乏規范的運營模式,又被單一的盈利模式所束縛,再加上實時傳播與實時互動,則事后的追責制度是無法完全消除影響,以及對未來的直播行為進行有效的規制。
因此,在網絡直播監管中,有兩點是該類平臺監管的特色:一是建立實時巡查機制,這是目前針對直播實時傳播和互動特征最為行之有效的手段;另一個是對使用者資格的限制,這是避免實施了嚴重侵權或違法行為的用戶利用其它賬號繼續使用直播的關鍵。新規對此確立了實名制及黑名單制度 ,不僅賦予了平臺管理者切實的權限,也明確了主播和用戶的責任。
當然,實名制對于互聯網的用戶來說,一直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原因在于:正是因為匿名,使得人們在互聯網中擁有了更多的言論自由;此外,人們擔心實行實名制后,一旦出現信息泄露或黑客攻擊,則個人信息及隱私將無法獲得保障。但鑒于網絡直播行業剛剛起步,則難免存在諸多問題,實名認證是對使用者權利的保護,也有利于避免類似的違規違法行為重復發生。
新規權衡以上兩點,在二十條做了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后臺實名、前臺自愿”,這既維護了用戶自由言論的空間,又保證了使用過程和互動環節的平臺秩序。此外,對主播申請條件的具體規定和備案要求,有助于規范主播職業,強化其道德和責任意識,使這個職業在經過惡性競爭階段后,能常態化發展。黑名單制度則是對實名制的補充和落實,其中規定了:禁止被記入黑名單的使用者重新注冊賬號 。這將根治目前主播被封停賬號后,以另一種虛假身份重回平臺的惡性循環。
三、從多方監管到平臺自律
綜上,在ISP中慣用的“避風港規則”和“紅旗規則”因具有事后性,而無法在網絡直播平臺上發揮切實的效用,《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通過明確主體責任和確立實名制、黑名單制及信用等級制度等多向機制,對ISP雙規則實現了如下補充:首先,規定平臺建立實時巡查機制,縫合了前兩種規則所無法規制的事前和事中行為,從而及時消除影響,阻斷網絡負面傳播的滲透;其次,實名制和黑名單制度的組合運行,起到了源頭控制的作用,因而具有了追責效力延伸至未來的效果,而傳統ISP規則僅能規制之前和當時的行為;最后,有關信用等級體系及平臺公約的規定,則有利于增強平臺及使用者的自律意識。
如今,制定社區公約在ISP平臺上已成為新趨勢,它在促進用戶與平臺協作管理的同時,也有利于在維護言論自由空間的同時保障網絡環境的健康與和諧。
注釋:
第36條: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2009年12月26日.
第7條: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落實主體責任,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人員,健全信息審核、信息安全管理、值班巡查、應急處置、技術保障等制度。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直播服務的,應當設立總編輯。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建立直播內容審核平臺,根據互聯網直播的內容類別、用戶規模等實施分級分類管理,對圖文、視頻、音頻等直播內容加注或播報平臺標識信息,對互聯網新聞信息直播及其互動內容實施先審后發管理。第8條: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具備與其服務相適應的技術條件,應當具備即時阻斷互聯網直播的技術能力,技術方案應符合國家相關標準。
第15條: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建立互聯網直播發布者信用等級管理體系,提供與信用等級掛鉤的管理和服務。
第6條:通過網絡表演、網絡視聽節目等提供互聯網直播服務的,還應當依法取得法律法規規定的相關資質。
第12條1款: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按照“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原則,對互聯網直播用戶進行基于移動電話號碼等方式的真實身份信息認證,對互聯網直播發布者進行基于身份證件、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等的認證登記。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對互聯網直播發布者的真實身份信息進行審核,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分類備案,并在相關執法部門依法查詢時予以提供。
第15條2款: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建立黑名單管理制度,對納入黑名單的互聯網直播服務使用者禁止重新注冊賬號,并及時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