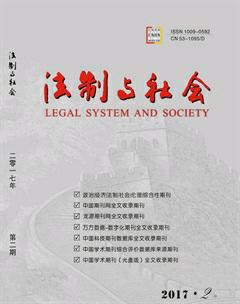完善我國巡回法庭運(yùn)行機(jī)制研究
摘 要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lǐng)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要從制度上解決司法不公的問題,則要進(jìn)行司法體制改革,故而《決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shè)立巡回法庭,審理跨行政區(qū)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產(chǎn)生背景及價值為研究視角,探討巡回法庭的區(qū)域設(shè)置、受案范圍等內(nèi)容,以期為完善巡回法庭運(yùn)行機(jī)制提供有益參考。
關(guān)鍵詞 巡回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 運(yùn)行機(jī)制
基金項目:河北政法職業(yè)學(xué)院2016年院級重點(diǎn)課題,課題名稱:完善我國巡回法庭運(yùn)行機(jī)制研究,課題編號:ZF20160608。
作者簡介:孫麗虹,河北政法職業(yè)學(xué)院。
中圖分類號:D926.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191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是中國司法改革進(jìn)程中受人矚目的成就,展現(xiàn)出我國司法改革的創(chuàng)新活力。巡回法庭關(guān)乎我國司法公正領(lǐng)域,對充分發(fā)揮審判機(jī)關(guān)職能作用,維護(hù)祖國法政統(tǒng)一,遏制地方保護(hù)主義及實(shí)現(xiàn)我國依法治國目標(biāo)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國巡回審判制度運(yùn)行以來,貫徹落實(shí)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和四中全會精神,獲取豐碩果實(shí)。當(dāng)然,任何一項改革方法均在艱難爬行中不斷摸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經(jīng)過一年也發(fā)現(xiàn)諸多問題,進(jìn)一步完善巡回法庭運(yùn)行機(jī)制,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diǎn),使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能更好地發(fā)揮其在理論與實(shí)踐方面的價值。
一、巡回法庭的制度源流
追溯到中國古代相關(guān)記載,并不存在“巡回法庭”的蹤影,類似巡回法庭的記載少之又少。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同地區(qū)已設(shè)立巡回法庭及審判制度。1932年,我國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該文件提出要到案件發(fā)生地審理,以吸收多數(shù)群眾觀看旁聽相關(guān)內(nèi)容,進(jìn)一步確立巡回審判制度 。隨之,各地先后發(fā)布文件并確立巡回法庭并確定巡回審判制度。其中,受多數(shù)人肯定的“馬錫五審判”,以深入分析、樹立群眾路線、兼顧民情為依據(jù),促使巡回法庭及審判制度達(dá)到鼎盛時期。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方式被傳承下來。1950-1982年,分別實(shí)施《人民法院組織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等,這些文件均對巡回法定及制度做出相關(guān)規(guī)定 。
2005年,我國發(fā)出《關(guān)于全面加強(qiáng)人民法庭工作的決定》,這一決定標(biāo)志著巡回審判制度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從上述關(guān)于巡回法庭及審判制度發(fā)展史可知,在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設(shè)立前,巡回法庭就是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在其管轄范圍按期到達(dá)或不定期到達(dá)特定地點(diǎn)流動審理,這些特定的巡回地點(diǎn)主要為案件發(fā)生地區(qū)、當(dāng)事人居住地或便于人民旁聽地,因開庭審理案件設(shè)立的法庭即為巡回法庭。
2001年,王利民教授在其編著的《司法改革研究》中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在各省、市高級人民法院派駐法官,以被派駐法官組建巡回法庭,審理跨越省市及自治區(qū)的各種特定案件 。2003年兩會時期,擔(dān)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李道明、趙世杰等人提到,為維護(hù)國家法制統(tǒng)一,有效克服地方保護(hù)主義,最合理的改革方法是設(shè)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以此管轄死刑復(fù)核及跨區(qū)重大民商事和重大疑難案件,并向大會提出相應(yīng)建議。因多種因素的影響,上述建議并未付諸實(shí)施。2014年,黨十八屆四種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必須設(shè)置巡回法庭,以此審理跨行政區(qū)重大行政或民商事案件。同年12月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最高人民法院設(shè)立巡回法庭試點(diǎn)方案,并與2015年12月正式啟動該項工作,先后在廣東省深圳市、遼寧省沈陽市設(shè)置第一、二巡回法庭。
二、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價值分析
(一)巡回法庭追尋司法機(jī)關(guān)依法獨(dú)立行使職權(quán)
現(xiàn)階段,我國法院、檢察院依托行政區(qū)域設(shè)置,人事編制、經(jīng)費(fèi)設(shè)施等均掌握在同級權(quán)利和行政機(jī)關(guān)手中,對于地方領(lǐng)導(dǎo)的壓力,缺乏抵制干預(yù)的氣勢。因此,四中全會提出設(shè)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以此辦理跨越行政區(qū)域的重大民商事或行政案件。在各級法院人員任免時,同級人大選舉產(chǎn)生同級別法院院長,同級人大常委會具有任免副院長、正副廳長和審判員的職能。我國創(chuàng)設(shè)這項政治制度初衷是要保證各級法院之間相互獨(dú)立,保障司法公眾,進(jìn)而維護(hù)司法的公信力。此外,這項措施有利于司法機(jī)關(guān)擺脫地方政府的鉗制,達(dá)到有勇氣、有能力獨(dú)立辦案的效果。
(二)巡回法庭的最終價值取向——公平正義
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以公開促進(jìn)公正是不爭的事實(shí),公正、公開與司法公正效果存在必然的聯(lián)系。《決定》指出:“必須構(gòu)建開放、透明、便面的陽光司法機(jī)制,從而推進(jìn)審判、警務(wù)、檢務(wù)及獄務(wù)公開,杜絕暗箱操作” 。分析近些年多數(shù)案件可知,司法系統(tǒng)逐漸由自身獨(dú)立轉(zhuǎn)變成身不由己,這種情況違背其創(chuàng)設(shè)初衷。
十八屆三中全國指出,省級下設(shè)的地方法院人財物均由中央管理。2014年中央改革領(lǐng)導(dǎo)小組再次強(qiáng)調(diào)該指標(biāo),進(jìn)而打破地方司法保護(hù)主義的決定。這項改革措施不包含省級高院人財物中央統(tǒng)一管理,此時,省級法院一直受制于同級黨政機(jī)關(guān),省級法院地方化的問題依然存在。基于上述背景下,設(shè)置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成為解決省級法院不統(tǒng)一管理最佳的措施。省級法院審理跨區(qū)域案件時,出自保護(hù)本省利益的私心出現(xiàn)偏頗本省當(dāng)事人的判決。同時,巡回法庭生理案件也能防止地方政府施壓法院不予立案或強(qiáng)行下達(dá)指令批示等行為,這種做法保證審判的公平、公正。
三、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運(yùn)行機(jī)制
(一)巡回法庭的區(qū)域設(shè)置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農(nóng)業(yè)大國,東西部發(fā)展水平差異較大,且人口分布并不均勻。處在西部多數(shù)農(nóng)村偏遠(yuǎn)地區(qū),交通運(yùn)輸不便利,群眾出行不方便,訴訟能力交叉,這種情況與“誰主張、誰舉證”司法制度并不匹配,巡回法庭能有效化解這種矛盾,是處理糾紛最佳的方法。由中國發(fā)展現(xiàn)狀可知,開展巡回法庭審判制度的地區(qū)多地處偏遠(yuǎn)、經(jīng)濟(jì)條件落后的農(nóng)村,這些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不高,交通條件不便利,人民很難承擔(dān)訴訟所需的人力、財力和物質(zhì),但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法院在主城區(qū)開展巡回審判制度的例外情形。因?qū)嵤┭不貙徟兄贫鹊貐^(qū)主要在農(nóng)村和人員稀少、交通不便的偏遠(yuǎn)地區(qū),上述地區(qū)人員流動極少,相互間經(jīng)濟(jì)交易關(guān)系非常簡單,因此,上述地區(qū)巡回審判制度受理的案件主要是婚姻糾紛、財產(chǎn)損害賠償就行、土地權(quán)屬糾紛等。而部分新興的巡回法庭,例如:勞動爭議巡回法庭、知識產(chǎn)權(quán)巡回法庭等,受理案件集中在某個特定類型。同時,部分法院將當(dāng)?shù)赜绊懘蟆傩贞P(guān)注度高或典型的案件例如巡回審判范圍。
(二)巡回法庭的受案范圍
巡回法庭的職能及目標(biāo)影響受案范圍確定,這種影響處于類似價值引導(dǎo)方面,并無法具體判定受案范圍,只能授予合理的受案方向。《規(guī)定》第2、4條依次從受理和暫不受理兩個方面,進(jìn)一步明確巡回法庭受理范圍。遵循穩(wěn)妥有序、價值平衡等原則確定巡回法庭受案范圍,當(dāng)巡回法庭試點(diǎn)成熟后,可依據(jù)實(shí)際情況擴(kuò)大巡回法庭受案范圍。《巡回法庭若干規(guī)定》第3條明確巡回法庭審理或辦理巡回區(qū)域內(nèi)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如下案件:(1)全國范圍之內(nèi)重大、復(fù)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重大復(fù)雜案件要依據(jù)具體案情、行政干擾程度的方面進(jìn)行綜合判定。(2)不服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的判決,裁定提出上訴的案件;(3)全國范圍內(nèi)具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4)不服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的罰款拘留決定申請再次復(fù)議案件。綜合司法解釋受案范圍可知,極易獲取巡回法庭現(xiàn)行受案范圍考核因素。巡回法庭的性質(zhì)決定其必然沿襲本部受案范圍,且受審級、管轄制度多方面限制,巡回法庭并未在受案方面有所突破。相對于本部來說,巡回法庭受理案件比較簡單,并不存在特殊司法意義案件,這種做法不僅能保障案件分流,也能快速實(shí)現(xiàn)職能分工后本部與巡回法庭的使命。此外,在設(shè)定的受案范圍中,部分案件進(jìn)入最高人民法院的視野,例如:全國重大、復(fù)雜案件,巡回法庭受理比較合理。目前,第一、二巡回法庭現(xiàn)設(shè)置13名法官,每個巡回法庭下轄3-5個省份,需要設(shè)置7-9個巡回法庭,并配備約120名法官。隨著試點(diǎn)地區(qū)的深入,案件量隨之增加,各巡回法庭預(yù)計增加160-180名左右的法官 。
(三)巡回法庭與最高院本部的關(guān)系
眾所周知,巡回法庭隸屬于最高人民法院,而巡回法庭并非一級設(shè)立的組織。因此,巡回法庭必須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統(tǒng)一的管理和派遣,巡回法庭所用的辦公設(shè)施及物質(zhì)保障,也不受地方政權(quán)機(jī)構(gòu)的管理。由巡回法庭管轄案件的范圍可知,其具有相對獨(dú)立性的特征。巡回法庭普遍設(shè)立以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要將工作重心轉(zhuǎn)移至監(jiān)督指導(dǎo)層面,對統(tǒng)一法律適用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和示范價值。除此以外,來自各專門及地方中級法院的上訴審案件由巡回法庭管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法官要處在流動之中,例如:三年為最長期限,使最高人民法院本部法官全面巡回一遍 。這種做法能有效預(yù)防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官時間長逐漸被地方化,以此造成司法腐敗的情況。同時,這種方法有助于審判的公正權(quán)威,使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健康成長。由于巡回法庭事物比較繁瑣,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巡回法庭事物協(xié)調(diào)中心,全面協(xié)調(diào)、統(tǒng)籌巡回法庭人員派遣、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案件管轄等事項。
綜上所述,巡回法庭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產(chǎn)物,在審判權(quán)利運(yùn)行、人員分配、信訪等方面均有重大的改革意義。本次研究對最該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設(shè)立背景、價值等方面展開探討,提出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運(yùn)行機(jī)制的方法,以期為巡回審判制度的完善貢獻(xiàn)一份力量。
注釋:
芶冰皓.論巡回法庭的設(shè)立.黑河學(xué)刊.2015(5).71-73.
王潔、劉超.淺論最高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完善.法制與社會.2016(4).44-45.
傅福興、李伊凝、牛強(qiáng),等.試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設(shè)立.法制與社會.2015(32).196-197.
張海楓.最高法院設(shè)立巡回法庭的價值分析——以去司法地方化為研究視角.法制博覽.2016(8).56-58.
方斯遠(yuǎn).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建構(gòu).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5,33(2).61-69.
縱博.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設(shè)立背景、功能及設(shè)計構(gòu)想.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5,33(2).7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