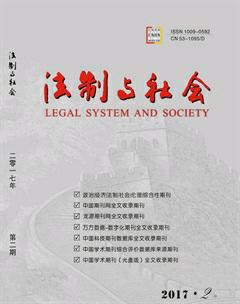朱希祖的學術經歷與史學思想
摘 要 朱希祖,民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他曾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著名高等院校任教,在史學、目錄學、校讎、文獻學、考古、藏書等研究領域均有造詣。本文就朱希祖的學術經歷與史學思想進行考察,總結其治學成就與特點,展示其在中國史學史領域的地位,客觀評析其在史學界的作用與影響。
關鍵詞 朱希祖 學術經歷 史學思想
作者簡介:李琳,河北大學歷史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中圖分類號:G649.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246
談及“新史學”,時人首先會想到梁啟超。梁啟超一直被學界認同是我國史學史學科的開創者。受其號召和影響,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走進史學界,相關論著也相繼出現,成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起源。然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第一人,其實并非梁啟超。最早從學科意義上探討史官、史家、史學等史學史基本內容的人是朱希祖。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鹽人。其父為朱永檠,以教書為業。朱希祖幼年隨父在家塾讀經史,十四歲父親因病去世,從此承擔家中重任,邊刻苦學習邊謀生掙錢。之后,朱希祖先后考中秀才與廩生,以授徒講學來維持家中生計。然而,清末時局的動蕩令其改變了求學之路,他開始習學英語,在1905年的浙江官費選派百名留日師范生的考試中中第。后赴日本東京留學,專修歷史,走上治史之路。本文就朱希祖的學術經歷與史學思想進行考察,總結其治學成就與特點,展示其在中國史學史領域的地位,客觀評價其在民國史學界的作用與影響。
一、學術經歷
(一)從章門高第到入職北大
朱希祖東渡日本后,開始留學生活。1908年師從章太炎,與錢玄同、馬幼漁、沈兼士、周作人等成為最早的“太炎弟子”,“常至民報社,別在大成學校請本師講授經子及音韻訓詁之學”。 由于他勤奮治學,頗為章太炎所青睞與栽培。章太炎《自定年譜》中寫道:“逖先博覽,能知條理。” 起初,朱希祖等人均追隨章太炎以小學為主要研究方向。之后,朱希祖將研究方向轉為南明史與戲曲,而他的南明史研究也是受到章太炎的影響而發端。1909年朱希祖歸國,與魯迅等人一同就職于浙江兩級師范學堂,講授文學史。1910年,朱希祖應嘉興中學監督范古農之邀,前往嘉興中學任教。這期間,朱希祖與章太炎多有書信往還,學術也大有進境。辛亥革命后,朱希祖被選舉為故鄉縣民事長,推新政,辦學校。1912年3月,又應沈鈞儒之邀,前往浙江省教育廳任職。
1913年,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國語讀音統一大會,以審定國音的基本音素。與會代表意見紛紛、各執己見,主要的三派分為偏旁、符號與羅馬字符。此時,作為浙江省兩名代表之一的朱希祖,力主采用古文篆籀徑省之形,取名為“注音字母”,得到與會人員的認可,一時間名震士林。 朱希祖等人的提議獲得了各代表的通過,此為國語之基礎,屬于中國首套漢字注音方案。
讀音統一大會召開之時,何燏時任北大的代理校長。這期間,北大的主流文風是由清末延續下來的桐城派勢力所掌控。西學的漸入、時代的變遷等導致北大內部發生人事變動,且章太炎享有的崇高聲望,使得太炎弟子逐漸入流北大。國語讀音統一會的召開,為朱希祖贏得很大的學術聲望,他在沈尹默的推薦下,首先被聘請出任北大預科教授。之后,沈兼士、馬裕藻等人也相繼受聘。
(二)從北大到中央研究院
朱希祖被聘為北大預科教授后,不久由預科轉文科。此時,北大的學風已由“章門學風”取代了老一輩的桐城派,朱希祖等章門弟子也相繼成為了北大的著名教授。1917年,時值胡適與陳獨秀等積極倡導文學革命,陳獨秀出于沈尹默的推薦被聘為文科學長。此間,北大增設了史學門,陳獨秀有意聘朱希祖為史學門主任,但因朱希祖意在文科方面有所作為,暫不愿進駐史學而擱置。兩年后的五四運動之際,史學門主任始由康寶忠擔任。同年,北京大學改科為系。1920年夏,康寶忠逝世,蔡元培推薦朱希祖擔任史學系主任。
這時,北大因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也已然成輿論之中心。除了胡適等“新人物”,包括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在內的諸多太炎門生大都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參與到了文化革命運動中來。朱希祖積極響應,也在《新青年》上連續發表《白話文的價值》和《非“折中派的文學”》兩篇文章,以明確表態。1919年,由胡適領銜,包括朱希祖、馬裕藻、錢玄同等教授聯名向教育部統一國語籌備會提出了關于新標點符號議案,得到批準。次年,朱希祖又聯合多人成立了文學研究會。1922年他同蔡元培、沈兼士等一起為北大爭取到了原由歷史博物館所藏的四分之三的明清內閣檔案的委托整理權,成立了后來的明清史料整理會。1923年到訪陜西中原古跡,收集漢唐史料。此外,他還兼任《國學季刊》的主編,積極參與學會組織的成立,在1928年成立中國史學會并擔任學會主席。
朱希祖入史學系后,他以新時代史學思想為指導,秉持蔡元培校長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主張“以科學方法為治史階梯,謂歷史為社會科學之一,欲治史學,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 大力進行課程改革,開設“史學史”課程,還與李大釗一起將史學系課程設置成了六個系統,聘請何炳松、陳漢章、陳垣、王桐齡、陳寅恪等名師講學。他任史學系主任十年間,為北大歷史學科的創建、中國史學史學科教育體系的建立與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此,他的弟子傅振倫評價說:“此種制度實施以后,國內公私大學史科,紛紛仿形。于是,中國史學,乃得躋身于科學之列,始漸有以史學名于世者。”
然而,北大的學風雖被“太炎弟子”所掌控,但在暗潮洶涌的民國,中學與西學強烈沖擊的局面,使得北大的人事、學風均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太炎弟子們相繼進入北大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地域性的同鄉關系。所謂浙人把持最甚的,在北大主要是指朱希祖任主任的史學系和馬裕藻任主任的國文系,“蓋懲于其鄉人朱希祖、馬裕藻等人之貪”,“欲北大辦好,非盡去浙人不可”。 隨著不滿浙人把持北大的風頭漸起,北大學生接踵而至地警告和要求當局,沈尹默等相繼離開北大,參與北大最高決策機構校評議會的朱希祖,在學生風潮的沖擊之下也不安于位,向校方提出辭職。
1930年,朱希祖改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明清史。他計劃將他的南明史研究纂成《南明史》,但在研究院待了不到一年便離開了,只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幾篇文章。
(三)從中山大學到中央大學
1932年9月,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電聘朱希祖為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此時,朱希祖正沉浸于南明史的研究中,其收集南明史料已達十年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也大大激發了他的愛國意識,南明一朝抗清的歷史,恰恰能映襯他當時的家國情懷。考慮到史料的繼續收集與中山大學的情況,朱希祖決定南行任教于中山大學。他在中山大學開設史通、中國史學概論、元明史課程,與開設西洋史學理論課程的朱謙之先生,被并稱為“二朱”。在朱希祖提議下,文史研究所開始招收研究生入學,是中山大學第一批研究生。與此同時,他還應鄒魯校長之請,兼任廣東通志館纂修,撰述了《新修廣東通志略例及總目》、《新修廣東通志總目說明書》、《廣東通志征訪條例》、《征集新撰近代廣東人傳體例》等文,在方志編撰學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1934年1月,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聘請朱希祖為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羅家倫曾是他在北大時的學生,考慮到長子朱偰時任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加諸南京離故土海鹽不遠,不免有葉落歸根之念。此外,當時的中央大學已經是名流匯集,包括當初被排擠出北大的黃侃等舊交均在此任教,最終決定前往南京。南京當時是國民政府的首都,金陵重地,又是六朝古都,而朱希祖早前就對六朝史事興趣濃厚,也頗有建樹。于是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六朝史的研究中,成果頗豐,其中尤以《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一書最負盛名。除此外,他對宋人趙明誠的金石學與宋代史學也有涉及研究。這一時期,朱希祖不僅繼續研究南明史,又開始涉及六朝史和宋史,這些大大擴展了其史學研究范圍,并進一步深化了其史學思想。
在南京的這段美好時光,學術條件優越,家庭稱心如意,是朱希祖多年來工作與生活都很愜意的時期。但是抗戰的爆發,使得這一切戛然而止。日軍步步緊逼,南京危急,國民政府做好了南遷重慶的打算。1937年底,朱希祖隨學校轉移至重慶下榻,此后再沒有離開,直到1944年病逝。
初到重慶,朱希祖沒有辭去中央大學的職務,繼續授課并積極參與其他教育事業。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召開,朱希祖為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張繼起草了籌辦總檔案庫和國史館的議案,提出:“民族之所以悠久,國家之所以綿延,全賴國史為之魂魄”,“夫欲續歷史,不可不設國史館,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設檔案總庫”。 國史館的設立,在抗戰時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國史不可絕,民族之綿延,正體現了時人心系民族存亡的愛國情懷。1940年,朱希祖又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的委員,勤懇閱卷,做事兢兢業業。同年,他辭去了中央大學的系主任與教授之職。1943年,重慶成立了中國史學會,朱希祖擔任理事與常務委員。
二、史學思想
朱希祖作為章太炎的得意門生,既繼承了章氏治學的精髓,又能對西方史學有所涉獵。他主持北大史學系期間,中西兼收,倡導開設各類史學課程特別是史學理論課,對近代史學的發展做了重要貢獻。他興趣廣泛,研究領域跨度很大,上至先秦兩漢,下至晚清以降,都有所涉獵。他的著述,僅僅羅香林整理的《朱逖先先生著作目錄》中所列的文章,就有300篇左右。這些著作包含著他深刻的史學思想與史學獨見,為史學界的一大財富。在此,就朱希祖的史學研究進行簡要分析,以展示其史學思想的獨特價值。
(一)中西并重
朱希祖早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歷史師范科,對西方史學多有接觸。期間,他又師從章太炎,繼承了乾嘉考據的學術傳統。這種學術經歷,不但拓寬了他的眼界,也使他認識到中西史學兼容并包的價值所在,既重視西方史學觀念、史學理論的學習,也堅持傳統史學的優秀傳統,并嘗試用新的學術眼光來認識傳統史學。
朱希祖在任職北大期間,對西方史學有重要的倡導之功。他任系主任期間,積極推動史學系的課程改革,在他看來“我國現在的史學界,實在是陳腐極了,沒有一番破壞,斷然不能建設”,因此中國史學界應該“虛懷善納,無論哪一國的史學學說,都應當介紹進來”。 朱希祖除了聘請何炳松、李大釗、陳翰笙、李璜等人講授史學理論課程外,自己也身體力行,在史學系開設“史學史”課程。他推崇德國史學家普雷希特的“新史學”,以此梳理中國傳統史學并撰寫《中國史學通論》,并作為大學講義流傳于世。他的史學史思想也集中體現在了這部著作中,此書內容上屬史學史范疇,有重要的史學地位與價值。首先,它是在中國史學史方面最早的講義;其次,該著雖是講義之作,卻是作者潛心研究的心得,與陳陳相因之作有別;最后,這部著作在內容上確有許多精到的見解。
(二)科學求真
朱希祖去世后,其子朱偰在總結乃父的治學方法時指出:“先君治學方法,首重科學,嘗言歷史學為社會科學之一種,故欲治歷史,必先通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各科學。” 朱希祖受西方史學理論影響,治史非常強調科學性,他在北大史學系的課程改革中就強調:“學史學者,先須習基本科學。蓋現代之史學,已為科學的史學,故不習基本科學,則史學無從入門。” 他將史學系的課程分為六類,把很多社會科學列為必修課程。1928年,北京高校發起中國史學會,朱希祖被推舉為主席,他在演說中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政治有黨派,學術無黨派,講史學的,尤應超出于政黨以上,乃能為客觀的公平觀察,不為主觀的偏私論著,方合于科學的史學精神。”
朱希祖所追求的科學是指治史的規范要嚴格,態度要客觀,宗旨是求真。具體來說,治史需要史料的支撐,而處理史料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則而非隨意為之。這種科學求真精神,使得他高度重視史料的搜集與史實考證。朱希祖一生研究興趣廣泛,在史學史、史館修史、史料考證、金石、目錄、史跡調查、方志、邊疆史等眾多領域都有所建樹。但是,這些著述,大多屬于未刊稿,這反映了他治學嚴謹的態度,如他所言:“生平頗不愿學胡適之有一篇發表一篇,不顧精粗良楛也。” 朱希祖強調史料為史學第一要義,窮一生之力搜求史料,時人稱其:“海鹽朱逖先希祖,購書力最豪,遇當意者,不吝值,……君所得乙部居多,尤詳于南明。” 朱希祖還根據自己長期治史經驗,提出治史三期論,闡明治史要經過搜羅期、考訂期、去取期三個階段,認為:“史料之考訂,雖極精確,而編篡之時,亦須維以社會最需要之條款,經以科學嚴格之律令,方足稱為上乘。” 這種嚴謹的態度,決定了他治學一方面涉獵甚廣,但同時又有精深的著述推出,僅舉他在南京所作的《六朝陵墓調查報告》就可見一斑,內容詳實可靠,治學嚴謹。斷代史方面,他主要的研究領域《新梁書》、《南明史》雖未最終完成,但有專門的精到論文存世。1947年,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論及“南明史”研究的狀況時,聲稱“最近則以朱希祖先生用力最深”, 特別表彰了朱希祖在史料方面的貢獻。
(三)經世致用
中國史學強調經世致用,體現了史家鑒古知今,關注現實的治學旨趣。這一點,在朱希祖身上表現的也非常突出。朱希祖指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訂事實為基礎,以探索歷史哲學,指揮人事為歸宿,此史學之全體大用也”。 在他看來,歷史研究不僅僅是饾饤之學,繁瑣的考據,不過是為探究歷史的依據。通過這種史實的還原,從中得出全局性的看法,古為今用,引古籌今。可見,強調史學研究之目的在于“指揮人事”,考據與義理兼顧,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
朱希祖對清代史家章學誠非常推崇,認為章氏“識見之最卓越者”,就是其經世致用的思想。朱希祖表示:“人之經世,必先洞明時局,而今之時局,非一朝一夕所成,皆由歷史演變而來,此歷史成立之原理也”,因此,“不明時局而專研歷史,是謂無根之學,誠不足于言史矣”。 這種對現實的強烈關注,使朱希祖認識到近現代歷史的重要性,指出:“古人所謂藏往知來,皆以現代為樞紐。即以現代為樞紐,則今日以前之現代史,尤為重要。” 在之后北大史學系課程改革中,他進一步強調這一點:“歷史以現代史為尤要。蓋史學之目的,在認識現代社會之來歷,以謀未來之建設。” 這種觀點,體現出他高度重視史學的社會價值,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還原史實,而在于觀察未來,創造未來,“而其樞紐,則全在乎現在。蓋欲創造未來,必先認識現代之社會”。
(四)愛國情懷
朱希祖治史,自覺的與時代相結合,既體現了史學經世的一面,又表現出深深的愛國情懷。朱希祖的弟子傅振倫評價乃師說:“先師以史當致其用,研究風氣應適合時代之需要,故每見幾發微,因勢利導,蔚為風氣,以裨于民族與人群。” 朱希祖闡發章太炎“亡人之國,必先亡人之史”的觀點,認為:“吾族自有其歷史,絕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國。亡國而國史不亡,則自有復國之日。何則?其魂魄永存,決不能消滅也。” 朱希祖窮年累月致力于南明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就是受其愛國情感的激發,“蓋讀此等書者,皆有故國山河之感,故能不數年間,光復舊物,弘我新猷”。 在朱希祖一生的研究中,始終牽系著國家與民族,彰顯民族大義。九一八事變后,他鉤稽史料,撰寫《偽齊錄校補》四卷、《偽楚錄輯補》六卷,目的就是為了昭示“操縱偽國者處心積慮之險,而同國之自相屠戮者,愿各鑒此前車焉”。
綜上所述,朱希祖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關鍵人物,地位不容小覷,更不容忽視。他的史學研究成果值得后人學習與繼承,史學思想值得借鑒。只有對他的史學成就與貢獻進行客觀評價與認識,才能全面了解民國史學發展的全貌。
注釋:
朱元曙、朱樂川撰.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25,192.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317.
楊曉春編.朱希祖六朝歷史考古論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3.
羅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雜志.1945,5(11、12).
傅振倫.先師朱逖先先生行誼.文史雜志.1945,5(11、12).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1.
朱希祖.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73,174.
朱希祖.《新史學》序 //何炳松.新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4,5.
周文玖.朱希祖與中國史學.史學史研究.1998(3).
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對于史學之貢獻.東方雜志.1944,40(16).
朱希祖.發起中國史學會的動機和希望.清華周刊.1929,30(11).
朱希祖.朱希祖書信集,酈亭詩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20.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5.
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 //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9,390.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2.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文史雜志.1945,5(11、12).
朱希祖.《文史通義札記》序 //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0.
今夏中華教育改進社關於史地教育之提案及歷史教育組地理教學組之會議紀錄.史地學報.1922,2(1).
朱希祖.清代通史敘//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
朱希祖.《偽楚錄輯補》自序//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