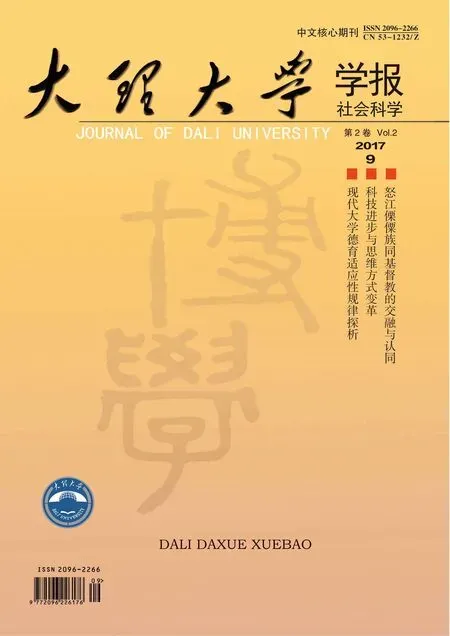一名在昆斯里蘭卡留學生的涵化與發展
陳艷清,黃成記
(云南財經大學,昆明 650221)
一名在昆斯里蘭卡留學生的涵化與發展
陳艷清,黃成記
(云南財經大學,昆明 650221)
涵化(Acculturation)是跨文化交際研究中常提到的重要概念,它往往和旅居者在他國的文化適應有關。隨著東南亞來昆明的留學生逐漸增多,對留學生文化適應、語言學習等方面的研究逐步增長。不過,多數研究重在考察某一留學群體的文化適應情況,鮮見考察某一個體涵化情況的個案研究。本案例較詳細地分析一名斯里蘭卡學生涵化四個階段的關鍵事件及意義:強烈的食物文化休克;不經意的破冰問候語;勤學漢語,善用同胞、東道國和跨國朋友圈;專業學習與創業并舉。希望本案能為在華或預來華的斯里蘭卡留學生及其文化適應研究提供一定的啟示。
涵化;漢語學習;人際交往;個人發展
自1957年2月7日中國和斯里蘭卡建交以來,兩國關系穩定發展。隨著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兩國間的教育和文化往來將迎來新的發展契機。云南作為西南地區連接南亞、東南亞的重要通道,省市各高校迎來了越來越多的南亞、東南亞留學生,對留學生的文化適應方面的問題也逐漸受到重視。
張如梅對大理南亞留學生文化適應與漢語學習關系的研究表明,南亞留學生與漢語本族語群體保持著明顯的社會距離與心理距離,且留學生群體的封閉性較強、聚合程度較高,習慣保留母國養成的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交際也多限于群體內的接觸和固定的范圍〔1〕。唐志敏等對云南大學東南亞學生在滇文化適應研究以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學生為對象,采用調查問卷和訪談的方法考察了人際交往、心理適應、地域文化差異、生活環境、學業、語言等因素對東南亞留學生在滇文化適應的影響,指出其文化適應受語言、飲食等影響較為明顯〔2〕。肖耀科、陳路芳對廣西某高校東南亞留學生(越南、老撾、泰國)的研究也發現,留學生一般習慣跟母國人聚在一起,性格開朗的留學生中國朋友較多,而性格內向的則較少跟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交流〔3〕。不過,文化適應和與中國學生交際方面的研究中,幾乎沒有看到有斯里蘭卡學生參與或者以斯里蘭卡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
一、涵化及本研究的重要性
“涵化”(Acculturation)是跨文化適應研究中經常提到的概念,但不同的學者往往因其研究需要或背景而用詞各異。有的用“涵化”,如關世杰〔4〕、陳向明〔5〕、史興松〔6〕,有的用“濡化”,如陳國明〔7〕、安然〔8〕。在此,本文不專門辨析已有研究的用詞偏好及詳情,而是認同Redfield等、Berry,以及關世杰、陳向明等人對涵化的理解,認為涵化是一種現象,是當來自不同文化的個人或群體在連續接觸時,個體向異文化學習和調整發展的過程,是個體在相互接觸的過程中文化及心理上的雙重改變〔9〕,是一種跨文化互動,一種互相影響、相互學習異文化的動態發展過程。
跨文化互動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個體主要通過與當地社會的交際互動逐漸實現文化的涵化以及個人成長〔10〕。但個體涵化的進程受到諸如個人在異文化中的人際交流能力、交流密切程度、與本文化保持社會交流的程度、異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容納性以及個人文化背景、個人素質(如個人對文化和異文化的態度、個人的開放性和精神恢復能力)等因素的影響。此外,人們帶入涵化的心理特征是因人而異的,并非每個人參與涵化的程度都是一樣的,因此我們應從主要關注某一群體跨文化適應的普遍特征轉向關注代表群體的樣本中的個體〔11〕。換句話說,研究個體的跨文化適應,或曰文化涵化,可以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入地探究具體情境中涵化的階段性特征和個體差異。
二、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對象簡介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一名斯里蘭卡籍在昆某高校留學生,名叫Asela①該名字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協商而定的,已征得研究對象的同意。。他來自斯里蘭卡一個比較有教養的家庭,父母現居斯里蘭卡西南部印度洋海濱城市加勒古堡。父親祖籍荷蘭,曾在美國、荷蘭以及斯里蘭卡某大學從事高等教育教學工作,母親為斯里蘭卡本土僧加羅人。Asela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個擅長舞蹈的姐姐,下有一個弟弟,目前也在云南某高校留學。
Asela本科畢業于斯里蘭卡首都的科隆坡大學,主修專業為日語,副修專業是人格發展。從訪談中得知,在科隆坡大學,副修專業的難度和要求均超過主修專業,但他非常喜歡自己的副修專業,并從中學到很多有利于自己個人發展的東西。科隆坡大學畢業后他就職于首都附近一所高中,做過半年多的中學教師。201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被通知可以申請到中國留學,并成功地申請到中國政府獎學金。2012年5月來到云南昆明,在某高校讀本科,專業是商務漢語,學制5年,2017年7月畢業。
(二)研究方法、問題與數據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采用質性的研究方法,遵循質性研究的一般過程,包括確定研究現象、對象、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了解研究背景、收集材料、分析材料、檢驗信度效度、道德倫理、撰寫報告等過程〔5〕43。我們首先對來自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國的三位留學生進行了開放式訪談,了解他們來中國后的生活、學習等適應發展情況。逐漸從他們感知到的原生國與昆明某高校在大學教學、學習等方面的文化差異,細化到其來昆明后的校園交際交友情況及其對他們個人成長、涵化等產生的影響,最后明確以一個比較典型的個例來較為深入地考察留學生的涵化過程及其個人發展。具體而言,本文試圖理解:斯里蘭卡來昆留學生經歷了怎樣的文化涵化?他的涵化如何影響著個人的成長和發展?
本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開放式訪談、半結構訪談、參與式觀察、多模態的信息互動(如微信、語音等)以及一次斯里蘭卡風土人情考察之旅。開放式訪談一次(2014年12月),主要目的是了解Asela的家庭背景、受教育經歷以及他對東道國學校教學、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半結構訪談分別在2015年4月、2015年10月進行,由研究者事先擬定好訪談提綱,然后按提綱依次進行問與答,必要的地方略有擴展。每次訪談時間為90分鐘左右,事后及時撰寫訪談總結、備忘錄,并對訪談的錄音進行轉寫和主題分析。參與式觀察主要由本文第二作者黃成記完成,因為他是Asela東道國朋友圈中的好友,常參與Asela的社交生活,方便獲取第一手的研究資料。
三、Asela涵化過程的重要事件及分析
Stage 1:拒絕接觸之文化震蕩事件
根據陳國明的研究,文化震蕩的癥狀種類繁多,而且因人而異。他列舉的文化震蕩癥候群包括如過度關心飲水與食物的品質、過度依賴來自同文化的人、懼怕與地主國人碰觸、敵視當地人、過度強調自己的文化認同、時常想家、無助感等18個方面〔7〕159。初到昆明的頭幾個月,Asela由飲食而受到的文化沖擊是極為嚴重的。
Episode 1:食堂“蟲——蟲”事件(2012年5月)
……這樣過來,一下子就到昆明,就我來中國第一個就是語言不懂。說什么我們都聽不懂。第二,就是,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我們發現生病啊什么的我們都不知道要跟誰說。然后第二(略停頓)第三個就是吃的,我室友知道我我可能三個月都只是喝了巧克力、餅干、水果,我不敢去外面吃飯,因為有一次我去學校打飯的時候,就有一個蟲——蟲(聲音很高,拉得很長)在飯里面,然后我告訴他,喂,這是……然后,他說:沒問題、沒問題。可我覺得這種文化很奇怪,然后我,對我來說,我真的受不了……
這是剛來昆明時Asela遭遇了強烈飲食文化沖擊的一個典型例子,這也是他經歷的重要文化震蕩表征之一:他過度關心食物的品質。以往的研究也發現,在諸如居住條件、氣候、衣著習慣、基礎設施等表層文化因素中,飲食習慣不僅較難適應,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旅居者的跨文化適應。此次食物文化休克導致他和另外兩個同伴3個月不敢到學校食堂吃飯,整體以巧克力、餅干為食,艱難度日。
Stage 2:與東道國學生初接觸:瓜子破冰事件
一個人離鄉背井,與一兩個本國同胞來到異國的昆明之后,Asela有什么問題都主要是跟父母交流,或者跟同胞交流,因為不懂中國的語言(用他的話說就是“文化不通,語言不懂”),“沒有認識的人,連生病都不知道要跟誰說”。加上在食堂經歷的蟲子事件,他們在昆明城里“獨居”了3個多月,直到8月份的暑期軍訓一個偶然的小問候,才開啟了他與東道國學生的破冰之旅。而這一次的破冰沒想到給他打開的是一個全新的、不斷開拓的跨文化人際互聯網機遇。
Episode 2:一聲英語問候(Hi),幾顆瓜子(2012年8月)
……剛好過了放假。就放假中間就開始那個軍,army training軍訓,(C:阿,軍訓,對)我們又一點很遠,我朋友就,我室友他他找到了一家西飯,就是西餐,就是有牛排啊雞排,Macaroni,然后他說:噢!那邊有,我們去看一下吧。然后我們有一天中午我們去那里吃飯,吃完飯過來,秋園那個游泳館旁邊有一個小門,對嗎?那個小門對面有四個男生看,就是他們在那個好玩,很好玩。那里有一個很矮矮的學生,他就很可愛,然后他跟我們打個招呼說:Hi。然后,因為他就是跟我們不一樣,他的手有點有問題,手就是有點有點(C:disabled?),對就是dis?abled,然后他abnormal了,所以我們就不好意思不跟他打個招呼。所以我們跟他打個招呼說:Hi。然后他說,他問我們來自哪里呀?用英文問我,我們都很開心啊!(音調很高,激動的那種)哦!!這里有說英文的人啊!然后就是他英文不是很流利。很流利的有個叫小李,Kenning,他英文比他好一點。他也慢慢跟我們交流,然后呢,他給了瓜子問我們吃嗎?我們說不吃,不吃。然后他說,好吃,你吃吧。然后我說,我不知道怎么吃。然后他教我吃瓜子,這樣我認識了他,然后他拿了我的座機號碼。第二天中午,是三點鐘左右,下雨,下了很大的大雨,然后他打電話問我們我們在宿舍嗎?我說:是的。然后他說,過來我們宿舍。我們開始,他漸漸玩了以后,然后他帶我們去昆明海埂公園,然后帶我們去看電影,他有車,他開車帶我們去玩。額,就是認識了他以后,我的生活都改變了。
原來,在跨文化的適應過程中,往往“一件很小的事情便可以決定一個外國人對一個國家的整體印象,而另一件同樣小的事情也會馬上改變這種印象”〔5〕141。Asela也如此,學校某個側門門口那個手有殘疾的男學生跟他說了一個幾乎人人都會的簡單問候語“Hi”,打了個招呼,而另一個男生教他嗑瓜子,他就突然覺得這個學校的大學生(這個文化)很友好,很值得交朋友。這兩個問候他的男生(小李、小白),后來成為他的好朋友、好兄弟,甚至成為他創業時的跨國合作伙伴。
Stage 3:學習漢語,朋友圈加速擴大,涵化加速
認識小李為首的中國學生之后,Asela開始有了強烈的漢語語言學習動機。據他回憶,認識小李之后的3個月,小李每晚去教他漢語,Asela的生活就基本都是在宿舍學漢語。5個月后,他覺得自己進步很大。2013年,他先后通過了漢語HSK四級和六級水平測試。到2013年9月新生開學時,Asela已基本能用漢語跟中國學生交流。后來,他積極地參與到學校內外的課外文化活動中(如云南省高校文化節的舞蹈比賽),參加學校的社團、協會等,并充分利用這些校內外文化活動練習漢語口語交際交流能力。從剛開始用詞交流,用手寫字,到后來很自信地去主動結交中國學生,甚至中國老師。隨著漢語語言使用能力提高,他產生極大的語言自信,這種語言自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參與更多跨文化交際的欲望,也決定了他想要與漢語本族語群體認同的程度〔12〕。隨著他對漢語認同程度的增加,與昆明本地人群,尤其是同校大學生接觸的數量和質量不斷增值,與本地師生接觸、交流慢慢成為促進他學習漢語語言與文化的最主要動機。
在Asela的涵化與認同發展過程中,小李,小白、Kervin、Lawrence等中國學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成為Asela發展人際關系的助力。有了較自信的漢語學習能力,Asela在學校的朋友漸漸多起來,慢慢地編織成了一個由各色人組成的朋友關系網絡,或者當下流行的叫法“朋友圈”。兩三年的時間里,Asela發展成為該校中外學生中的人盡皆知的活躍分子。從對他的觀察和訪談資料中分析,截至2015年6月,按國籍和地區分,他的朋友圈主要有同胞圈、東道國朋友圈,以及跨國朋友圈三個次級圈〔13〕。按他與各色朋友的親疏關系分,東道國朋友圈里的層次比較明顯,有普通朋友、密友以及其他非常規朋友(如領導、女朋友)。
Stage 4:深化友誼,合作共贏,共同發展跨國商務關系
與東道國學生建立了友誼,學會了中文之后,2014年,Asela與最初和他相交相識的好友(Asela稱其為“哥們”“好兄弟”)小李展開了跨文化商務合作。Asela在斯里蘭卡成立了美蘭旅游公司,主營中國—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以及蘇梅島精品高檔旅行。小李畢業后,在昆明某文化國際旅游有限公司工作,并發展為公司股東之一。該公司在北京、上海、廣州、廈門等地都有業務,客源多,業務資源相對豐富。據Asela所言,公司剛開始時,他采用自己在中國拉客,或與中國其他旅行社分享游客等方式開展公司業務,但是因為自己的公司不具有知名度,依靠他本人一個個體所吸引的顧客數量十分有限,業務非常不穩定。后來,他與小李溝通后,二人分工合作,小李負責中國游客相關的旅行產品銷售,Asela自己公司負責提供與產品相應的報價和游客在斯里蘭卡的全程服務(Asela親自帶團)。慢慢地,他借助小李公司在中國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廈門等地豐富的旅客資源,公司每個月都能獲得相對穩定的訂單數量,公司運營和管理逐漸順利,公司所得利潤也逐漸增多,公司業務也在穩定發展。
展望未來,Asela的夢想已經起航。他大膽地融入中國文化,或者說昆明本地文化,甚至商場上的社交文化(訪談中Asela稱,這兩年來,跟中國人談生意跑業務時,常常見人就稱“大哥,大哥,來,坐,坐,坐”……),主動地去適應、涵化、發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到現在為止,通過漢語學習,通過朋友,他幾乎得到了他想在中國追求的一切,如懂中國的語言,結交了很多層次的中國朋友,并與中國同學和朋友共同合作,開展中斯商務合作,積累經驗和資金,以便在他的國家創辦最好的中文學校,做他最想做的教師職業。
四、結語
涵化,是在與身上揣著文化背景的人交往互動中發生的,也許是有意識的,也許是無意識的。涵化過程中每個人的進程和經歷是非常個人化的,也是極為動態的,但涵化不僅僅是文化的適應,更是個人作為跨文化人的成長和發展〔14〕。從Asela的個案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他也經歷了食物引起的文化休克、文化震蕩,他也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教學方式曾有難以適應,但是“瓜子破冰”之后他主動積極地與東道國大學生進行有效的同伴互動,善于利用自己的語言和人格魅力廣交朋友,善于洞察商機、與友合作。在他短暫的中國求學四年期間,他目前的發展已經超越了普通意義上的涵化,實現了更大的個人發展,甚至為中國昆明與斯里蘭卡的貿易關系新增了契機與活力。我們無法想到那個當初因為蟲子而3個月不敢吃中國食物的留學生,居然成為該校幾萬中外學子的交友男神和創業典范。
當然,Asela的故事還沒結束,他將繼續在中國攻讀對外漢語教師專業的研究生。正如莊恩平教授指出,21世紀的挑戰是學會如何理解和欣賞文化差異,并把這種理解變成人際溝通的能力〔15〕。希望本文個案中某些事件為促進我們中國學生與其他來華留學生的有效人際交往和溝通提供一定的啟發,希望那些接收來華留學生的中國高校留學生教育管理部門重視來華留學生的入學教育,尤其是跨文化適應方面的教育,以便有效地幫助留學生克服或縮短文化休克期,使之更有效地適應在華的學習與生活。希望Asela在中國的涵化經歷對斯里蘭卡國家和人民更直接地了解中國打開一扇小小的窗,成為一面講好中國故事的小旗,為我國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作出一點有益的支持。
本文曾在第22屆國際跨文化交際學會年會(2016年7月于上海外國語大學)上宣讀。感謝北京大學高一虹教授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悉心指導和幫助;感謝莊恩平、顏靜蘭教授等與會專家和學者對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建議。
〔1〕張如梅.大理學院MBBS項目南亞留學生文化適應與漢語學習關系的調查研究〔J〕.大理學院學報,2015,14(1):84-87.
〔2〕唐志敏,王惠茹,徐菲燕.在滇文化適應情況研究:對云南大學東南亞留學生的調查〔J〕.教育教學論壇,2015(29):73-75.
〔3〕肖耀科,陳路芳.在中國的東南亞留學生的文化適應問題:對廣西民族大學東南亞留學生的調查〔J〕.東南亞縱橫,2012(5):38-42.
〔4〕關世杰.跨文化交流學: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學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5〕陳向明.旅居者和“外國人”:留美中國學生跨文化人際交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史興松.駐外商務人士跨文化適應研究〔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
〔7〕陳國明.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8〕安然.跨文化傳播與適應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9〕BERRY J W.Acculturation: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5,29(6):697-712.
〔10〕KIM Y Y.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M〕. CA:Sage Publications,2001.
〔11〕SAM D L,BERRY J W.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34.
〔12〕D?rnyei Z.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73.
〔13〕BOCHNER S,MCLEOD B M,LIN A.Friendship patterns of overseas students:A functional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1977,12(4):277-294.
〔14〕胡炯梅.跨文化交際中折射出的文化差異研究:基于中亞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案例分析〔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16,14(3):86-92.
〔15〕莊恩平.跨文化外語教學:研究與實踐〔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17.
A Sri Lanka Undergraduate's Acculturation Process in Kunming
Chen Yanqing;Huang Chengji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China)
Acculturation,a popular but important concept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has been mainly concerned with a sojourner's adaptation in a new cultur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one's customary one.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from South Asia and South Eastern Asia,studies on overseas students'learning of Chinese,and their acculturation in China have
great attention.However,no individual among the vast sojourners has been singled out for deeper and more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s to w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along the way he or she adjusts and accustoms to the new culture.With the individuality of acculturation in mind, this case study looks at the four stages and their related key events in his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that is,culture shock resulting from typical Chinese food,a popular greeting"Hi",the strong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 to build personal networks,and the starting of busines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ri Lanka.It is hoped that this case story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of a sojourner when living and studying in a foreign situational context.
acculturation;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personal development
G648.9
A
2096-2266(2017)09-0088-05
10.3969∕j.issn.2096-2266.2017.09.016
(責任編輯 黨紅梅)
2017-04-06
2017-05-10
陳艷清,副教授,主要從事跨文化交際、語言學與外語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