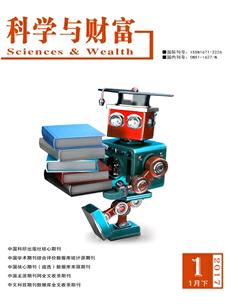從《嫦娥奔月》與《竹取物語》看中日古代社會文化的不同
樸實
摘 要: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故事。這些流傳至今的神話故事雖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但不同文明所產生的神話包含著不同的內涵。日本的《竹取物語》與中國的《嫦娥奔月》都講述了仙女奔向月宮的故事。本文在參考各現行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這兩個神話傳說的對比分析,探討了由此所反映出的中日兩國在古代社會文化方面的不同之處。
關鍵詞:社會文化;社會風貌;生死觀
近年來,隨著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的不斷加深,關系密切卻又存在很大不同的中日文化傳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學術界對兩國文化的比對研究也越來越多。對于日本的物語之祖《竹取物語》,有學者將其與我國的神話故事、民間傳說進行了對比分析。比如,李海蓉在《中日“奔月”神話比較研究》一文中,從探究中國嫦娥奔月傳說對日本《竹取物語》影響的角度,對兩者相似之處進行了比較分析和探討,最終揭示了中國的文學作品的母本對日本作家的深層影響。趙虹的《<竹取物語>與<斑竹姑娘>的比較研究》認為《斑竹姑娘》是《竹取物語》的原型,也肯定了漢文學對《竹取物語》的影響。本文通過對《竹取物語》與《嫦娥奔月》的對比分析,來探究中日兩國在古代社會文化方面的不同之處。
一、故事簡介
《萬葉集》第16卷中已有《竹取翁歌》,“歌序”云:“昔有老翁,號曰竹取翁也。此翁季春元月,登丘遠望;忽值煮羹之九名女子,白嬌無儔,花容無匹。”講的就是竹取翁與九命仙女相會的故事。雖然與《竹取物語》不存在直接的關系,但可以推測出本來是存在類似“竹取翁歌”那樣為數不少的“竹取翁”的故事的。
《竹取物語》成書于公元9世紀末至10世紀初,故事大致分為化生、求婚、升天三部分。一位伐竹老翁在一棵閃閃發光的竹子中發現了一個女嬰,并帶回家中撫養。不就女嬰便長成為一位貌美絕倫、超凡脫俗的女子。因其容貌之美能使滿屋生輝,故取名為“輝夜姬”(又有譯“赫映姬”)。許多王公貴族子弟前來向她求婚。她許諾會嫁給能尋得她喜愛寶物之人,可是這些求婚者都失敗了。后來,天皇想憑借權勢來強娶她,便用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來誘惑伐竹老翁,也遭到拒絕。原來,輝夜姬本是月宮中人,因犯錯被貶至人間,待懲罰期滿后,便會在中秋月圓之夜回到月宮中去。天皇得知后,派了很多侍衛到伐竹老翁家中,可是也沒能阻擋天人帶走輝夜姬。最后,輝夜姬給伐竹老翁與天皇留下書信與不死藥,披上羽衣,在眾人的茫然失措中升空飛向了月宮。
相較于《竹取物語》,嫦娥奔月的故事則顯得更加撲朔迷離。最早提到嫦娥的是《歸藏》。較為完整的記錄見于西漢的《淮南子?冥覽訓》,“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后羿覺得對不起受他連累而謫居下凡的妻子嫦娥,便到西王母那里去求來了長生不死之藥,好讓夫妻二人在凡間永遠生活下去。但是嫦娥卻過不慣凡間生活,不滿足于長生不死,所以趁后羿不在家,偷吃了不死藥,成仙飛至月宮。而據屈原的《天問》所載,因為后裔對嫦娥有不忠行為,和和河伯的妻子關系曖昧,因而引起嫦娥極大不滿,才離開后羿跑到天上去的。東漢張衡《靈憲》也有記載:“(嫦娥)竊西王母不死之藥,奔月,將住,枚占于有黃,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為蟾蜍。”又有說法認為,嫦娥是為了避免不死藥落入奸詐刁鉆、心術不正的蓬蒙之手,不得已才吞下不死藥的。中國的神話體系本就錯綜復雜,后世在傳說過程中更是演繹出多種不同的版本。不過,其中以第一種故事版本流傳得最為廣泛。
二、中日不同的社會風貌
神話是根據原始勞動者的自身形象、生產狀況和對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來的。神話中神的人物形象,是原始人類的認識和愿望的理想化。例如,狩獵經濟比較發達的部落所創造的神話人物大多與狩獵有關。人以刀斧、弓箭為武器,神話中的人物也就變成以這種工具武裝起來的英雄。神話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超于凡人的力量,但有時也會遭遇到挫折和厄運。因此,通過神話可以隱約看到先民的一些事跡、當時的生產狀況和社會風貌。日本著名的民俗學家柳田國男認為《竹取物語》是“反映時代的作品”。
《竹取物語》產生于日本平安時期。那時日本社會文明剛剛確立,封建社會制度尚不成熟。整個故事以平安時期的貴族生活為背景,描繪出一個較為自由、平等的社會環境。例如,臣民竟敢于違抗天皇的命令。這與中國封建集權專制統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父親允許女兒在婚姻問題上有自己的決定權,這完全違背了中國封建禮教關于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長制度,也違背了“老尊幼卑”的家庭倫理規范;男女互通詩文說明女子在當時也有受教育的機會;關于戀愛的追求與考驗則表達了當時人們自由浪漫的愛情理想。
嫦娥奔月的傳說最早產生于中國戰國時期,到了西漢初期有了確切的文字記載。當時的中國已經建立了較為健全的封建社會制度。嫦娥雖然成仙脫離了凡間,但害怕眾仙嘲笑,不敢前往天庭,轉而奔向月宮,生活在寂寞冷清的廣寒宮中,落得個“寂寞嫦娥舒廣袖,獨攬月宮一片天”。按照《靈憲》的說法,嫦娥最后變成了蟾蜍。唐朝詩人李商隱更有詩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正是她倍感孤寂的心情寫照。悲劇性的結局都在懲罰嫦娥拋棄后羿獨自飛仙的行為,這正是中國古代封建禮教制度中“夫權”思想的折射。在中國古代社會,丈夫對妻子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力,違背丈夫的意志,勢必會遭到當時社會的譴責與懲罰。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封建禮教已經成為了人們難以擺脫的思想桎梏,支配著當時人們的日常言行舉止。
由此可見,兩個神話故事中的人物關系,反映出中日兩國不同的社會風貌。無論中國文化對日本產生了多大的影響,日本民族文化還是呈現出了其獨特的一面。《竹取物語》展現了日本古代社會不同于中國封建社會較為平等自由的一面。
三、中日不同的生死觀
生死問題是人類的原始性思考,也是一個永恒探討的話題。從宗教到科學,從醫學到哲學,從達爾文的進化論到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古今中外無數圣人先哲探索過、研究過。生,較之于死,無疑是美好的,是人類本能的追求。可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終將難免一死。這是誰都無法逃避的。藥物治療疾病的神奇功效使得人們有了寄希望于不死藥可以治療死亡的幻想。在古代,中國人相信有前世今生,更有人期望能夠通過宗教修行成仙,從而長生不老。不死藥、生死輪回的信仰、升仙,都是人類恐懼死亡、試圖逃脫死亡的產物。
在嫦娥奔月的傳說中,后羿為了能使夫妻二人長生不老,不辭辛勞、翻越晝夜不息的火焰山,渡過片羽亦沉的弱水,才在西王母那里求得一粒不死仙丹。這不死藥使用不死樹結的不死果煉制而成的。不死樹三千年開一次花,三千年結一次果,煉制成藥又需三千年,足以見其珍貴稀罕。無論是后羿、嫦娥,還是其他故事版本中后羿的弟子蓬蒙等,人人都想服下這不死藥。
然而,在《竹取物語》中,不死藥是天人帶來給輝夜姬服用以除去其身體在凡間所沾染的穢氣的。輝夜姬為報答伐竹老翁的養育之恩轉贈于他。伐竹老翁因為失去女兒,悲痛不已,不愿服用不死藥,又獻給了天皇。天皇看過輝夜姬的信后,作詩一首:“不能再見輝夜姬,安用不死之靈藥”,也不愿服用不死藥,最后命侍從把輝夜姬留下的不死藥與信拿到離月宮最近的山頂燒掉。此后,這座山就叫做“不死山”,即現在的“富士山”。死亡是無法預測和抵抗的。作為一種自然現象,日本人早已坦然接受這一人的最終歸宿。
由此可以看出,兩個神話故事所反映出的兩國截然不同的生死觀,即對不死藥的“爭搶”與“謙讓”。嫦娥寧愿放棄夫妻情分,承受來自社會倫理的譴責,忍耐孤寂的月宮生活,也不愿放棄擺脫死亡升仙的機會。而伐竹老翁則認為失去了輝夜姬,即使活在世間也沒有意義。相比之下,《竹取物語》反映出了日本人超然的生死觀。
通過對《嫦娥奔月》和《竹取物語》這兩則古代神話故事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兩國古代社會文化的不同之處。日本的社會文化雖然受到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影響,但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又有其與眾不同且多元的一面。兩則神話傳說所都講述了“奔月”,卻顯現出了不同的社會風貌和生死觀,同時也為讀者勾勒出了兩位美麗而性格迥異的女性形象。
參考文獻
[1] 李海蓉.中日“奔月”神話比較研究[A].考試周刊.2009(10).
[2] 趙虹.《竹取物語》與《斑竹姑娘》的比較研究.日本研究.2003(02).
[3] 郭常義.《竹取物語》與古代日本的倫理、君權意識.日本研究.2000(02).
[4] 張龍妹,曲莉.日本文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
[5] 田國男.昔話と文學.角川書店.19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