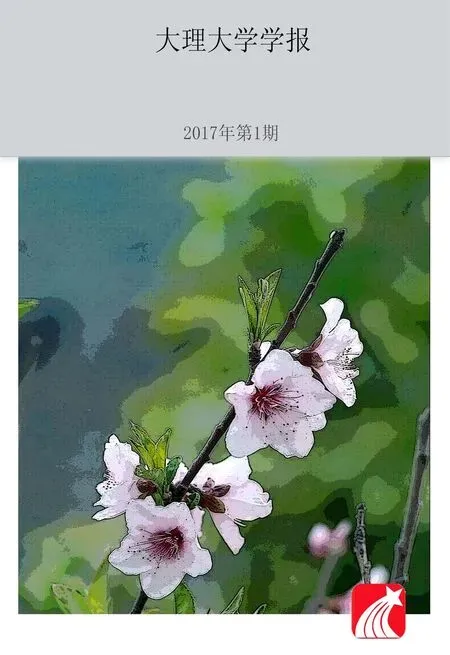孤本《驛路歌》與清代云南作家張漢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杭州 310028)
孤本《驛路歌》與清代云南作家張漢
董雪蓮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杭州 310028)
《驛路歌》是一本用詩歌形式寫就的由滇至京紀程吟詠之作,為現存孤本。《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叢書廣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中國古籍總目》均無記載。經考證應為清初云南著名詩人張漢所作。該書用詩歌文體寫驛路,不僅形式新穎,還形象、簡潔地描述了當時京滇之間驛路的情況,具有地理學和文學上的研究價值,同時可補中國古籍聯合目錄之遺漏。
驛路歌;張漢;清代;云南;地理
《驛路歌》,一本用詩歌形式寫就的紀程之作,成書于清初康熙年間,為現存孤本,藏于中國臺灣傅斯年圖書館。長期以來,此書湮沒于浩如煙海的古籍中,鮮見于史料記載。現將其相關信息作一略述,以俾學界相關人士指教。
一、史料中對《驛路歌》一書的相關記載
關于《驛路歌》相關信息,云南史志僅見于史學家方國瑜先生《云南史料目錄概說》,其中記錄了尋訪此書的過程。
《驛路歌》一卷,張漢撰。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藏咸豐元年抄本,瑜未獲讀,惟可知為自滇至京循驛道紀程吟詠之作。瑜兒時見家藏京滇驛程之書,坊間所刻袖珍本,為旅行指南,因俗書未見藏書家著錄,不識坊間因張漢盛名而假托否?又按:東方文化委員會所藏圖書,今歸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九六三年,瑜訪書見原《驛路歌》下,有“提京”二字朱印。聞謝國楨言,在解放前,偽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從此館書庫中提去大量圖書,此為其一種,不知今在何處云。〔1〕
此段話透露了兩點信息:一是《驛路歌》署名張漢,方先生未獲睹原書,不知此書是否有假托張漢所撰之嫌;二是此書確有,但已下落不明。
經遍查史志與目錄,惟見民國所纂《續修四庫總目提要稿》對《驛路歌》一書有介紹。
《驛路歌》,不分卷,抄本。清張漢撰。漢字月槎,籍貫、事跡俱不可考。惟書尾有“咸豐元年春二月長白諾問農錄”字樣,則為嘉道時人可知。是篇乃將由滇至京驛路,成詩以述,共四十九韻,所過之程大致俱備,以便于記憶耳。后附自滇省至京師郵程,羅列各驛站距里之數,蓋備與詩歌參閱……〔2〕
除此而外,未見相關記載。《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叢書廣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中國古籍總目》等聯合古籍目錄亦未著錄此書。經尋訪,于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數字典藏系統”數據庫中查到了掃描圖片版的《驛路歌》。原來該書原本收藏于中國臺灣傅斯年圖書館。看來方國瑜先生所記錄的謝國楨所言,確有其事。
二、《驛路歌》作者及創作時間考辨
《驛路歌》字數并不多,一共只二十二頁,封面“驛路歌”三字右下角,寫有“張月槎先生著”字樣,首頁篇名下亦有“月槎張漢”幾個小字。篇末扉頁上寫有“咸豐元年二月朔后一日,長白諾問農錄于養拙齋之南窗。”下方蓋有印章,可惜年深月久,印章字樣已無從辨認。由此看來,《續修四庫總目提要稿》的相關記錄與此書體現出來的信息是基本一致的。只是關于作者張漢的記錄稍顯模糊,言及其“籍貫、事跡俱不可考”,現今筆者查閱相關史志,將張漢生平與著述情況略述于下。
張漢,字月槎,號莪思,晚號蜇存,云南臨安府石屏州(現云南省紅河州石屏縣)人,《(乾隆)石屏州志》記他“己卯正月十六年八十卒于家”〔3〕103,可知他生于康熙庚申年(公元1680年),卒于乾隆己卯年(公元1759年),根據孫灝《石屏張月槎公墓志銘》〔4〕,張漢“十七補學宮子弟員,戊子舉鄉試,癸巳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勅譯國書,乙未授檢討”〔4〕,在翰林院十年之后,張漢于癸卯年(公元1723年)出任河南知府,在任八年,“清慎勤為,治判郭氏三十年未決之案,鋤豪奸猾吏,民頌神君、父母,多政績。……不阿上游,誣以狥庇僚屬罷”〔4〕。歸家數年后,張漢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復被舉薦入博學鴻詞,次年“丁巳補試列二等,復授檢討”〔3〕103,并出任山東道御史,“有直聲”。丁卯年(公元1747年)張漢再度辭官,此后十余年不復出,終老鄉野。
張漢平生有詩七千余首,文章數百篇,但因其在世時未加整理刊行,以致四處散落,“家徒四壁,益嗜古不倦。……所著詩古文詞六十九卷,貧無資,未得盡刊行于世”〔5〕5,現存《留硯堂詩選》六卷和《留硯堂文集》兩卷,為清代云南狀元袁嘉谷所編,分別收入《清代詩文集匯編》和《叢書集成續編》,但作品數量已不及原來的十分之一。除此之外,張漢墓志還記載他還著有《經史纂略》《等韻二合音》《孝鵠編》《格言書紳錄》《錫嘉錄》《同門十子錄》《江燈筆記》《雪燈筆記》《故事雜錄》《紙尾錄》《詩林樵》《耳余筆錄》《守河南二千日記事》《過庭詩話》《洛中謠》,已刊。有《乞言錄》《續河南府志》《張氏家乘》,藏于家。道光年間的《云南通志稿》及光緒年間《云南通志》也有相同記錄,袁嘉谷修撰的《石屏縣志》則更詳細地將其著述按經史子集進行了歸類,記錄了存佚情況。由此看來,張漢一生筆力雄健,可謂著作等身。
張漢在當時頗有詩名,同時及后世許多學者對其評價都很高,袁枚曾與張漢同在翰林院,對其詩非常稱道,他在晚年回憶張漢時還希望能再讀到他的詩:“丙辰召試,有康熙癸巳編修云南張月槎先生,名漢,年七十余,重入詞館。……后五十年,余游粵東,飲封川邑宰彭公竹林署中。西席張旭出見,詢知為先生嫡孫,急問先生遺稿,渠僅記《秋夜回文》一首。”〔6〕晚清詩人吳仰賢最推重的云南詩人是張漢和錢灃,曾有詩句“文章氣節數張月槎張漢錢錢南園錢灃,一代宗風足比肩”〔7〕來稱道二人。清初學者儲大文評論張漢詩“上源于國風而采諸輶軒,被諸樂府”,認為在滇南詩人中,“張子第一矣”〔5〕1,云南唯一的狀元、著名學者袁嘉谷亦評價張漢詩“出入于大歷、長慶之間,其在吾滇,固上扛禺山(張含),下揖南園(錢灃)而無愧者”〔5〕3,將其列為云南第一流的詩人。
孫灝在墓志中評張漢“位雖未大顯,盛名在海內。其嘉言懿行、文辭書翰,可錄而傳者多也”〔4〕,是非常中肯的。雖然張漢仕途不得意,未能在官場大展拳腳,但氣節文章,卻受世人推重。
以上就是張漢基本情況。當然,方國瑜先生對于此書是否為張漢所著存有疑問,是因未親自獲見此書,此乃方先生作為一名史學家的謹慎之言。
筆者認為,從目前掌握的材料,《驛路歌》一書,確實出自張漢之手,且本書應作于作者第一次進京途中。
袁嘉谷編選張漢《留硯堂詩選》時,每一卷都依據原本,按照創作時間段編次,在目錄中,每一卷標題后都注有小字作為說明,如目錄第一卷后注有“卷一:七十九首,原《刪后草》三卷、《馬上吟》二卷,康熙丙子至癸巳之作,共五百六十六首”〔5〕5的字樣,其余各卷亦然。張漢是癸巳年進士,由此我們可知這一時期的詩歌寫于他中進士步入仕途之前。也就在該卷中,較為集中地出現了諸多與《驛路歌》中地名呼應的詩作。如《驛路歌》第二頁寫道:“試問重安江上渡,石頭鋪酒黃平好。好從云洞過偏橋,鎮遠河邊宿一宵。”在這兩句詩中,出現了重安江、黃平、云洞、偏橋和鎮遠河幾個地點,而在張漢詩集第一卷中也相應有《重安江霧》《黃平玉皇閣》和《鎮遠江中》等詩。又如《驛路歌》第六頁寫有“試問新鄉何處是,衛輝府里聽朝歌。”從這句詩我們可知作者到了河南新鄉和衛輝,并聯想到了殷商的歷史。同樣在張漢詩集第一卷中,有《比干墓》一詩,我們不妨一讀其中幾句:“牧野陳尸殄鴉群,三仁評定痛無商。書名有待春秋筆,誓死爭凌日月光。殷土一抔王氣壯,尼山四字墨痕香。銅盤古篆封元渥,不解孤臣恨國亡。”〔5〕10從詩中我們能深深感知到張漢由悼念比干而發出的對殷商歷史的深深感慨,與《驛路歌》中到衛輝就聯想起殷商的情緒深為契合。
其次,從《驛路歌》情感基調來看,雖然路途遙遠,時有疲憊、艱辛和阻礙,“崎嶇鳥道走郎岱,坡貢山高路又長”〔8〕3“龍崗卻過邢臺邑,莫向內邱恨路難”〔8〕6,但放眼整首詩,其基調始終是輕快、昂揚的,隨著一程接一程的累加,讓人讀到的不是旅途辛勞的抱怨和無奈,而總是充滿對下一站的期待與興奮之情,“來朝且渡傳溪驛,再去辰州也不遲”〔8〕4“日暮大龍君駐馬,明朝清化動征幡”〔8〕4。在這些詩句中,總是時刻準備奔赴下一程的心情隨處可見,這種情緒的傳達有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初次出行的興奮和新奇,對于前路的未知與期待;二是對于個人前程的信心與憧憬。那么,這種信心與憧憬來自何處?自然是第一次參加會試的激動與期望。張漢對自己的才學是充滿自信的,《石屏州志·張漢傳》稱他少年時即“博洽四庫,為文風發泉涌,千言立就”〔3〕103,因此首次進京參加應試他必然信心百倍、壯志滿懷,這種意氣風發的感情不自覺地流露在了詩句之中。雖然從張漢的生平可知,他一生從滇至京城的完整行程至少有三次,一次是癸巳年進京會試,然后次年進京入職翰林,再就是乾隆乙未年第二次入仕。其余在為官期間還有可能往返,但從以上幾點分析,筆者認為《驛路歌》應是作于第一次進京途中。
三、《驛路歌》的內容和相關價值
《驛路歌》以詩歌形式記錄了作者從滇省至京城的路線和旅程,并在詩歌結尾附上了所經過每個驛站的里程和名稱。在此書中,作者為我們描繪的路線從省府昆明出發,詩歌一開始就點明了起點站,“滇陽策馬望神京,夜宿板橋月色明。”〔8〕1從昆明往東北方向經板橋、楊林至曲靖府,由曲靖府出滇至貴州,途經易隆、馬龍、沾益、白水驛、自平彝縣出至貴州至亦資孔驛,再經安順府、貴陽府和鎮遠府到達湖南,然后經辰州府、常德府,自澧州清化驛出,到達湖北荊州府,路經襄陽府,自襄陽縣呂堰驛,出至河南新野,然后過南陽、開封,由滎澤渡黃河,經衛輝府,再由彰德府湯陰縣至直隸省廣平府,經順德府、真定府、保定府,達順天府,過邢臺、栢鄉、新樂,而后過盧溝橋進入終點站彰義門,共計驛站一百零四個。路線非常清晰明了。
就如上文提到,《驛路歌》的題材并不新穎,由滇至京或由京至滇的旅程有數種相似之作,況且從內容的詳細和豐富性而言,《驛路歌》并無任何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不具備相應的價值。
首先,從文學價值的角度而言,《驛路歌》與其他日記或散文形式的旅程類著作不同,它以詩歌的形式寫成。每一句詩里都有一到兩個地名,要把地名巧妙地串聯起來,讓人對作者的路線和所到之地一目了然,并且還讀得饒有趣味,這體現了作者非同尋常的才思和文筆。“遲來馬底夜黃昏,暫飲界亭酒一樽。新店從來無好店,鄭家驛里是荒村。”〔8〕4長途跋涉后的疲憊和自我放松,或是對所到之地的失望情緒,都傳達得細微真切。“憑吊南陽三顧處,空傳博望祭風臺。臺高遙望裕州煙,爭戰保安客飲泉。”〔8〕5用典精到、巧妙,點出地名的同時,詠史、懷古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間,意境生動,讓人如身臨其境,自有一種別樣的感染力。從詩歌整體風格而言,文字清新、明快,畫面生動,雖寥寥數語,卻讓人如同置身其中。作者串聯地名毫無生澀牽強之感,看似信手拈來,顯示了其敏捷才思和駕馭文字的高超能力,將漫長疲憊的旅程寫得生趣盎然,自有別出心裁之妙,給讀者一種特殊的閱讀體驗,在文學創作手法上,亦值得借鑒。
其次,從地理學角度而言,《驛路歌》的存在有相應價值。筆者選取了另外兩種同樣是清代滇省與京城之間的旅程作品,即楊名時《自滇入都程紀》和李澄之《滇行日記》進行考察和對比,前者記錄的同樣是由滇至京,后者是由京至滇,雖然粗看之下,路線基本相同,驛站記錄也出入不多,但經仔細對比,有些地名、路線和驛站還是有差別。例如在《驛路歌》里,張漢有詩句“遙望楊松煙樹外,日向罐子窯邊紅。紅日東升上花貢,客來毛口過河塘。”〔8〕3我們知道他過了楊松驛后到了罐子窯,然后是花貢,再是毛口。但在楊名時《自滇入都程紀》中,罐子窯驛站過后是律當,而非花貢,然后到了下一站毛口驛。再如張漢的路線自湖南辰州府的便水驛之后,與楊名時所記大有不同,張漢在里程記錄里寫道:“六十里辰州府,六十里馬底驛,六十里界亭驛。”〔8〕13可知他經過了辰州府,并經過馬底驛和界亭驛,同時有詩“迢迢驛路底晃州,便水悠悠去復留。前接芷江橋一座,馬公坪里可遨游。游戲頻開懷化思,山塘一宿又何之?來朝且渡傳溪驛,再去辰州也不遲。遲來馬底夜黃昏,暫飲界亭酒一樽。”〔8〕4從詩句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在馬底和界亭兩個驛站停留,他還經過了晃州(今湖南省新晃縣)、便水驛(屬今湖南省西部)、芷江縣、馬公坪(今湖南省慈利縣境內)和懷化。在《自滇入都程紀》中,作者同樣經過辰州府,自便水驛路后,走的是公平驛、黔陽縣和辰谷縣〔9〕。類似的差異還有。誠然,作者這種路線的差異完全有可能因為各種原因臨時改變,但這至少為清代云南至滇的路線和驛站考察提供了更多的參考。另外,有些地名在清代或許有過變更,或是別稱,比如在楊名時《自滇入都程紀》中記載了直隸真定府的阜城驛,但在李澄之《滇行日記》和張漢《驛路歌》中,均作“伏城驛”。這為考察地名在不同時期的變更、官方與民間的叫法、路線的異同有一定參考價值。
第三,可補大型古籍聯合目錄之缺。由于《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叢書廣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以及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均未著錄該書,故此書應為孤本。筆者查閱了其他電子古籍數據庫如《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中國基本古籍庫》等,均未見關于此書任何記載。此外,在云南各版本地方志中,亦未見錄。因此《驛路歌》一書的發現,可以填補中國古籍聯合目錄編選的遺漏,同時對云南地方志中清代云南作家的著述情況也是相應的補充。
因此,從以上方面而言,《驛路歌》的發現具有相應的學術價值。
〔1〕方國瑜.云南史料目錄概說:中〔M〕.北京:中華書局,1984:653.
〔2〕《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37冊〔M〕.濟南:齊魯書社,1996:248.
〔3〕本書編委會.中國地方志集成·云南府縣志輯:第51輯〔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4〕(嘉慶)臨安府志:卷十九〔M〕.清嘉慶四年刻本.
〔5〕張漢.留硯堂詩選〔M〕∕∕《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匯編:2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袁枚.隨園詩話:卷十四〔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
〔7〕吳仰賢.小匏庵詩存〔M〕∕∕《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匯編:68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楊名時.自滇入都程紀〔M〕∕∕上海書店出版社.叢書集成續編:65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9〕張漢.驛路歌〔M〕.咸豐元年抄本,臺灣傅斯年圖書館館藏.
The Unique Edition of The Song of Road and Zhang Han,a Writer of Yunnan in Qing Dynasty
Dong Xueliang
(Humanities School,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The Song of Road,a book written in form of poet on the way from Yunnan to Beijing,is a unique edition in the world.There is no any record of it in Aggregation of Serie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Collections of Serie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Chinese Ancient Rare Books Bibliography,or Chinese 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Books.Taiwan now.It is verified to be written by a famous poet, Zhang Han,from Yunnan in early Qing Dynasty.The book is about the post road in poem style with novelty,vivid images and concision in describ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post road from Yunnan to Beijing in Qing Dynasty.It shows the value of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and can fill the omit in the catalogu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The Song of Road;Zhang Han;Qing Dynasty;Yunnan;geography
10.3969∕j.issn.2096-2266.2017.01.014
I207
A
2096-2266(2017)01-0064-04
(責任編輯 黨紅梅)
2016-10-31
2016-12-01
董雪蓮,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