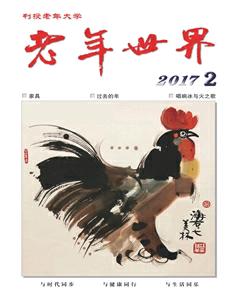人生路坎坷奉獻心永存
塞音+于錦繡
跟在醫療隊后面的倔強少年
趙龍出生在陜西省蒲城縣。在那個中國大地最為貧弱的年代,軍閥割據,戰火連綿,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朝不保夕,艱難度日。趙龍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和中國無數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一樣,疾病、兵亂、地租等等,都是懸在頭頂的鍘刀,隨便哪一個都能將這樣家庭瞬間擊碎。
父親在趙龍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給地主家做飯,當傭人,后來被地主賣了。那年,趙龍才10歲,沒有了家庭依靠,失去了雙親庇佑,他開始流浪。走東街,串西巷,逢見人家,討一口吃食。漂泊的那段時間,他時時想著去當兵,這樣既能給母親報仇,又能解決生計問題。哪里有當兵的消息,他都要湊過去聽一聽,對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最初的認識也來自這樣的“道聽途說”。
那時候,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宣傳,污蔑紅軍,說紅軍都是紅眼睛綠頭發的妖怪,見到小孩子就要吃。所以,紅軍一來,趙龍他們都要躲進裝麥秸的倉庫里。慢慢見的多了,趙龍發現遠不是那么回事。紅軍把老百姓的院子打掃得干干凈凈,水缸都挑滿了水。遇到農忙,還會幫著收割莊稼。看在眼里,記在心里,過早涉世的趙龍有了自己的判斷,他相信紅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是真正的工農子弟兵,要當兵,就要當紅軍。
趙龍回憶說,那時國民黨也四處征兵,他還被選中當勤務員,但最后他還是悄悄溜走了。幾經輾轉,他找到了一支紅軍隊伍。當時趙龍剛滿12歲,騎不了馬,扶到馬背上就會掉下來。負責征兵的同志告訴他:紅軍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你太小了,走不了那么遠的路,也騎不了馬。紅軍的拒絕并沒有打消他參加紅軍的決心,他拗著一股勁兒,就跟在部隊后面。
那是紅二方面軍的一支隊伍。跟的時間長了,他和行進在部隊后面的醫療隊熟悉起來,看著醫療隊員忙不過來,他就幫著照顧傷員,端屎端尿地干著力所能及的事情。就這樣,這個倔強的孩子被默認留了下來。他拿不了長槍,打不了仗,就一直跟著醫療隊。不久,部隊整合改編,趙龍到了紅四方面軍,但還是被安排在后方醫院。由于戰事激烈,成百上千的傷病員被送往后方醫院救治,雖因缺醫少藥,不少傷病員光榮犧牲,但后方醫院仍為川陜蘇區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趙龍曾說起,為了行軍需要,醫療隊分給他一件大棉襖,他白天當衣服,晚上當被子,十分愛惜。
延安的學習工作是我人生的起點
1941年前后,趙龍隨部隊來到延安城。距離延安城20公里有個柳樹店村,中央軍委衛生部于1939年在柳樹店村建立了一所醫科大學,叫中國醫科大學,后改名為延安醫科大學。后來,紅四方面軍后方醫院與醫科大學部分合并,趙龍還到醫科大學學習了一些衛生救護知識。
之后,趙龍被安排給周靜當勤務員。他回憶說,周靜是位女干部,擔任延安干部子弟學校校長。抗戰爆發后,陜甘寧邊區的大批干部奔赴前線作戰,子女留在后方無人照管,為了照顧這些子女的學習和生活,黨中央創辦了這樣專門收留干部子弟和烈士遺屬的學校。趙龍說起的周靜,很可能就是當年在延安負責一些革命烈士的孩子日常生活和學習事務的工作人員。解放后,趙龍也去找過周靜,但始終沒有找到。
趙龍回憶,周靜那時還很年輕,大概20多歲,很能干。作為勤務員,趙龍要幫著給那些革命烈士的孩子洗衣服、做飯,那些學生中就有葉挺的孩子。工作之余,周靜教趙龍文化知識,每天教他識幾個字,趙龍學得很快,一年多以后,就能寫信了,趙龍便當起了學校的通訊員,每天往返于學校和延安城數里外的大砭溝口,取信送信。現在回憶起來,趙龍仍然十分感謝周靜。
1942年,趙龍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調往《解放日報》。《解放日報》是當時的中央機關報,黨的很多政策決議都是通過《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向全國傳達。趙龍喜歡發電報的聲音,這正是源于在日報社以及后來到新華社當通訊員的經歷。趙龍回憶,新華社跟國內國外都有聯系,既要掌握國內戰局發展,也要了解國際形勢。對趙龍而言,那起伏不斷的嘀嘀聲是戰斗的號角,是勝利的召喚,也是永遠回響在耳邊的故事。
除了給各地區發電報,他在延安時還參加了南泥灣大生產。那還是預備黨員剛剛轉為正式黨員的1943年,秘書長動員趙龍 去南泥灣開荒,給新華社種點糧食。
為克服解放區面臨的日軍“掃蕩”、國民黨頑固派封鎖以及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在“一把镢頭一把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的口號下,八路軍進駐距離延安城東南45公里的南泥灣,將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牛羊滿川、麥浪起伏的陜北江南。
趙龍所在的生產隊有100多人,每個隊員都有生產任務,隊員們搞競賽,比速度。趙龍記得,當時他們每個人每年要生產三千斤小米,開30畝荒地。那時候糧食畝產量不高,一畝地只能收百十來斤谷子,任務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隊員們夏天砍樹鋸木板,冬天上山燒木炭,這樣折合下來,才夠完成任務量。趙龍回憶,當時在南泥灣的戰士勞動量都很大,老百姓鋸木頭兩個人一天鋸七尺,八路軍每天每人要鋸兩丈四尺;老百姓的耕牛才犁七分地,八路軍每人每天要挖一畝半多。另外,他們還要挖菜園子種菜,保證新華社千余人的蔬菜供應。
因為得了關節炎,走不了路,趙龍沒有機會上前線作戰。回憶起延安的生活,他有很多想說的,那時吃飯以小米為主,小米粥、棒子面,一個月或者一周吃上一頓白面就很不錯了,住的窯洞,冬暖夏涼,布置簡單,生活上雖然艱苦,但人們很快樂,“在延安的學習工作是我人生的起點,當時做什么事都覺得是非常高興的,自己也愿意做,沒有人強迫命令。延安對于革命者來說的確是一個搖籃,是培養發展革命者的地方,也是堅持抗戰勝利的一個保障。”
第一功勞
1949年初,為了迎接全國解放,及時培訓出合格的干部,提高中直機關部分職工的文化水平,中直黨委籌建中直文化學校。趙龍很聰慧,在文化學校學習了兩年,從最初級的一班一直升到了成績最好的九班。當時,他們這批學員考人民大學,共考上6個,其中就有趙龍。但入學體檢時查出他有內膜炎,這樣大學就沒有上成。
1951年8月,趙龍被調到北京中直黨委俱樂部,任副主任,負責中央直屬機關領導的文化娛樂活動。評價自己的工作,趙龍把在中央俱樂部的七年作為他的第一功勞。他回憶,毛主席喜歡看郝壽臣演的“花和尚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朱德喜歡看的是四川的“三瓶醋”(戲曲名,三個吃醋的人),鄧小平怕別人擋著他,每次看節目都坐在第一排。
周總理很幽默,有一次要出國演出,在歡送晚會上,周總理要講話。那天暖氣不好,屋里溫度低,周總理說:“今天有點涼快呀,涼快好,頭腦清醒。”大家都笑了。散場后,周總理要走了。趙龍說:“我跟在他后面,走到門口,門給鎖住了,出不去了,我一著急,上去左右一挫,把門給挫開了。周總理笑著對我說:‘你真有辦法。”“在中央俱樂部,我經常給領導們組織舞會。夏天,領導到北戴河去,我也跟著去負責安排跳舞、唱歌、演戲。在工作中,我始終把握著‘吃兩頭、帶中間的做事原則,即中央的精神要吃透,基層的精神要吃透,中間的問題就好解決了。”
奉獻在包頭
1957年,32歲的趙龍被調往內蒙古包頭市,就此把根扎在了包頭。他先后在青山區政府、包頭市文化局、包頭市愛衛會任職工作,直到1984年離休。60年過去了,當我們想知道他為包頭市的建設和發展做了多少貢獻的時候,他說他記不得了。家人幾次提醒,他只能勉強回憶起在衛生部門工作的一些情況。
趙龍說,包頭那時是全國綠化的先進城市,中央在包頭召開愛衛會現場會議,讓全國,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31個城市向包頭學習,學習包頭的綠化和美化。
趙龍老人現在已經92歲了,在內蒙古地區所有健在的老紅軍中,他是最年輕的。他有嚴重的關節炎,腿腳不便,出入行動都要用輪椅。老伴兒李其英88歲,也是一位離休干部,老兩口的生活都得由孩子們和保姆來照顧。只要天氣好,每天上午8點,保姆都會推著趙龍去附近的植物園曬曬太陽。雙腳蹬地,借著反向力推動輪椅,是他唯一能做的鍛煉。到10點,保姆再把他推回去,休息,吃午飯。下午,他還要看上一兩個小時的書報。規律的生活習慣是他長壽的秘訣之一。
他話不多,但思路很清晰,有主見,談起事情,條理分明。家人說,他聽力下降,平時極少開口說話,看到我們來,很高興,說了十幾分鐘,這已經是很難得了。
后記
我們用一個上午的時間采訪拍攝趙龍老人,希望我們的打擾不會影響他規律的生活。從有限的資料和交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老紅軍默默無聞、甘于奉獻的赤子情懷。我們這些享受著和平和發展的后輩兒孫們應該記得他們的故事,記得那些遠去的歷史。祝愿他們健康幸福、快樂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