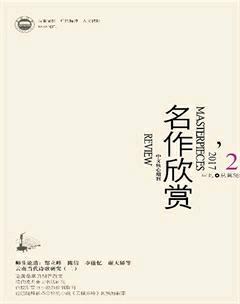論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正統文學觀念
摘 要:《詞曲概》是《藝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間詞話》問世前最重要的詞學批評著作。中國古代便有“詞為小道”“胡夷里巷之曲”的說法。劉熙載在《詞曲概》中是將其視為與詩、書、賦一樣的正統文學范疇,詞曲的正統文學特性在書中有鮮明的體現。
關鍵詞:《詞曲概》 正統文學 道德觀念
劉熙載,字融齋,清末著名學者,一生以治經學為主,是中國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著述豐富,《藝概》是其文藝批評的專著,其中《詞曲概》是關于古代詞曲的專論。在古代曾被視為“艷科”“小道”的詞曲一直都沒有詩、賦一樣的文學地位,而在劉熙載的《詞曲概》中卻以正統文學的觀念來品評詞曲,這是劉熙載的獨到之處。
一、給詞曲以正統文學地位
詞和曲都是“倚聲”而作。所倚的“聲”大部分是“開元以來”的“胡夷里巷之曲”。因為其不夠“雅”,所以曾被視為“艷科”“小道”。劉熙載在前代文人對詞曲給予肯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詞曲的文學地位,從詞曲的起源方面證明二者同詩、賦的關系。如“樂歌,古以詩,近代以詞”{1},“詞導源于詩”和“詞如詩,曲如賦”。此將詞曲和詩賦聯系在一起,從源頭提升了詞曲的地位。
除了在起源上說明詞曲乃正統文學之外,還從風格方面予以肯定。如“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后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在詞的發展史上很多人認為蘇詞為“變調”“別格”。而劉熙載卻一反此說,認為“晚唐、五代乃變調也”,言下之意蘇詞方為正宗,這正是從詞發展史的角度提升了詞的文學地位。
二、強調“詞品”與人品
中國古代的正統文學以品格的的高低作為評判標準。劉熙載說:“論詞莫先于品。”就是說將詞的品格作為論詞的最高標準。在劉熙載之前論詞往往不以“詞品”為首。劉熙載在《詞曲概》開篇云:“樂歌,古以詩,近代以詞。如《關雎》《鹿鳴》,皆聲出于言也;詞則言出于聲矣。故詞,聲學也。”由此可見詞是聲學。詞和曲都是先有了調子,再按它的節拍,配上歌詞來唱的。它是和音樂曲調緊密結合的特種詩歌形式,都是沿著“由樂定詞”的道路向前發展的。{2}因此詞“聲學”的定性和“倚聲填詞”的創作方式決定了它是以合聲律曲調為審美追求,而品格往往得不到重視。
儒家傳統文化強調作者自身的道德修養,重視作品反映的道德情操,并以此作為評價其作品品味的標準。因此劉熙載認為:“美成詞信富艷精工,只是當不得個‘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劉熙載認為周美成詞作中的“雅”只是表面現象,骨子里當不得一個“貞”字,在他看來周邦彥詞缺乏風骨及高尚品格,不能起到教育讀者、有益世道人心的作用,因而不能被認為是君子寫的詞,更不足以被作為學習的對象。通過“詩品出于人品”這一閱讀標準,周美成的詞“未得君子詞”的地位便在劉熙載那里確定下來。他又說:“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煉,然未得為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這里的“蕩”和“貪”皆是指氣格不正。同樣的他認為柳永的詞:“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絕風期未上耳。”這里的“風期未上”也是在強調詞的品格,可見劉熙載一改前人論詞以藝術為重的觀點,取而代之的是“論詞莫先于品”。
劉熙載在《詩概》中說“詩品出于人品”,論詞時也認為詞品與人品應具有一致性。在整部《詞曲概》中,劉熙載給予最高或較高評價的是蘇東坡、辛棄疾一派詞人。劉氏指出:東坡《定風波》云:“尚余孤瘦雪霜枝”;《荷花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藝概·詞曲概》)。“雪霜枝刀”“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雪霜枝”“風流標格”,正是融齋詞品結合人品對東坡詞作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概括。
三、“情”須是雅正之情
劉熙載肯定的是憂國憂民或潔身自好的正統儒教認可的可登大雅之堂的情感,對于抒發兒女情長的作品,還是有所抑制的。{3}比如他對柳永的評論:“耆卿《兩同心》云:‘酒戀花迷,役損詞客。余謂此等只可名迷戀花酒之人,不足以稱詞客,詞客當有雅量高致也。或曰:不聞‘花間‘樽前之名集乎?曰:使兩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質之。”(《藝概·詞曲概》)劉熙載認為只有恢弘的氣度、高雅的情致才可稱為詞客,對于柳永抒寫流連花間的相思之情是很不屑的,所以緊接著下一條他寫道:“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于情者,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為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事,其小焉者也?”(《藝概·詞曲概》)劉熙載指出他所肯定的“情”是儒家提倡的有益世道人心、政治教化的“情”,是“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情。劉熙載持有“尚正”的文學觀,在論詞曲時多次出現“正”這一字眼。“正”意為符合儒家傳統禮節,符合仁義之道。
“尚正”文學觀滲透于中國古代文學活動的方方面面。評論任何作家作品,劉熙載都強調作家的人格修養與作品的政教內容。因為文學作家和文學作品擔任著教育感化讀者的任務。所謂“曲盡人情”,這種“情”便是以正為主導之情。劉熙載論曲時這樣說:“可知歌無古今,皆取以正聲感人,故曲之無益風化,無關勸誡者,君子不為也。”
四、重視詞曲的社會功能
劉熙載在《藝概·自序》中說:“藝者,道之形也。”他認為各類文體都有“載道”“明道”的使命,詞曲也不例外。正統的詩文,歷來重視言志載道的社會功利作用,故詩有詩教、文有文道。不僅重視言志,而且更重視“志”是否合乎儒家的要求。
藝術與倫理性的社會感情相聯系,從而與現實政治有關,這是儒家對禮樂的理性主義的解釋。{4}劉熙載認為詞要為社會服務,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也是這一儒家思想的體現。“詞莫要于有關系”,這里的“關系”便是指詞與社會的關系。在與詩作對比時又說:“詞導源于古詩,故亦兼具六義”“詞之興、觀、群、怨,豈下于詩哉?”這是以詩教為詞教,強調詞與其他正統文學一樣須具有社會功能。如“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為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這里的表德即是指在詞中有益宣傳某種政治思想,可見劉熙載對于“表德”的重視。
“詞,樂章也,雅鄭不辨,更何論焉。”說明詞雖是樂章,但論詞的前提是辨“雅鄭”。這里的“雅鄭”并不是指雅頌之聲和民間音樂,而是指詞的兩種截然相反的類型。“雅”是能夠給人積極向上精神力量的作品,“鄭”則是使人耽迷酒色享樂的靡靡之音。將“雅鄭”即詞對于人是否具有積極作用作為論詞的又一前提,體現了劉熙載對于詞的教化作用的重視,亦是其正統文學觀在詞論方面的體現。
五、寬厚、中和的批評原則
中國古代文論家在評論某一作家作品時向來不走極端,在闡釋一部作品時,會將作者本人的思想、身世和所處時代等各種因素綜合考慮,也就是“知人論世”的原則。這一原則注重聯系作者的生平思想、所處的時代背景及道德修養,沒有將詞作與作者本身的人生經歷割裂開來。如在評文文山詞說道:“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對于蘇辛詞他說:“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悉出于溫柔敦厚。”
情感是文學活動的核心要素,貫穿在整個文學活動之中,當一件作品呈現在讀者面前時,有的讀者反映平淡,有的讀者反映強烈,這與讀者的情感與作品表現出來的情感契合度相關,比如:“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對于讀者接受的差別,劉氏也不求統一的標準,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
劉熙載持溫柔敦厚的論詞觀。“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杰之詞。才子豪杰,各從其類而愛之,強論得失,皆偏詞也。”可見劉氏對于讀者喜好及個人的價值取向持寬容的態度,并沒有強論得失。對思想傾向不完全合乎儒家的作家作品也不一概否定,而是持有寬容的態度。{5}再如“劉改之《沁園春》泳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闕。以褻體為世所共譏,然病在標者猶易治也”。劉改之因作品“褻體”而受到世人的譏諷,但劉氏卻未和世人一樣評價他,而是認為他“病在標猶易治也”,由此可知劉熙載寬厚、仁者愛人的本性,“治”表現出劉氏對于過錯的積極糾正,亦是對于文學作品盡善盡美的追求。
綜上所述,劉熙載論詞曲帶有明顯的正統文學觀念,關注詞曲的社會作用,強調作品的雅鄭和作者的品格,這些思想在文學作品飛速增多的當下具有積極意義。
{1} 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6頁。(以下所引《詞曲概》中文字皆出此書同一版本,不另作注)
{2} 龍榆生:《詞曲概論》,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3}{5} 李超:《論劉熙載〈藝概〉的文學接受思想》,《浙江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
{4} 李澤厚:《美的歷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53頁。
參考文獻:
[1] 劉熙載.藝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3] 龍榆生.詞曲概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4] 蔡鎮楚.中國文學批評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5.
[5]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殷大云.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初探[J].內蒙古師大學報,1984(4).
[7] 周峰.論劉熙載文學思想的儒家傾向[J].上海大學學報,1995(1).
[8] 曹保合.談劉熙載的品格論[J].衡水師專學報,2002(1).
作 者:劉曉萌,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2015級古代文學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學。
編 輯: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