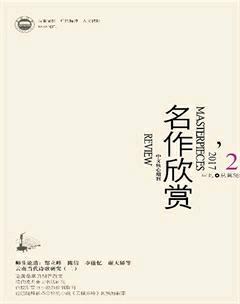張愛玲小說的悲劇意識
摘 要:張愛玲的小說充滿了強烈的悲劇意識,她善于展現舊中國社會形形色色的人,她給弱者以同情,她同情那些受傷了的灰色人物,因而其作品總是充滿了清晰而濃重的悲劇意識。她的這些悲劇意識來源于她自身對于人生與社會的認識,并呈現出極其鮮明的時代特色。
關鍵詞:張愛玲 悲劇意識 小說
一、鮮明的文化特征
所謂的悲劇意識,通常是在當人們體會到自我和整個人類社會、自然界抑或全宇宙存在對立和分裂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同時也是在人們體會到“我”和“本我”之間同樣存在矛盾的過程中產生的,伴隨著人類意識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人們的悲劇意識將越來越強烈。張愛玲常常通過寫作將自己的人生苦悶表現出來,我們能夠充分地感受到悲劇意識蔓延于其整部作品中,作品呈現出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一)“蒼涼”世界的“蒼涼”人生 張愛玲在小說創作中通常采用一言說的方式,通過自己獨特的視角描述新舊更替時代的上海、香港等地老一輩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在她的小說中,“蒼涼”二字顯得尤為突出,其他與“蒼涼”接近的字詞也用得非常頻繁,充滿了凄涼之感。以《沉香屑·第一爐香》為例,葛薇龍和喬琪夜即使在喧嘩熱鬧的夜市中閑逛也體會到了無限的荒涼,在繁華中仍然感受到對未來的迷茫。而在另一部作品《傾城之戀》中同樣如此,小說開篇便用蒼涼的胡琴聲拉開了故事的序幕,凄凄慘慘的胡琴聲使整個小說顯得格外的凄涼。在《金鎖記》中,長安不得不結束一段曾經讓自己容光煥發的愛情時,張愛玲寫道:“這是她的生命里頂完美的一段,與其讓別人給它加上一個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結束了它。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又一個“蒼涼”出現在小說中,可以說“蒼涼”是張愛玲小說最普遍的基調,從中也可以看出她對現實社會甚至整個人類世界都充滿了無限的失望和不滿。張愛玲筆下一個又一個傳奇的故事總是容易讓人不由自主地沉迷于其中,讓人們充滿好奇地去查探曹七巧以及許小寒們在生活中不得不經受的各種壓抑,葛薇龍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虛榮以及墮落。通過張愛玲的小說,人們可以很容易地體會到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時代的繁華早已散去,舊家族的沒落讓人心最丑陋的一面逐漸暴露。可以說,“蒼涼”二字既描繪了小說主角們的生活狀態,也體現了整個現實世界的“蒼涼”。
(二)末日意識與現世享受 從張愛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無論是對整個社會的人性還是對人生都含有一種異常的絕望。她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個人即便有足夠的時間等待也沒有什么用處,畢竟我們的時代是倉促的,當今的世界已經居于極大的破壞中,并且還會有更多更大的我們無法想象的破壞正在等待著我們。不管我們的文明最終是走向升華抑或是浮華,這些都已經不再重要了,因為它們終將變為過去。人們總是說我的小說中充滿了‘荒涼,主要是因為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里已經受到了太多威脅。”在她看來,人們生活的那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現實世界最終將會在無盡的破壞中變為過去,可以說這是張愛玲悲劇思想的較淺層次的體現。除此之外,她認為更多更大的無法想象的破壞終究還會到來,這將變為更大的“威脅”,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也是她悲劇思想的更深層次的體現。從某種程度上說,張愛玲的末日意識是十分難得的。縱觀我國現當代作家,只有極少數的人有這樣的意識。此外,她的這種悲劇意識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時代的變化做出適當的調整。總的來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張愛玲的悲劇感并不是徹底的、一成不變的。于她而言,無論是人們的人生指向抑或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文明,最終都將不復存在,悲劇才是永恒不變的。可以說,張愛玲的“蒼涼”是骨子里散發出來的,但是她卻能十分巧妙地把這種“極端覺悟”與“人生歡樂”恰到好處地融為一體,并且通過世俗生活的歡愉將末日世界產生的各種絕望沖淡,創造出一個十分凄美的藝術傳奇世界。
二、悲劇意識的現實成因
榮格曾說過,一個人的“意識經驗”對其作品的創作有著極大的影響,不論是作品的選材還是創作角度都和作家的生活背景以及人生經歷有著密切的聯系。眾所周知,張愛玲的家族在當時是十分顯赫的,她的外祖父和祖父都位居高官。但是,對于1920年才出生的她來說,她親眼看到的以及親身體會到的卻是整個家族的沒落,家族的變化使她變得非常惶恐和壓抑。對于她來說,惶恐并不是由于物質生活的缺乏,而是遭受了太多的精神壓迫。父母的離異以及父親的再婚,讓她從小就失去了常人很容易便能獲得的父愛和母愛。19歲的她考上了令人羨慕的倫敦大學,但是由于混亂的戰爭的影響,她不得不選擇在香港上大學。香港最終還是沒能躲過戰爭的侵襲,1941年12月,日本人開始不斷地向香港發動戰爭,正值大二的張愛玲不得不中斷了自己的學生生涯。親身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她充分體驗到了人生的脆弱。一旦發生戰爭,人生中的所有東西都充滿了不確定性。戰爭對張愛玲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可以說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她的思想方向。年少的張愛玲早早地便經歷了家族的沒落、父愛母愛的缺失以及戰爭的黑暗,可以說這樣的人生經歷使得她的悲情意識越發濃重,她學會了冷眼觀看這悲劇的世界,學會了用暗含譏諷的寫作方式來表達自己內心的不滿。總而言之,張愛玲的悲劇意識與其人生經歷以及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與此同時,這種悲劇意識又反過來影響著她的整個人生態度,使其悲觀意識不斷加深。
三、獨特的文化意義
(一)為海派文學注入新的靈魂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張愛玲的末日意識與她對上海糾結的情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當然,我國傳統文化對于她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的。那么,她從小生活的上海,她自幼便接觸的上海文化以及她喜愛的海派文學之間又會有什么樣的關系呢?總的來說,我國的傳統文化以及文學使她獲得了相對成熟的寫作技巧,同時也使她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具有中國色彩的悲劇意識,但是,真正使她的悲劇意識帶有現代色彩的還是都市文學。
都市文學,顧名思義便是將當前的現代都市作為寫作的背景和基礎,用現代人普遍具有的價值觀來仔細地觀察都市生活以及現代文學的一種文學寫作方式。最初開始將都市生活作為寫作題材和背景的是葉靈鳳先生以及創作了《沖擊期化石》一文的張資平。后來,穆時英、劉吶鷗等也逐漸將對都市的描寫以及都市情緒融入自己的作品中。除此之外,張愛玲也開始描寫中上層家庭的都市生活。從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現代海派文學的發展脈絡,他們的作品除了描繪現代都市之外,還具有十分突出的現代意識,體現了現代人的內心世界以及對個性化的追求,同時也表現出現代都市人普遍存在的精神矛盾。毫無疑問,張愛玲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她對現代都市的體會以及對都市人生活狀態的描寫都是十分真實細致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和新感覺派相比,張愛玲對都市人的精神世界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會。因此,她對都市人的人生處境以及狀態的描寫也具有了更多的悲劇意識。
(二)解構傳奇,還原人性底色 和大多數人一樣,年少時期的張愛玲也非常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出名,能被更多的人認識,但是真正出名后,她卻刻意地想要隱藏自己,她遠離了喧鬧的都市,過起了隱居生活。她在《沉香屑·第二爐香》中也表達了自己只是想以一個繁華世界外的人的角度來觀看這個世界的紛紛擾擾以及潮起潮落。她沒有像當時的大多數作家一樣在作品中表達憂國憂民的焦慮,她只是靜靜地觀看著這個世界的世俗人性。她通過自己的方式來還原人們的真實狀態,同時也使得愛情的神圣與傳奇不斷被消解。除此之外,張愛玲也通過作品對男權、親情、革命等表達了自己的疑惑與嘲諷。
(三)凌厲的文化批判精神 20世紀40年代,傅雷在評論張愛玲的作品時說:“顯而易見,《金鎖記》是她至今為止最成功的作品,很有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的韻味。”傅先生對張愛玲的作品給出了非常高的評價。于青曾說:“假若將魯迅先生對于國民性的批判當作是對我國民族文化構建的巨大貢獻,那么,毫無疑問,張愛玲對于女性意識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國民族文化的構建。”從曹七巧這個人物形象中我們能夠明顯地看到張愛玲同樣體現了反封建的意識,但是與魯迅相比,張愛玲對封建文化的感情顯得更加復雜。魯迅是以一種理性的態度堅決反對宗法社會的黑暗腐朽,他通過塑造一系列鮮明的形象,如阿Q、祥林嫂、愛姑等來表現自己的反封建思想,同時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改造國民性,構建新的民族文化體系。張愛玲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十分矛盾,從她的小說中對于人物著裝的刻畫以及對周圍環境的描寫可以看出,張愛玲對封建大家庭有著很深的眷戀,但她也深深地知道,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文化對人性的殘害是十分慘烈的。
參考文獻:
[1] 李掖平.生存悲劇的蒼涼書寫——論張愛玲小說的悲劇意識[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2).
[2] 顏小留.論張愛玲小說《傳奇》的悲劇意識[J].汕頭大學學報,1996(6).
[3] 楊林.論張愛玲小說中的生命悲劇意識[J].現代交際,2014(4).
作 者:胡春芳,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3級本科在讀。
編 輯: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