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比大叔”的童詩
陳賽
雖然看不到你的臉/可當你翻開這些詩篇/我在某個遙遠的地方/能聽見你的笑聲/我也露出笑臉
——謝爾·希爾弗斯坦
在童詩集《人行道的盡頭》中,謝爾·希爾弗斯坦向孩子發出了邀請:
如果你有夢想,請進,
如果你有夢想,如果你愛說謊,
如果你喜歡祈禱,如果你充滿希望,如果你會花錢買一顆魔豆……
如果你會裝模作樣,請你坐到我的火堆旁,
我們來編織一個金色的彌天大謊。
請進!
請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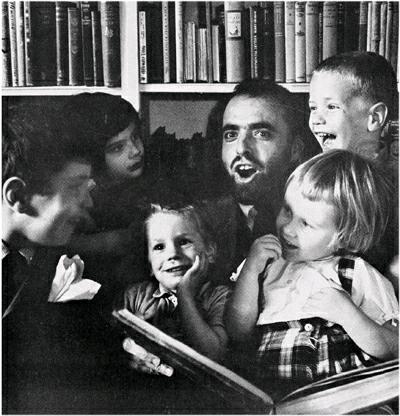
“謝爾比大叔”的邀請令全世界的孩子難以抗拒。他的詩里充斥著古怪荒唐的孩子,一個提著水桶去擦星星,一個用胡子蕩秋千,一個要拍賣自己的小妹妹,一個把自己的弟弟當廢品扔掉,一個裝病不去上學,一個愛從26層高樓往下吐口水,一個在睡前虔誠地向上帝祈禱:“如果我在醒來前死去,求主讓我的玩具都壞掉。這樣別的孩子就再也不能碰它們……”
謝爾曾經說過,自己之所以寫童詩,是因為自己能在10分鐘之內寫出一首來。他的傳記作者麗薩·羅格克(Lisa Rogak)甚至將他與莫扎特相比,說是上帝在借他們的才華發言。
他的確有一種獨特的駕馭文字的才華。他的詩既辛辣,又動人,既怪誕,又搞笑,有時候粗鄙不堪,卻又誠實率直,富有童趣。
謝爾一生寫了數千首詩,畫了堆積成山的漫畫,僅從數量和豐富性而言,就構成了他獨特的藝術魅力。但這些詩畫中比例更大的是給成年人寫的。在給孩子寫書之前,他是《花花公子》的專欄作家,畫漫畫,寫游記,走到哪里都有兔女郎投懷送抱。他也為流行歌曲寫歌詞(他曾經為美國一些非常著名的鄉村音樂歌手寫歌,比如約翰尼·卡什的《一個叫蘇的男孩》、瑪利安納德·費思福的《路西·佐敦之歌》以及愛爾蘭流浪者的《獨角獸》等等),還寫了上百出戲劇,包括名噪一時的《女人或是老虎?》。
這是一個很復雜的人,思想怪異,視角獨特,我行我素,能享受生活,也善于內省。他是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能像孩子一樣思考問題的成年人,也是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像成年人一樣游戲人間的孩子。
正因為如此,他的童詩既天真又老成,既童言無忌、天馬行空,又保留了對人性本質的深刻洞察,對孩子和成年人都具有極強的吸引力。但與此同時,他的詩和畫也被認為“太詭異、太反權威,不符合兒童脆弱的神經”。他最著名的兩本童詩集《人行道的盡頭》和《閣樓上的光》(1981年出版,《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的第一本童書,并在榜單上停留了三年多)曾經在美國的多家圖書館被禁多年。
人們列舉了他詩中各種少兒不宜的內容,毒品、欺騙、暴力、自殺、死亡、邪教,對權威的蔑視,對父母的不敬,甚至還有食人的情節,比如有個小孩掉到絞肉機里,被不知情的別的孩子當漢堡給吃掉了。
更讓父母光火的,可能是《小艾比蓋爾和漂亮的小馬》這樣的詩。小姑娘艾比蓋爾想要一匹小馬,她的父母不給她買,于是她難過地死掉了。詩的插圖就是死去的艾比蓋爾躺在那里,身邊是她悲傷的父母。詩的最后,謝爾告訴他的小讀者:“這是個很好的故事,/當你的父母不給你買,/你想要的東西時,/你可以讀給他們聽。”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童詩完美地濃縮了童年的種種憂懼與渴望。孩子們在他的詩里發現相似的自戀、缺陷、愛、恨、挫折感、對力量的幻想以及種種難以言說的欲望;而有心的成年人則能從中品出更為復雜的況味。比如有一首詩叫《十八種味道》,十八種香甜誘人的口味——巧克力、酸橙和草莓,/南瓜、香蕉和咖啡,/焦糖牛奶還有波森梅,/堅果冰激淋,烤杏仁,/香草汁,奶油咸味糖果。/奶油磚、蘋果浪,/椰子外加摩卡咖啡,/桃子白蘭地,檸檬蛋羹,/每一勺都是那么爽滑甜美,/這甜筒冰激淋可是全城之最,/如今它卻躺在了地上……嘖嘖——
孩子們讀了,固然為冰激淋扼腕嘆息,而成年人感到的,恐怕更多的是悲涼,生命的豐美與脆弱,轉折就在那一句短短的“嘖嘖”。
幾年前,《連線》雜志的編輯為硅谷父母挑選書單,謝爾有5本書入選。推薦這套書的編輯說:“沒有一個現代詩人能像謝爾那樣捕捉童年的想象力與玩心。”但我想,他之所以為極客所熱愛,還因為他看世界的角度和我們如此不同,比如這首《倒影》:每當我看到水中/那個家伙頭朝下,/就忍不住沖他笑哈哈,/但我本不該笑話他。/也許在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小鎮/穩穩站著的是他/而我才是大頭朝下。
《向上跌了一跤》:我給鞋帶絆倒,/向上跌了一跤——/向上跌過屋頂,/向上跌過了樹梢,/向上跌過了城市上面,/向上跌得比山還高,/向上跌到半空,/那兒聲音和顏色交融在一道。/我朝四周一看,/頓時眼花繚亂,/昏頭昏腦,/我的肚子實在難受,/于是直往下掉。
《新世界》:樹木倒立著,搖擺自由,/汽車飄起,天上懸掛著高樓。/有時感覺真不錯,/換個角度來看這地球。
還有首《聽聽那些“不許”!》:孩子,聽聽那些“不許”,/聽聽那些“不要”,/聽聽那些“不該”,/那些“不可能”,那些“不會”。/聽聽那些“從來就沒有過”,/然后仔細聽我說——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孩子,/任何事都會成為可能。
這首詩今天聽起來,有點像硅谷青年每天掛在嘴邊的輕飄飄的口號,對謝爾來說,卻是他一生與命運抗爭的真實寫照。1930年,謝爾·希爾弗斯坦出生于芝加哥中西部的一個小鎮,父親是東歐猶太移民,母親在芝加哥出生,大蕭條時期夫婦倆苦心經營一家不成功的面包店。謝爾天生有讀寫障礙,注意力障礙,父親希望他繼承家業,他卻一心只想畫漫畫。
他很早就發現自己對畫畫的熱愛,但因為父親的激烈反對,他的整個童年就是在不安全感與自我懷疑中度過的。多年后,他回憶說,如果有得選,他“當然更愿意做一個三壘手,手臂上掛著三個女孩”,但幸運的是,他既不會打球,又不會跳舞,得不到女孩子的青睞,只好把精力都轉到畫畫寫詩上面。而且,當時無論畫畫,還是寫詩,都是懵懵懂懂,沒見過什么世面,也沒什么人可以抄襲,卻由此發展出了他自己的風格,此為又一幸事。
更幸運的是,命運指引他同時找到了女人和藝術——他23歲那年從朝鮮戰場退伍歸來,本想靠畫漫畫養活自己,卻到處找不到工作,只好一邊畫畫一邊擺攤賣熱狗。百般落魄之中,他遇上了《花花公子》的創始人休·赫夫納,兩人一見如故——他們都在芝加哥長大,都參過軍,都是漫畫家,都熱愛女人。謝爾為《花花公子》創作的第一幅漫畫刊登在1956年8月號上,從此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創作生涯。
為《花花公子》工作的幾十年里,他經常往返于芝加哥與紐約,出沒于各種酒吧、派對、夜總會,在餐巾紙和桌布上寫詩畫畫,用低沉的煙熏嗓子唱民歌和爵士。他喜歡跟人交談,但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觀察者,而不是社交愛好者。無意間聽到的只言片語,或者隨意捕捉到的一個面部表情,都可以成為一首新的詩、一幅畫或者一首歌。他還說服了赫夫納資助他周游世界,住最豪華的酒店,跟最美麗的女人做愛,然后發回文章、攝影與漫畫。
謝爾從來就沒有想為孩子繪畫或者寫東西。他對孩子沒什么耐心,對兒童文學更是沒有好感——“見鬼,小孩子已經受夠了自己的渺小和不重要。但E.B.懷特給了他們什么?一只提心吊膽會被沖下下水道或掛到窗簾上的老鼠,一只準備去死的蜘蛛。”
如果不是被他的朋友托米·溫格爾強拉硬拽進當時厄休拉·諾特斯喬姆的辦公室,他大概永遠也不會給孩子寫東西。厄休拉·諾特斯喬姆是當時紐約童書界最著名的童書編輯,曾經發掘出一批美國最優秀的童書作家,包括莫里斯·桑達克、托米·溫格爾和路易斯·菲茲修等。她的出版哲學是“為壞孩子出好書”。
1963年,32歲的謝爾出版了第一本童書《會開槍的獅子》,講一只獅子在“成功”之路上遭遇的身份危機。在謝爾的所有作品中,這是他本人最喜歡的一本,因為“內涵最為復雜”。
一只任性的小獅子,自從學會了開槍,并成為無可匹敵的神槍手之后,它的生活就完全改變了。它離開了森林,離開了獅子朋友,來到大城市,到處表演,掙了好多錢,成了大名人。但是有一天它突然覺得做什么都沒意思,做名人一點都不好玩。而且更糟糕的是,當它再次回到森林里的時候,它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只獅子還是一個人。
但是,外界最多的毀譽都在他的第二本童書——《愛心樹》上。一棵樹愛上了一個男孩,讓他在自己的枝椏上玩耍,享受多汁的果實。男孩一點點長大,樹把自己的樹蔭、果實、枝葉,到最后把整個樹干都給了男孩。等到男孩變成了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回到家里,坐在樹樁上休息——那是樹僅剩的東西了。
在童書史上,《愛心樹》是一本罕見的雅俗共賞、老少皆宜的作品,同時也是爭議最大的作品之一。這么多年來,不同的人從這個故事中讀出了完全不同的意義,有人認為這首詩歌頌了母愛的無私,有人則認為批判了人性的自私。宗教布道者讀出了基督無條件的愛;女權主義者則讀出了男女之間施與受之間的不平等,他們認為愛心樹是女性無私的象征,而小男孩是男權至上主義者的代表;生態主義者則讀出了人類對環境的殘害。熱情的支持者將這本書列入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童書之列,而激烈的批評者則認為這本書對年輕人心靈的摧殘在過去50多年里沒有別的書可以相提并論。
謝爾自己的說法則是:“這個故事并沒有太多信息要傳達,不過想說,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一種人施予,一種人索取。”僅此而已。
這本書當初的出版并不容易,編輯們認為這個故事對孩子來說太壓抑,對成年人來說則太簡單,而且謝爾堅持要保留那個悲劇的結局——“人生的結局通常都很悲慘,即使我的大部分東西都很搞笑,但你也不必非得強作歡喜。”
寓言的魅力就在于,越是簡單,闡釋的空間越大。我更傾向于認為,這本書原本就無關愛或幸福,而是關于結局本身,關于時光的流逝,一切終歸無可挽回的衰敗。就像最后一頁,一個光禿禿的樹樁和一個駝背老頭木然看著遠方。這可能更符合謝爾對于人生荒涼本質的感受。
謝爾于1976年寫出了《缺失的一角》,講一個圓缺了一角,于是滿世界尋找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它漂洋過海,歷經風吹雨打,終于找到了最合適自己的那一角,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圓。
故事本來應該在這里收尾,謝爾卻讓他的圓唱著歌離開了——它仍然要去尋找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
謝爾向來不掩飾對大團圓的不屑。無論在他的詩、歌、戲劇還是漫畫里,都沒有快樂結局。他有一首詩叫《歡樂之地》:你去沒去過“歡樂之地”?/那里所有人都滿心歡喜,/他們成天玩笑打趣,/還唱著最快樂的歌曲。/一切事物都那么美,/“歡樂之地”沒有煩惱。/那里整天充滿歡樂。/我也曾經去過那里——真是無聊。
在他看來,所謂大團圓結局、魔力或神奇手段會在兒童心中“造成一種疏遠感和陌生感”。孩子們會問:“為什么你給我講的那些幸福的事情我就沒有遇見?”
但是,圓到底在追尋什么?一千個人大概又會得出一千個不同的結論。但缺失與追尋之間,自由與羈絆之間,那一點點瘋狂與非理性,一直是謝爾所追求的。
他曾經說過:“一雙舒服的鞋和隨時離開的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兩件東西。”
他的一生,從未停留于一種藝術形式,或者在同一個地方停留太久。相同的哲學也適用于他的愛情。他從未結婚,有無數的性伴侶,但也養育了兩個孩子。他的第一個孩子夏娜死于腦動脈瘤,死時年僅11歲。這對他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至死都未能解脫出來。女兒的死也使他很長一段時間內遠離童書創作。
他曾經說過:不要依賴任何人——男人、女人、孩子或者狗。我想去世界的每個地方,見識一切東西,生活中一些美妙的東西會使你欣喜若狂。
但是,這一切終歸又讓他失望。這也是為什么他最后終止了《花花公子》的旅游專欄,他告訴休·赫夫納:“那些旅行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因為都是跟我一樣的人。我已經見過高山,見過金字塔,見過熱帶,那又怎么樣?如果我創造了一個世界旅行者和冒險家的形象,現在我想坐下來,跟蘇珊一起種玫瑰——我就要這么做了。”
這位蘇珊,不知是否就是夏娜的母親?
1999年5月,謝爾因心臟病在佛羅里達州基韋斯特的家中逝世,享年68歲。
在他死后,生前未曾發表的100多首童詩結集出版,題為《什么都要有》。詩集中最后一首是《我走了以后》:
我走了以后,你怎么辦?
誰為你寫詩,誰為你畫畫?
某個更聰明的人,某個新來的人?
某個更棒的人——
也許就是你自己!

